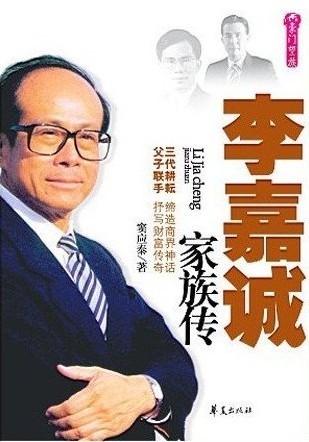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杰勒德感到怪难为情。
“别怕,小伙子,魔鬼呜呼了。”那老兵打着嗝说道,一边丢给侍者一个钱币。
“你跟他半斤八两,一样差劲。”老头生气地说道,“你付得太多了。”说着,那专横的老阿里斯泰底斯带着一副严加责备的面孔从木盘里拿出一个钱币还给了他。这时,杰勒德在一个半小时之前驳斥过的那个人从持续的沉默状态中清醒过来,走到他跟前说道:‘你说的固然不错,但你要知道,花蜜通过蜜蜂的肚子以后照样很好。”
杰勒德呆呆地望着。这回答来得太迟了,以致他莫名其妙,究竟这是对什么东西所做的回答。看到他哑口无言,那人断言他是被驳倒了,便心安理得地走了回去。
卧室在楼上,看起来像些土牢,除了床以外别无家具。一个男招待专断地决定谁和谁睡在一起。无论添钱也好,祈求也好,都不能使谁独自睡一张床,因为这是为惯例和习俗严格禁止的,否则你就等于要求独占一副跷跷板,毫无意义。侍者指定一个大黑胡子的人和杰勒德同睡一张床。他倒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但也不是十全十美。他不愿睡觉,而愿意坐在床边强行地没完没了地对可怜的杰勒德讲述当天发生的事情,并对那些既不凄厉动人,又不滑稽幽默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轮番地又哭又笑。最后,杰勒德把手塞进耳朵。由于他嫌床单被褥太脏,无法脱衣,便和衣而卧。不久,总算进入了睡多。但睡了一两个小时,他就被冻醒:原来是他那喝醉了的同床把羽毛垫全给霸占了。本能如此,无可奈何。他们睡的是两张拼拢起来的床。较低的一张很硬,是草垫;较高的一张很软,是轻如绒毛的羽毛垫。杰勒德拉拉羽毛垫,但那富有经验的酒鬼机械地死死抱住不放。杰勒德企图趁他不备时猛地把它拉开,但是本能太强,他对付不了。于是他从床上下来,跪在他的同床未加防范的一侧,轻而易举地把羽毛垫夺走,卷着它滚进床底,躺在垫子的边上,而把剩余部分裹住肩头。入睡之前,他不时地听见他上面有个东西在咕噜着,嚎叫着,因而使他感到小小的满足。本能就这样被机智击败了,而胜利了的机智则躺在羽毛垫上得意洋洋地笑着,显然是没有完全被灰尘呛得喘不过气来。
天刚亮,杰勒德就起了床,把羽毛垫往打着鼾的同床身上一扔,跑出去寻觅牛奶和新鲜空气。
一个兴高采烈的声音用法语向他打招呼:“嗨!伙计,你真是日出而作呀。”
“躺在狗窝里的人自然得早起。”杰勒德生气地说道。
“别怕,朋友,魔鬼呜呼了。”这是他立即得到的回答。接着老兵告诉杰勒德,他名叫丹尼斯,打弗拉辛到西兰,前往公爵在法国的领地。这是一个使他感到较为满意的调动,因为他可以重返故乡,与曾和他泣别过的一群姑娘重逢,并将再听见人们讲法语。“你是谁?到哪儿去?”
“我叫杰勒德,往罗马去。”更为含蓄的荷兰人说道,说话的表情并不想使交情更发展一步。
“那就更好了。我们可以一道走到勃夏第。”
“我要走的不是这条路。”
“条条道路通罗马嘛。”
“不错。但我要走的是到罗马的最近的路。”
“那么,好吧,为了找个好伴,就该我来绕点路了。你的相貌我很喜欢,而你又能说法语,或基本上能说法语。”
“在说定以前,我得先讲两句。”杰勒德冷冷地说道,“我也是按俗话行事。俗话的确能使年轻人增长见识。‘绵羊说好狼是恶伴’,而常言说,当兵的和狼差不多。”
“这是谎话,”丹尼斯说,“再说,如果当兵的真是狼,那么‘狼不吃狼’。”
“不错,兵士先生。不过,我不是一只狼。您是知道的,‘一有机会可乘,狼就要逮羊吃’。”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别谈什么狼和羊吧。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好兵绝不抢劫一个同伴。得了,年轻人,猜疑过多是不适合你这个年龄的。走江湖的人要学会看相。我想我既然在你脸上看出忠厚老实,你在我脸上也能看出忠厚老实。你担心的是你腰带上那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吗?”(杰勒德的脸一下子白了。)“瞧这儿吧!”说着他解开他的袋子,从里面倒出两捧金币,然后再把它们放回原来的藏匿处。“这是给你的一个抵押。”他说道,“你拿着这个,让我们结为同伴。”说罢,他把袋子连同金币全部递给了他。
杰勒德呆望着。“如果我过于谨慎的话,你这点钱还不够。”但他脸红了一阵,看到这人对自己的信任而显得高兴。
“哼!我能看相,你也必须会看相。要不,你永远没法把你那四根骨头平安地带到罗马。”
“当兵的,你会发现我是个没趣的伙伴,因为我的心很沉重。”杰勒德说道,慢慢地向他让步。
“我会使你开心的,我的小伙子。”
“我想你会的,”杰勒德亲切地说道,“这些天我真太需要耳边听听友善的声音。”
“啊,有我在身边,没有人会感到悲伤的,我会用我的口头禅鼓舞他们可怜的心:‘大伙别怕,魔鬼呜呼了。’哈!哈!”
“那么,就这样吧。”杰勒德说道,“但你要把你的袋子拿回去,因为只信任一半我办不到。我们将一道走到莱茵河,愿上帝和我们两人走在一起!”
“阿门!”丹尼斯说道,然后举起他的帽子,“向前进!”
两人勇敢艰难地往前走着。丹尼斯使令人疲乏的旅程充满了生气。什么打仗、围城,以及一些使杰勒德感到新鲜的东西,他都谈,而且,是个不管走到哪儿总要闹点小风波的人。他碰到谁都要对他说说他的口头禅。“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但它会把他们唤醒过来。”他说。不过,每当他们碰到修士或神父,他总要拉长脸,谋求神父的祝福,并毫不畏惧地往他身上倾泻潮水般的德国话,尽管语序混乱,形不成句子。他对看到的所有妇女,不管地位高低,一律脱下帽子,并用他的鹰眼仔细琢磨她的最美之处,然后用切合这类事物的祖国语言对她进行赞美。每当他看到一只食腐肉的乌鸦或喜鹊,他都要取下他的十字弩,跑开大路一浪远去包抄它。有一次,他的确以值得赞叹的利落和敏捷射下了—只老乌鸦,然后跑到最近的一个鸡窝,溜进去,把它放进窝里。好心的主妇会说:“唉呀,魔鬼在孵我的鸡蛋了。”
“不会。你忘记它已经死了。”杰勒德反对道。
“它是死了,它是死了,但是她不知道,因为她不认识我这个把喜讯从这一城市带到那一城市以鼓舞人心的好人。”
这就是平静时的丹尼斯。
黄昏时,我们这两位旅客来到一个村庄。这是个很小的村庄,但有一个招待旅客的地方。他们四处寻找,结果找到一个带有谷仓和马厩的小屋子。小屋子里少不了有个火炉,再就是绳子上挂着烘烤的衣服,还有一两个旅客阴郁地坐着。杰勒德要求给他们开晚饭。
“晚饭?我们没有时间为旅客做晚饭。我们只供给住宿,给人和牲口供给舒心的住宿。此外,你们可以得到点啤酒。”
“生在荷兰,偏要去别的国家,真是个疯子!”杰勒德用荷兰话气愤地哼道,女店主惊了一下。
“你在说什么鬼话?”她问道,一边画着十字,露出了迷信的惊恐神色,“你们可以在村里买你们高兴买的东西,然后拿到我们灶上煮。但是,好旅客,求您别在这儿念符咒。现在别念。您一念可真叫我起鸡皮疙瘩。”
他们跑遍了全村找吃的,最后总算搞到了烤鸡蛋和褐面包当晚餐。
天色还一点不晚,他们的侍者便来找他们。这是一个提着灯笼、面颊呈玫瑰色的老人。
他们跟他走去。他领着他们走过一个肮脏的农家场院。他们费劲地找干净的地方落脚,小心地挪动着脚步,最后被带到一个奶牛房。奶牛的每一侧都铺着一点干净草,外加一捆捆好的草当枕头。老人以慈父般的骄傲望着他的这一安排。杰勒德可办不到。“怎么,你们让基督徒睡在牲口中间吗?”
“得了,这对于可怜的牲口已经够苛刻的了,连个转身的余地也没有。”
“什么?这么说,对我们就不算苛刻了?”
“苛刻在哪?艰苦在哪?我一辈子都在它们中间睡觉。瞧我!我已经八十了,有生以来从没头疼过——都是因为在奶牛中间睡觉。你们这些傻瓜呀!奶牛的呼吸比酒或者基督徒的呼吸甘美十倍。不信你试试!”说着他把卧室的门砰地一关……
“丹尼斯,你在哪儿……”杰勒德呜咽着问道。
“这儿,在奶牛的这边。”
“你在干什么?”
“我不晓得。但就我所能猜想的,我想我是快睡着了。你在干什么?”
“我在做祷告。”
“在你的祈祷中别忘了为我祈祷。”
“那可能吗?丹尼斯,我很快就要做完了。别睡觉,我想聊天。”
“那就请快吧,因为我感到……嗯……像……躺在一片暖云上——在天上飘。”
“丹尼斯!”
“嗯!唉!喂!是起床的时候了吗?”
“哎呀,不是。瞧我这儿忙着做完祷告好聊天,而你哩,却在睡觉!我们没有盖的,天亮以前准会冻死。”
“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办。”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抱着奶牛。”
“谢谢你。”
“那么你钻进草里去。连这个你都要发牢骚,真是没经过风雨,没见过世面。要是像我前几天那样,全身赤条条的,除开我帮人杀掉的一个家伙的尸体以外,别无任何保暖的东西,在一个霜冻的夜晚躺在战场上,你怎么受得了呢?”
“可怕啊!可怕啊!你跟我详细说说吧!这听起来倒挺有趣。”
“事情是这样的。在布拉邦特我们打了一场小仗,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我们牺牲也大,几个弓弩手呜呼哀哉了,我也算一个。”
“被打死了吗,丹尼斯?得了吧!”
“死得像个猪。我全身满是长矛穿的孔,鲜血直流,就像从踩着的葡萄不断淌出马松红酒那样。我竟然用诗一般的句子来讲这故事,也真是太慷慨了,因为……嗯……我瞌睡来了。嗯……我说到哪儿了?”
“被打死在战场上,像猪一样淌着血,或者说,像葡萄一样淌着液汁。往下讲吧,我求你再往下讲。一个好的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去睡觉,简直是罪过。”
“算你说得对。这个时候呀,几个专门在光荣的战场上剥夺死尸衣物的流浪汉跑来,把我全身脱得精光。他们没继续加害于我,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
“不错。因为你已经死了。”
“当然啦。这想必是黄昏时候的事。夜晚到来以后,出现了严重的霜冻,我伤口上的血凝结了,堵住了从我心口上冒出的涓涓细流。半夜时,我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你以为你是在天上吧?”杰勒德急切地问道,因为这年轻人被灌输过许多修道士讲的故事。
“冻得太厉害,想不到那上面去哩,小伙子。再说,我听见周围都是受伤的人的呻吟声,所以我知道我是在老地方。我晓得,要是没有盖的,我是熬不过这一夜的。我冻得发抖地摸来摸去。最后有个家伙忽然不叫了。‘你已经打发上路了。’我说道。于是,我向他爬去。果然不错,他死了。不过,幸好还有热气。我搂着我的大老爷,但身体太弱,搬他不动。于是,我抱着他滚到近旁一个沟里。清早,我的朋友们发现我躺在沟里,满身被荨麻刺破,搂着一个死了的弗兰德人在苟延残喘。”
杰勒德颤抖着。“这就是战争,这就是诗人和行吟歌手以及演说家喜爱的主题。古人说得好:‘战争使稚气的人神往。’”
“你这样说吗?”
“我说——有些人胆子多壮呀!”
“不是吗,小伙子?所以我说呀,经过了那种……事……之后,这种事就算是天堂了。又软……又暖和……又有好伴、奶牛……别怕……魔鬼……呜!”
接着,那溜滑的舌头便静止了几个小时。
早晨,杰勒德觉得有种液体射到他眼睛上面而惊醒过来。原来是丹尼斯在把奶牛的奶头当做水枪向他喷射。
“啊,去你的!”杰勒德嚷道,“你竟好意思浪费鲜美的牛奶。”说着,他从行囊中取出一个牛角,“把它装满吧,不过,我的确也不晓得我有什么权力动她的奶。”
“你尽管放心!这女伴昨晚不怎么客气。不过,那有什么呢,真正的友谊是用不着客气的。今天我们同样不跟她讲客气。”
“她怎么冒犯你了,可怜的家伙?”
“吃了我的枕头。”
“哈!哈!”
“醒来以后,我不得不找我的脑袋,发现它跌进了牛厩的阴沟里。它吃掉了我们的枕头,我们又从它那儿喝回了我们的枕头。祝你健康,夫人,请别见怪。”说着,这快活的家伙喝着奶牛的奶来祝奶牛身体健康。
“那老汉昨晚说得有理。”杰勒德讲道,“我离开家乡以来,还从来没有起床时感到过这样精神爽快。以后就让我们躲开大城市,睡在修道院或者母牛房里吧,因为我宁肯睡在新割的草上,也不愿睡在六个月以前洗过的床单上,而奶牛的呼吸的确是比基督徒的呼吸更好闻一些,就更不用说那男男女女都喜欢的大蒜味了。这大蒜味奶牛讨厌。圣贝汶作证,我也同样讨厌!”
当兵的从头到脚望了他一眼,说:“要不是你下巴上那一小撮胡子,我就会把你当做一个姑娘。而且,凭着圣路克的指甲发誓,还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
走了三座城市,都是一个类型。步行了许多令人厌倦的里程之后,也看不到它们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即使他们碰不上一座修院或一间奶牛房,杰勒德还是逐渐学会了锻炼自己逆来顺受,并学会了如何仿效他的同伴,因为他认为他的这个同伴在身心强健方面几乎算得上一个超人。
不过,也存在着抵消这一敬重的东西。
杰勒德认为,丹尼斯也像他的先辈阿基里斯那样,有他脆弱的部位,非常脆弱的部位。
他的弱点就是“女人”。
不管他在说什么或做什么,一看见穿裙子的他总会立刻停住,全神贯注于那女性的服装以及那服装遮盖着的人体,直到它们从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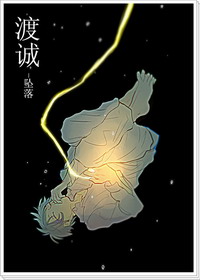
![[主欢乐颂]阿诚的欢乐(悚)之旅[伪装者]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4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