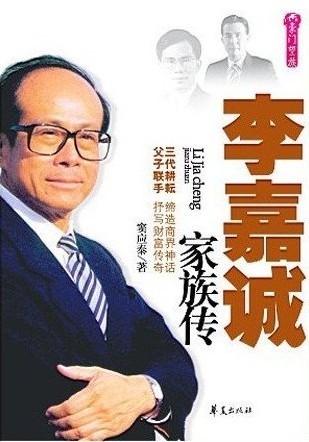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道。
杰勒德脸红了一下。他告诉丹尼斯,这位有学问的医师将给他放血,并用烙铁给他灼烧伤口。如此而已,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啊!原来如此。那边那个小孩在吹煤火干什么?”
“那还用说么!”医师对杰勒德说道,“正是为了在切开静脉,放出有毒血液的时候灼烧静脉呗!这是惟一的安全办法。阿维森纳的确建议过结扎静脉。但如何结扎他没说,而且我相信他自己也不知道。任何一个伊塞玛利的后裔也不知道。至于我,我对这些靠不住的权宜办法毫不相信。你们可以把这句话当做一条可靠的定理:凡是阿拉伯人或阿拉伯派的人说是对的,就一定错。”
“啊,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丹尼斯说道,“难道你头脑这么简单,竟准备让他把烧红的烙铁放在你健康的肌肉上?如果你曾经试过把小指头放在蜡烛里烧十秒钟是什么滋味,那么你尝到的将是长达十分钟的这种滋味。难道死后将在炼狱中受的燃烧还不够你满意?你一定要花钱在这儿先尝尝是个什么滋味?”
“我一点没想到这个。”杰勒德认真地说道,“这好心的医师没说‘烧’,而是说‘灼’。固然这都是一回事,但‘灼’听起来没有‘烧’那么可怕。”
“傻瓜!这是他们的法术,用他们的黑话把普通人搞糊涂,直到好肉被烧得懂懂响才让他明白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现在,你听我讲我见过的事吧。当某个当兵的在战场上受伤流血时,这些行医的说:‘发烧,给他放血!’于是他们两头点蜡烛,把流血过多的人又来个放血。结果发烧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致命的虚弱,因为人需要依靠他全部的血液来维持生命。这些只懂得穿刺和烧灼的人,既无先见之明,又不顾几小时后准会发生的情况,就像野兽那样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点现象,便剥夺了他的伤口给他残留下来抵抗虚弱的血液,终于使他衰竭而死。杰勒德,我看见过数以百计的人就这样被划破和刺破血管而离开了人世,何况还是高大汉子。你瞧,要是他们有幸能在找不到医师的地方受了伤,他们反而能活着。这种事我也见过。要不是幸亏没有外科医生在场,你想,在布拉邦特那一仗中我能活过来吗?霜冻止住了我的伤口流血,所以我才活了过来。假如有个外科医生用刺针在我身上再戳一个洞,放跑我最后一滴血,那就会把我的灵魂也跟着放跑。看到他们发疯似的给流血士兵放血,我就不信他们这些人。不用说,这一连老兵也杀得死的玩意,能轻易地杀死一个靠牛奶和水度日的体弱市民。”
“你讲的倒是合乎常识,”杰勒德没精打采地叹口气说道,“但用不着把你的嗓门提这么高,我又不是生来就是聋子。刚才我都听得十分清楚。”
“常识!好一个常识!”不爱倾听别人说话的医师嚷了起来,“要晓得,这是个当兵的,一个职业在于杀人,而不在于治人的畜牲。”接着他用很勉强的法语补充说道,“你这不学无术的人,如果你要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插手的话,愿你遭到厄运;而你这受蒙蔽的年轻人,如果你听从这个靠洒人鲜血过活的人,那么愿你也遭到厄运。”
“十分感谢,”丹尼斯假装有礼貌地说道,“但我是个老实人,不愿剥夺任何人的名声。我的确是在洒人鲜血方面讨点生活,但在您面前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我每杀死一个,你就要杀死二十个。我每洒一调羹的血,你就会洒一澡盆的血。世界仍然在受骗人的把戏愚弄。我们当兵的耍的是长刀。打仗的时候,我们每杀一个人就得结上两个仇人,而你们这些身穿长袍的伪君子玩的是温柔的语句和小小的放血针。正是你们在使人类日渐稀少。”
“病房可不是开玩笑的场所。”医师叫道。
“对,大夫,但也不是嚎叫的地方。”病人生气地说道。
“得了,年轻人,”那长者客气地说道,“你要放明白些。不管是谁,都应当信赖我的医术。我一生都花在了这门技术上。我是在蒙彼利埃学的医。那是法国,也是全欧的第一所学校。在那儿我学了粪便学、病理学、治疗学,最了不起的是解剖学,因为在那儿,我们这些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门徒,具有那些伟大的古人从来没有过的条件。我们诀别了四足动物、猿猴、异教和穆罕默德教。我们向教堂执事购买尸体;我们摇撼绞架;我们在深夜毁掉教堂丧葬人干的活;我们心中满怀着对科学和人类的热爱。各级官府都得到巴黎的命令,要他们视若无睹!他们便视若无睹。奥林匹斯的神灵啊,他们是怎样视若无睹!那乐善好施的国王亲自帮助我们,每年两次给我们送来被判处死刑的活犯人,并说:‘你们就按科学的需要来处置他好了。如果你们认为合适,满可以对他进行活体解剖。’”
“凭希律王的肝脏和尼禄的肺腑说,要是他再这么赞扬下去,会叫我为那生我的法国脸红。”丹尼斯用最大的嗓门嚷道。
杰勒德尖叫了一声,用指头塞住耳朵,但很快就把指头拿出来,生气地大声嚷道:
“你这大声吼叫、说不干净话的马桑大公牛,快收起你那爱嚷嚷的舌头吧!”
丹尼斯装出一副后悔的样子。
“呸,你这卑微的小人!”那大夫带着一种漠然的轻蔑说道,同时用一只手在他头上摇摇,就像人们今天想使一只猎狗往下冲锋一样;接着他又威严地,滔滔不绝继续往下说,“除在局部地方以外,我们很少或从不对活的犯人进行解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把荒年流行的一些疾病,选择比较感兴趣的接种到这些犯人身上。”
“比较感兴趣的就意味着最危险的。”丹尼斯温和地轻声说道。
“我们观察这些病发展的各个阶段,直至其成熟期。”
“成熟期就意味着这家伙的死亡到来。”丹尼斯又温和地轻声说道。
“好了,我可怜的病人,究竟谁值得你信任?是这个年轻无知而又有偏见的憨里憨气的丘八呢,还是满载着若干世纪积累的智慧的老臾呢?”
“那就是说,”丹尼斯不耐烦地叫道,“你是相信鹦鹉告诉喜鹊,喜鹊告诉(木坚)鸟,(木坚)鸟告诉燕八哥,而身着长袍的燕八哥又告诉另一个身着长袍的穴鸟的话呢,还是相信我这样一个无需通过斜着眼看东西或说假话而有所得的人亲眼所见的事实呢?何况我不是用那对专门用来捉弄我们的耳朵听来的,而是用我那哨兵似的眼睛亲眼看到的。我看到的事实是发烧而被放血的人死亡,但发烧而未被放血的人活着。慢点,到底是谁把这位吸血蛙请来的?是你吗?”
“不是,我原以为是你。”
“都不是。”那大夫解释道,“好心的店主通知我,他店里有个人‘倒下’了。我暗自思量:一个异乡人,需要我的医术。于是我就急忙赶来了。”
“先生,这是善良的基督徒的表现。”
“这是个善良的血犭是的表现。”丹尼斯轻蔑地叫道,“怎么,难道你幼稚到这种程度,竟不知道这些店主都和某些当地公民勾结在一起,而这些家伙每得到一件赃物都要分给他们一份吗?为了盗走你的鲜血,不管你付给这老贼多少钱,那店主都会因为把你出卖给他而分到三分之一的报酬。这还不算,一旦你的鲜血放在那盆里端下楼梯时,店主就会检查它,闻它,并赶忙派人去通知和他合伙的殡葬人,并从那个生意当中又分到他的三分之一。要是他等到医生已走下楼梯,那么医生就会抢在他前面邀约和他自己合伙的殡葬人,从而得到他的那三分之一黑钱。你这老朽的‘红与黑’,我说的是实话吧,快说!”
“丹尼斯,丹尼斯,谁教你把人想得这么坏?”
“是我的眼睛,因为这么多年来,在我所走过的各个国家,我都亲眼看见人们干过这些事。他们说的好话再也蒙骗不了我的眼睛了。”
那大夫机灵地利用这最后两句话来逃避针对他个人的问题。“我也一样和你有眼睛,我办事不仅仅是根据传统,而且是根据我亲眼所见。况且,也不仅仅是根据我亲眼所见,而且是根据我亲身的实践。我通过放血治好过的人数和那抢我生意的阿拉伯派的医生由于不放血而治死的人数不相上下。才不过是前两天,我治好了一个受到麻风病威胁的人。我在他的鼻尖上放了血。去年,我治好一个三日疟。怎么治好的呢?在食指上放血。我们的神父丧失了记忆力,我用放血针的针尖给他恢复了记忆力。我在他耳朵后面放的血。我还给一个患痴呆症的小孩放过血。如今,他是一家的白痴当中惟一能辨别左手和右手的人。几年前这儿闹鼠疫,可不是江湖郎中所说的每隔六年左右闹一次的假鼠疫,而是货真价实的拜占庭鼠疫。我给一个市政官大量放血,并灼烧那些征兆性的横痃,从而把他从坟墓里拉了出来。但当时的那位外科医生,一个危害很大的阿拉伯派分子,不幸自己得了鼠疫。啊哈,他喊着拉泽斯、阿维森纳、穆罕默德,喊着喊着就死去了。而他所喊的这些人,要是能来的话,也会像他自己那样一命呜呼。”
“啊,我可怜的耳朵啊!”杰勒德叹息道。
“难道我如此不幸,连您这样一种仪表和谈吐的人也拒绝我的医术,而听从一个粗鄙的立八?而这丘八甚至如此落后于他自己那倒霉的行业,身上还背着德国小孩用来射鸽子的石弯——自从土炮出现并淘汰了它们之后一直遭到德国兵嘲笑的石弩!”
“你这出言不逊的老江湖骗子!”丹尼斯嚷道,“肩上背弩的人要比那些穿莱茵裤子的人高出一头。甚至现在,弩的杀伤力也远远超过你们那些震耳欲聋的臭炮,正像你那放血针的杀伤力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杀人玩意的总和一样。去你的吧!首先叫你们‘吸血蛙’的那个人真叫得很聪明。吸血鬼,滚!”
杰勒德痛苦地呻吟着:“圣母在上,但愿你们两个都嚷着去见魔鬼。”
“谢谢你,伙伴,我不再叫了。但必要时我会咬的。他有针,我有剑。如果他放你的血,我就放他的血。把话说在前面,只要他的针一戳着你的皮,小家伙,我的剑柄就会捅进他的肋骨。”
这时,丹尼斯脸色发白,两只手交叉在胸前,样子显得阴沉,不好惹。
杰勒德倦怠地叹了口气,说:“既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就让我说一两句吧。”
“对!让这年轻人自己来选择是生还是死好了。”
杰勒德通过对比和自己的模范表现间接地责备他这两个吵吵嚷嚷的顾问。他以无比平静、亲切而温和的态度说话。下面就是杰勒德——伊莱之子的话:“我毫不怀疑你们两人都是想为我好,但你们两人却在共同加害于我。平静和安宁是我最需要的,而你们却嚎叫着,像两只狗争啃一根骨头。说实在的,要是这种吵嚷继续下去,我真会变成一根骨头。”
顿时出现了一片沉寂。而打破这沉寂的仍然是杰勒德银铃般的声音。他安详地躺着,平静地凝视着天花板,慢慢地吐着他的话。
“首先,尊敬的先生,我感谢您跑来看我,不管是基于人道,还是为了诚实地挣钱。反正各行各业都得谋生活。
“您的学识,尊敬的先生,看来是很丰富的,至少我觉得如此。至于您的经验,那么您的年纪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保证。
“您说您曾经给许多人放过血,而在这许多人当中,好些事后并没有死,而是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我不能不相信您。”
那大夫欠了欠身。丹尼斯不满地哼了一声。
“另外一些,您说您也给他们放过血,但是——他们死了。我也不能不相信您。
“丹尼斯比起您来知道的少,但是他知道的东西都很有把握。他是个不喜欢猜测的人。我本人就注意到了这点。他说他曾看见发烧而被放血的人大部分死亡,但发烧而未被放血的人反而活着,我不能不相信他所说的。
“这么说现在一切都成疑问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被放血,我就得付给您治疗费,并遭受烙铁的灼烧和熬煎,而我并没有犯什么重罪。
“对一种没有把握的治疗,用金钱和痛苦付给代价,我是决不干的。
“除开金钱和舒适之外,特别是在一个病房里,平静和安宁也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看来人们争论医学问题不可能不动肝火和提高嗓门。因此,先生,我想试试睡会儿觉。丹尼斯可以出去走走,瞧瞧本地的女性。我也不想再耽搁您,使您不能去诊治那些花得起血和金钱来接受放血和灼烧疗法的人。”
那年老的医师天生脾气暴臊。在这场舌战当中,他曾多次费了老大的劲才把火气压住。但现在火气却控制了他。最能保持尊严的办法是保持沉默,他也知道这点。于是,他站起来,高傲地向门边走去,后面紧跟着提着大篮子的小孩。
但是在门口他憋不住了,膨胀了,爆炸了。他猛一转身,张着嘴巴跑了回来,那小孩和大提篮不得不猛地转上半圈,才幸好没被他撞翻,不过撞翻不撞翻,医生毫不在意——即使不在盛怒的时候也是如此。
“唉!你拒绝我的技术,你藐视我的医道,我不再管你了,算是我的报复。你这无可救药的白痴。瞧我最后一眼,也瞧太阳最后一眼吧。愿你头上冒血!”说罢他便跺着脚往外面走。
但走到门口他又猛地转身跑了回来,他的藤篮子构成的尾巴像猫尾巴那样也跟在他后面溜地一转。
“顶多十二个小时你就会进入第二期高烧,你的头会裂,你的乳突会跳。啊哈!哪怕一根小针落地,你也会跳到天花板上。到那时,你叫人来找我,我可不来咯。”说罢他又往外走。但走到门的把手跟前,火气更旺了,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飞奔过来,那吓得脸色苍白的小孩和藤尾巴急忙迫在他后面。“跟着是——胃部痉挛。啊哈!”
“再就是吐胆汁。啊哈!
“再就是——出冷汗和死亡般的呆滞。
“再就是——感官全部混乱。
“再就是——吐血。
“过了这个阶段就什么也救不了你了,连我也救不了你了。即使我能救,我也不想救。对不起,那就只好说声‘永别了’。”
听到如此暴烈而精细的恐吓,连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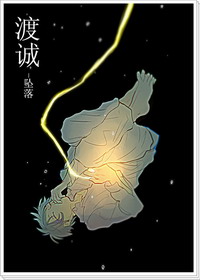
![[主欢乐颂]阿诚的欢乐(悚)之旅[伪装者]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4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