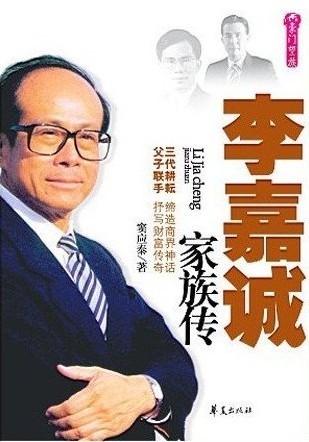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怕冷吧?是想吐吗?是个白痴动不动想哭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他的回答都是一个——英国作家一般译成:Oh!Oh!Oh!(啊!啊!啊!)法国作家一般译成:Hi!Hi!Hi!(唏!唏!唏!)因为,小说里的象声词就是这样死板。
“谁晓得这怪脾气的小崽子得了什么毛病?”那年轻的船夫不耐烦地厉声叫道,“还是瞧瞧这边。看,这些人是来找谁的?”那老人和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一眼就瞧见有四个人在沿着河的东岸走。见到这情况,他们停划了一会,神秘地聚集在船尾耳语起来,时而望望乘客,时而又望望步行的人。
以后发生的事情表明,他们本来最好是把他们的思考用来探索探索萝卜脸的谜。我请求和我同时代的人原谅,我的原意指的是“无畏的孩提的那种深不可测的内心”。
“如果我的怀疑是真的话,”一个年轻人耳语道,“干吗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逃命呢?让我们划到西岸去吧。”
那老人坚决反对。“什么,”他说,“难道叫我们为陌生人受连累吗?你疯了吗?不行,我们最好划到东岸去。和权势人站在一边,这就是我的忠告。维特,你说呢?”
老年和青年决定不了的事,一阵风不偏不倚地决定了下来。这时吹起了一阵狂风,小船倾了过去,人们逃到向风的一面来使它平衡。但他们惊恐地看到整个船上,从船头到船尾有一大股水向避风的一面冲去。转眼之间,他们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感觉到的只是莱茵河水,那寒冷而湍急的莱茵河水。
原来是“萝卜脸”拔掉了栓塞。
那几个军官解开了他们腰部缠着的索子。
杰勒德游起泳来简直像个鸭子。但是,最优秀的游泳能手在船翻掉被抛进水里之后,也要先沉下去才能浮起来。深暗色的水在他头顶上大声地冒着气泡。待他浮上来之后,他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但转瞬之间,他就看见那黑船底朝天,几个人都在紧紧地抓着它。他像只水狗般摇摇头之后,凭着一种不假思索的模仿本能向它游去。但他还没来得及游到船跟前,就听到身后一个喊声,声音虽然不大,却充满了深沉而勇敢的大丈夫才有的痛苦:“永别了,伙计,永别了!”
他一望,看见可怜的丹尼斯被他那倒霉的弓弩压得不断地下。沉。他脸色刷白,两只眼瞪得大大的,绝望地盯着他亲爱的朋友。杰勒德发出一个充满爱与恐怖的野性的叫声,发狂似的劈开浪头向他游去。但转眼之间丹尼斯就没顶了。
顷刻之间,杰勒德已经赶来拉他。
军官们系起一根绳子把一头扔进了水里。
第二十八章
祸与福的相倚相伏是一种耐人寻味而又几乎普遍存在的现象。挂在弓弩手背上、高出头部的钢弩固然使他下沉,但这同一钢弩,正因为它挂在背上的这个位置十分顺手,却又很容易地被杰勒德一手抓住。他一手抓紧弓,另一只手运动于弓和同样管用的索子之问。顿时要代表是塞涅卡(LuciusAnnaeusSeneca,约前4—65)、爱,丹尼斯便被杰勒德利用他自己的弓弩猛地一拉,将半个身子浮出了水面。
“别抓我!别抓我!”杰勒德喊道,极端害怕发生那种要命的事故。
“没有那么蠢。”丹尼斯嘴里灌着水咕噜着说。
杰勒德看到自己对付的是这种好样的角色,马上充满了希望,并镇定下来。“仰卧好。”他厉声说道。接着他一边抓紧弓,一边向前游了一把,帮助丹尼斯完成他所要求的仰卧动作。“手扶着我的肩,另一只手打水!不对——要像这样朝下打。我要你怎么动作就怎么动作。”杰勒德抓住丹尼斯的长发,把它紧紧地扭成一股,并将一端用牙咬住,然后他借助于他那年轻有力的脖子的强壮肌肉,轻松地把那士兵的头保持在水面上,逆着水流使劲游去。他迟疑了片刻,考虑向哪边游,但丝毫没意识到这简单决定的极为重大的意义。他看到西岸稍稍近些,便向西岸游去,而没有像个听话的小孩,乖乖地游向监狱,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情节。
由于水流湍急,他们不得不以一个相当大的角度斜着游向对岸。当他们游了一百码左右时,丹尼斯不安地低声问道:“还有多远?”
“别怕,”杰勒德嘟哝着说,“鸭子会干的,荷兰人也会干。你就像躺在床上一样安全。”
不多一会,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已来到浅水,便涉水而过。一旦脚踏陆地,他们就互相从头到脚望着对方,仿佛想用眼睛把对方吞噬下去。随着一阵冲动,彼此又用一只胳膊搂住对方的脖子,一面喘着气,一面百感交集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这神圣的时刻,生命对于两人来说真是天堂般的美妙。而对于那救了朋友的生命却因爱情而被迫离乡背井的杰勒德来说,更是美妙无比。啊,欢乐!有哪个诗人曾经飞翔到或者尝试飞翔到这样的高度?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何况是所爱的一个人的生命!这种时刻才真是值得一活,哪怕活他七十年。心情稍稍平静之后,他们便拉起手,像对情侣似的沿着河岸走去,不晓得也不在乎他们将往何处去。
船夫都平安地坐在那先前四着而现在凸着的船上。萝卜脸先生,这“颠倒事物的祸首”,坐在中间。这一阵纷扰似乎基本上并没有打乱他的习惯。至少,当他把我们的朋友抛进莱茵河时,人们看见他在欢呼;而当他们逃出莱茵河时,人们也看见他同样在欢呼。
“我们要不要等他们把船弄正过来?”
“不用了,丹尼斯。船费已经付了,我们不欠他们什么。让我们往前走吧,快快走吧。”丹尼斯表示赞同,并指出他们可以沿这河岸一直走到科隆。
“我不打算去科隆。”他得到冷静的回答。
“嘿,那么你要到哪儿去呢?”
“到勃艮第去。”
“到勃艮第?唉,不可能,这太好了,简直不能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是真话,而且还很有道理。去罗马走哪条路对我有什么要紧呢?”
“不,不,你不过是说说使我开心而已。这改变太突然了。别以为我心肠这么不好,竟会把你的话当真。再说,难道我没看见你在谈到科隆的名胜时眼睛炯炯发光吗?那些教堂、塑像、圣骨——”
“你多傻呀,丹尼斯,那是因为想到我们会一道去欣赏它们嘛。教堂!不管我走哪条路去罗马,我都会看到好多教堂。圣徒和殉道者的遗骨?哎!世界上有的是。但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在地球上哪儿还能找到第二个呢?我不想使你从通往你亲爱的家乡和盼望你的姑娘的归路上偏离更远,但我也不想离开你而使我失去你。自从我把你从莱茵河救出来,我比以前更加喜爱你。你是我的珍珠,我把你捞了上来,我就必须保有你。别再不顺着我了,不然你会使我又发烧的。你还是喊起你‘别怕’的口头禅,领着往前走吧。嘿,目标勃艮第,前进!”
丹尼斯高兴得跳了起来。“鼓起勇气!向勃艮第前进!啊,你放心!那鬼东西这回肯定是呜呼了。”于是他们转过身来,离开莱茵河向远方走去。
当这个决定明朗化之后,在莱茵河彼岸一直在注视这一讨论的一小伙人便蠢蠢欲动。两个朋友刚迈出几步,就听到从河那边传来一个喊声:“站住!”
杰勒德转过身来,看见那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伸出一个官方的标志以及一张羊皮纸。他的心往下一沉,因为他素来是一个好公民,习惯于服从此刻命令他返回杜塞尔多夫的声音——法律的声音。
丹尼斯并不赞同他的谨小慎微。他是一个法国人,因此他藐视任何别的国家,包括它们的法律、居民以及风俗习惯。他也是个当兵的,因此他对情况作了一个军事上的估计:面对着较强的敌人,中间隔着条河,后方开阔,退却很容易。他一眼看出那船还飘在河中间,至少要到杜塞尔多夫才有别的渡船。“我将退到那小山上,”他说道,“一避开他们的视线就快步跑。”
他们散步似的继续走着。
“站住!以知事的名义命令你们站住!”
丹尼斯转过身来,故意弹响指头对知事表示轻蔑,并继续往前走。
“站住!以大主教的名义命令你们站住!”
丹尼斯又弹响指头对大主教阁下表示轻蔑,并继续往前走。
“站住!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命令你们站住!”
丹尼斯又弹响指头对皇帝陛下表示轻蔑,并继续往前走。
杰勒德遗憾地看着这无益的哑剧表演,一当他们翻过小山的坡顶之后,便说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必须以跑步代替慢走奔往勃艮第。”说着两人便跑了起来,一气跑了大半个里格才停下。
丹尼斯跑得喘不过气,问杰勒德他发烧的病跑到哪儿去了“我开始为你病好感到十分惋惜。”他冷冷地讲道。
“我想,我是把病扔进了莱茵河。”杰勒德回答道。
他们很快来到一个小小的村庄。丹尼斯买了一大块面包和一大瓶莱茵白酒。“因为,”他说,“我们得睡在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里。如果我们歇店,准会在床上被抓住。”当然,这不过是老兵身上一点普通的警惕性。
在当时那个时代,搜捕违法者,特别是属于平民阶层的违法者的法网是非常严密的。不过公众提供的合作几乎等于零,至少在欧洲大陆情况如此。关于旅客的往来情况,店主们到处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对旅客的行为所负的责任看来甚至超过他们对旅客的疾苦所负的责任。
太阳下山了,两个朋友都感到高兴。在星光下(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月亮要到早晨三点才会升起)长途跋涉之后,他们愉快地来到属于不远处的一户人家的谷场。他们最近打了好些大麦,在打麦场一边堆的草和另一边堆的没打过的麦子几乎一般高。
“这儿有两张顶呱呱的床。”丹尼斯说道,“我们躺哪张床好,麦子床呢,还是麦草床?”
“让我们躺麦草床吧。”杰勒德说道。
他们坐在麦草堆上,吃着黑面包,喝着酒。然后,丹尼斯用草把他的朋友盖起来,草堆得高高的,只给他留下一个出气孔。“人们说,潮湿对发烧的人是要命的。不过,我要把湿气弄得暖和一些。”
杰勒德要他放心。“莱茵河的这几滴水不可能使我着凉。我现在感到体内有足够的热量烧焦一个狗窝,或者,要是我在一片云彩里的话,把云里的水烧开。”说完这句俏皮话之后,他很快就失去了知觉,也许真可以说是“掉进了睡多”。
丹尼斯睁着眼睛只躺了一会儿,便听到了使得他把身子蜷伏得更紧的某种动静。从杜塞尔多夫的方向传来了马蹄声。当马蹄伴随着十五世纪人们所熟悉和了解的,但现时在欧洲已像印第安人的喊杀声一样变得陌生了的嚎叫“得得”跑过的时候,谷仓都在震动。
丹尼斯在他躺着的麦堆上发抖。
杰勒德酣睡得像个陀螺。
这一切都像阵风似的刮了过去,马队和呼啸声消失在远方。
那勇敢的士兵深深地吸了口气,轻声地吹了阵口哨,便合上他的眼睛,作为第二号陀螺酣然睡去。
早晨,他坐了起来,想伸出手去摇醒杰勒德。他的手落在那年轻人的额头上,发觉它完全湿了。既然充当他的临时护士,自然不忍心把他叫醒。“打断一个病人的睡眠,或止住他的汗是要不得的。”他说道。
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之后,他感到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回转身来,为了自我保存,重新睡上一觉。
可怜的丘八,在他艰苦的一生中经常被迫采用这一权宜之计。正午时,他被动弹起来的杰勒德弄醒,看到他已经坐了起来,麦草像粪堆一样在他周围冒气。这是动物体温对抗潮湿的结果。杰勒德喊他“懒鬼”,他只是默默地露着牙齿微笑。
他们开始出发。丹尼斯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弓弩让杰勒德拿着,爬上路边一棵很高的树。“到下一个村的的路很安全。”他说道。两人便向前走去。
快进村的时候,丹尼斯停了下来,突然问杰勒德感觉怎样。
“怎么!难道你看不见吗?我感觉罗马就像那个村落一样近在眼前。”
“小伙子呀,你的身体呢?你的皮肤呢?”
“不冷也不热,昨天是一阵冷一阵热。但现在还缠着我的是这只讨厌的腿。”
“这可是大大的不幸,我的许多朋友从来没感到过这种困难。”
“唉!又来了,痒得不可开交。”
“倒霉的年轻人,”丹尼斯认真地说道,“你的毛病总的说来是烧退了,伤口也正在愈合。既然如此,”他疼爱地说道,“那么我要告诉你一个要不然我不会告诉你的消息。”
“什么消息?”杰勒德眼里闪耀着好奇的光芒问道。
“正在通缉我们,而且是由轻骑兵来执行通缉令。”
“啊!”
第二十九章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杰勒德感到一阵眩晕,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接着他愤怒地咬紧牙齿。稍有勇气的人都会有野猪一样的表现,大概困为野猪并不是蠢驴。在看到优势力量时新工具原名《新工具或解释自然的一些指导》。英国弗兰,野猎也会躲开:但如果你跟踪它太紧,太长久,总之,如果你使它烦了,它就会猛地转过身来,朝一大堆猎人扑过去,说不定还会把你撞翻。这时的杰勒德正牙关紧闭,露出打算决一死战的神情。但他马上就脸色一沉,惋惜地说道:“我的斧子掉在莱茵河里了。”
他们在一起商量。“谨慎”叫他们避开村庄,“饥饿”却说“该购买食物”。
“饥饿”最雄辩,而“谨慎”则最有说服力。最后,他们决定从田野上抄过去。
他们在一个草垛跟前停下来,借用它两捆草,把草拿进一条不会被人看见的干沟渠里。两人躺着草上,周围尽是尊麻。
他们轮流冲出去,带着萝卜回来。就这样,一边隐蔽,一边啃萝卜,一直消磨到傍晚。
他们很快又哆嗦着爬了出来。外面又黑又下着雨,他们从村庄的另一边上了路。
这是一个阴沉的夜晚。一片漆黑,风吹得很厉害。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但别人也看不见他们,听不见他们。就我所知,他们是从搜捕他们的敌人旁边像鬼魂一样溜过去的。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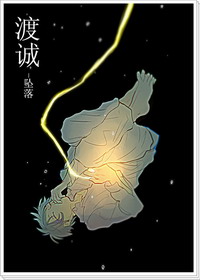
![[主欢乐颂]阿诚的欢乐(悚)之旅[伪装者]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4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