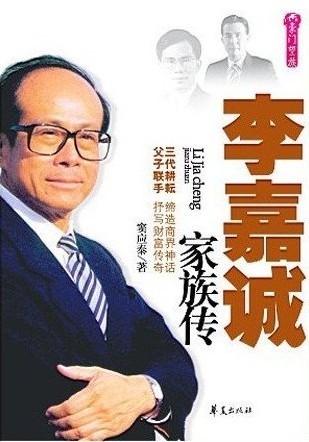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是神父们做祷告的地方。”杰勒德说道。
“并不经常如此。”丹尼斯说道,“地窖里燃着成打的蜡烛,摆着王侯才能享用的佳肴:十五份有鹿肉、松鸡和免肉鲜味的清汤,以高超的烹调技术做出的二十种不同的鱼(因为是礼拜五)。每两个健美的大姑娘中间都夹着一个男人,而每两个头带风帽的小伙子中间都夹着一个姑娘。只有我是例外。想想看,我得通过翻译来求爱。我疑心那家伙每替我说一句情话就替自己说上三句。要是他没这么于,你满可以把他当傻瓜吊死。有几个柔弱的女性是新手,不习惯喝美酒,先得哄哄她们,才肯把酒放到她们洁白的牙齿跟前。但是她们一学就会。他们轮流讲故事,说笑话,传酒杯(顺便说说,他们叫人把方酒瓶都做成祈祷书的样子人一个修士弹着七弦琴,用春天黄莺般动听的声音唱着小调。那些诗句起先确使姑娘们脸孔变得绯红,但她们很快就习惯了。”听到这儿,杰勒德气得要爆炸。
“可鄙的家伙!毒化青春的无赖!败坏童心的恶棍!要不是你丹尼斯在场,又因为你丹尼斯没受过更好的教育,但愿教堂倒塌在这帮人身上。不敬神的可恶的伪君子!”
“伪君子!”丹尼斯带着全非矫饰的惊奇叫道,“瞧,这正是我没了解他们之前给他们的称呼,可你原先不赞成。不错,他们是有罪过的人。所有好人都有罪过。不过,凭圣丹尼斯戴盔的头骨说,他们不是伪君子,而是真正快活的爱闹嚷的浪荡子。”
“丹尼斯,”杰勒德严肃地说道,“你一点没想到那晚你冒的危险。你们伙在一起糟蹋了的那个教堂经常闹鬼。我是从一位年老的修士那儿听来的。死人在里面走路。有人听见他们轻轻的脚步声在石板上‘啪啪’地走过。”
“天哪!”丹尼斯轻声说道。
“这还不算,”杰勒德把声音几乎压低到耳语声大小说道,“从被你们变成餐厅的地窖里曾经传出上界的声音。死者神秘聚会的声音会使听见的人半夜三更不寒而栗。丹尼斯,信徒们在夜晚醒着的时候,有时会听见死人嘴里发出音乐声。在神圣的地窖深处埋葬着的死人中间,会像一阵阵回音似的模糊地鸣响着凡人的手指弹奏不出来的旋律。”
丹尼斯露出一副惊惧的面容。“哼!要是我早知道的话,骡子加绞车索也不可能把我拖到那儿去。那么,”他叹了口气,“我就失去了一次享福的机会。”
是否进一步的探讨会使那鬼魂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说明,谁也说不上。这时一个“一脸胡须”的师兄骑着他的骡子,手上挥动着一张羊皮纸从修院跑来。这是盖斯布雷克特和弗洛里斯·布兰特之间订立的那张契据。杰勒德把它看做是对故乡的纪念而十分珍惜。想起他差点丢失了这张契据,杰勒德不兔脸色苍白起来。丹尼斯感到非常有趣的是,他不但给了那几俗的师兄一枚钱币,而且给了那骡子鼻子一个吻。
“现在我可要读读你了,”杰勒德说道,“即便你写得比这糟糕双倍,但——为了保证永远不丢失你……”说着他坐了下来,取出针线,用女性般的巧手把它缝在他的紧身衣上。他的心灵和灵魂都回到了塞温贝尔根。
他们来到了被许诺的福地。兴高采烈的丹尼斯对所有的妇女都脱帽致意,她们也行屈膝礼或者微笑作为回礼。他对大多数男人都一个劲地猛说他的口头禅。听到这个口头禅,有些人眼睛一愣,有些人露出牙齿笑笑,有些则两种表情兼而有之。最后,他把他的朋友安置在一个许诺已久的勃艮第旅店。
“这是家小旅店,”他说道,“但我打从过去就知道这是家好样的,叫三鱼旅店。那儿写的是什么?我认不出。”他指着横贯整个楼房的用大的法文字母写的一行字。“啊,我知道了,“此处留宿徒步旅客或骑马旅客’。”丹尼斯一边仔细地读着一边说道,然后显出非常神气的样子。
杰勒德也去看,但上面那个句子实际上写的是:
此处不能赊欠留宿。此种老实人已不复存在,亏账不还者已将其害死。
第三十三章
他们在走道上碰到了店主。
“欢迎,先生们。”他一边脱帽鞠躬,一边说道。
“行了,我们已经离开德国了。”
在来宾室他们见到了女店主,一个长得很丰满的四十岁妇女。她对他们行屈膝礼,并露出十分热诚的微笑。“劳驾请坐,高雅的先生。”她对杰勒德说道,并用围裙掸掸两张椅子。不过他们并不想坐。
“谢谢您,太太。”杰勒德说道。“好呀,”他想,“这真是一个有礼貌的国家。劳驾请坐?这我准会以少有的耐心劳这个驾。但很快就会劳驾吃饭,劳驾消化,最后,还得借助于赫克里士的帮助,劳驾上床,劳驾酣然入睡了!”
“嘿,丹尼斯,你在干吗?只给我们两个人订晚餐吗?”
“干吗不呢?”
“怎么,用不着等四十个人才可以开晚饭?勃艮第万岁!”
“啊哈!别怕,伙计,魔——”
“这不用说。”
萨利克法律似乎还没有深入到法国的旅店。至少在这个旅店里,戴女头巾帽和穿女上衣的还占支配地位。穿紧身上衣和马裤的人不多,行动也软弱。店主本人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老是没头没脑地向人们脱帽。妇女们从他身边走过时,就像匆忙穿过树林时移开一根活树枝那样,不屑一顾地把他悄悄推向一边。
一个侍女端来了晚餐,女店主空着手跟在她后面。
“快请,先生们,”她兴致勃勃地说道,“您如今只有一个敌人,它就躺在您的刀下。”(我自以为机灵地猜测,这准是一种公式化的语言。)
他们动手吃饭。女店主把她的椅子朝他们的桌子移了移。除开膳食以外,还提供陪伴服务。她像老相识那样和蔼可亲地同他们聊天。当这个礼节完毕之后,那忙碌的太太便很快走开,把她的女儿,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丽少女,送进来占据空了的座位。她倒不像年长的母亲那样开朗可亲,然而文雅而活泼。当她知道杰勒德走了多远的路来到这儿,还将走多远的路去罗马时,便对这可怜的小伙子立刻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和关心。她呆了大约半个小时。她走后杰勒德说道:“这是旅店吗?嘿,简直像个家。”
“谁按法国方式行事,谁就彬彬有礼。”丹尼斯充满了自豪感,高兴地说道。
“彬彬有礼?不,这是基督之道。把我们这些今天来明天走的漂泊者作为家里的客人来欢迎,这正是基督之道。说实在的,谁又比远离家人的疲惫的旅客更值得怜悯和同情呢?嘿,又来了一个。”
新来的是侍女,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女人,长着翘鼻子、一张笑着的大嘴和一双闪闪发光的黑眼睛。袒露着的手臂长得很结实,但不很标致。
她一进来,一个旅客就颇为随便地拿她开了个玩笑。但不多一会满屋的客人便对那人哄堂大笑,因为她那久经锻炼的舌头很快就打发了他的挑逗。这正像一个新手和一个击剑师进行击剑比赛一样,剑一相碰,新手就被戳着了。在眼下这个场合,一个接一个的新手都想和她较量一番。只见马莉昂将两只大胳膊叉在腰间,把满屋子的人都玩得团团转。这位农村姑娘所具有的粗野而灵利的俏皮和幽默达到了完美的地步。这种幽默写在纸上会显得鄙俗,但说出来却无往而不胜。它不是机智的铜剑,而是机智的木棍。天资在这方面给了她很大的帮助,而每天在旅店的训练则补充了天资遗留的不足。
但我将不给她拍照,而只是粗略地给她勾个轮廓,因为这是四百年前的事。打趣她的俏皮话是粗鲁的,而她都针锋相对地一一予以回击。虽然她是个不乱来的女人,但可以不眨眼地说些我们今天的正派男人即使在男人中间也说不出口的东西。
杰勒德目瞪口呆地坐着。这对于他说来几乎是那“有趣的动物学类别”,即人类的一个新品种。他对丹尼斯耳语道:“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你们法国人说‘妇人的舌头就是她的宝剑’。”这时她正好打倒了一个进犯者。骑士般的丹尼斯,为了慰劳和支援“柔弱之器的女性”——其实是士罐子中间的铁茶壶,又使出他的口头禅,“别怕,我的女友,那……”等等,等等。
她马上转过身来冲着他说:“只要有一个弓箭手还活着,魔鬼怎么可能呜呼呢?”(这时满屋的人都以她的同盟者为对象大笑起来。)
“今天是洗衣服的日子,先生们。”她突然严肃地说道。
“改天好吗?我们旅客不能在你们洗我们衣服的时候赤身裸体呀。”一个坐在火边的怪脾气的老家伙反对道。这人在别人打趣的时候默不作声,现在才爬进众人欢畅的阳光中来。
“我不是针对你说的,老古板,”马莉昂高傲地说道,“但既然你问我,”说着她从头到脚慢慢地打量了他一番,“那么,我想你满可以连人带衣一起在澡盆里打个滚,没有坏处。”(笑声)“但我原先想讲的是,我认为——这位年轻的大人先生——可能会愿意把他的胡子浆浆硬。”
现在轮到可怜的杰勒德了,因为他下巴上长的“庄稼”很稀,而且丝一般柔细。
这时,在哄笑的人当中声音笑得最响的要算是背叛朋友的丹尼斯了,因为他的胡子很长,而且硬挺得出奇,以致莎士比亚——虽然从未见过他——都说到了他的点子上:
“满嘴奇怪的咒语,胡须长得像个豹子。”
——《皆大欢喜》
杰勒德毫不在意地承受这好斗女性的讽刺。他没有什么讲求漂亮的虚荣心。“不要说我了,侍女小姐,”他微笑着说道,“我的胡子是不值得你操心。请你照管照管这个势头很旺的‘庄稼’吧!”说着他指向丹尼斯的“须状植物”。
“当我要浆浆长扫帚的时候,再照管它也不迟。”
当人们对这毫不含糊又一语中的的俏皮话又笑又喊的时候,女店主走了回来。她还没来得及跨过门坎,我们的亚马孙女英雄已变成了一个貌似温良而柔顺的假圣母。
女店主们都是了不起的制伏人的好手。像她们那样的,我看世上少有。侍女们,悉听尊便吧!不过这只是浪费表演技巧,因为女店主早已听见,而且心里也并非不喜欢这一串串的笑声。
“唉,马莉昂姑娘,”她情绪很好地说道,“如果你每格格笑一次就给我下个蛋,那么,三鱼旅店就永远不缺煎鸡蛋的油了。”
“太太,”杰勒德说道,“该付多少钱?”
“付什么钱?”
“付我们的晚饭钱。”
“忙什么?难道等你们走的时候再付不行吗?旅客走时才付钱,这是‘三鱼’的规矩。”
“不过,太太,‘三鱼’的墙上写的可是:‘此处不能……’”
“去它的!让那跳蚤钉在墙上,别管它。瞧这儿!”说罢她指着布满象形文字、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这些赊的账,俗话说画的“道道”,只有这位太太和她女儿才懂得。母女二人只需在必要时登上一个小方凳,用刀子在天花板上堆积的黑烟上刮刮,就可以画出一些道道。太太解释说墙上写的大字是用来吓退穷光蛋的,或者偶尔有个想赖账的面孔撞进来强行要求住宿时,作为对付他的依据的。“您知道,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他们,因为法律不准许我们这样做。”
“您怎么知道我的面孔不会赖账呢?”
“啊,这还用说,这是今年秋天走进‘三鱼’的最善良的面孔。”
“我的呢,太太?”丹尼斯说道,“您没在我的面孔上看到赖账的样子吧?”
她从容地望着他。“不像这小伙子的面孔这样善良,也永远不会这样善良,不过倒是个老实人的面孔。尽管如此,”她淡漠地补充道,“要是我比现在年轻十岁,我是不愿在漆黑的夜晚在离家太远的地方碰到这样一张面孔的。”
杰勒德发愣地望着,丹尼斯却大笑起来。“嘿,太太,我只消把夜露从花上吸掉,您就用不着减掉十岁,甚至减掉一天,而值得为您冒冒被抓破脸的危险了。”
“瞧,女主人,”马莉昂刚一进屋就说,“我不是前两天还说过,如果您有心的话,您还可以使他们神魂颠倒吗?”
“我敢说你是说过的。一听起来就像个傻丫头讲的话。”
“太太,”杰勒德说道,“这太奇怪了。”
“什么?啊,不,不,这一点不奇怪。要知道,我在这儿呆了一辈子。一个姑娘在旅店里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相。”
马莉昂:“第二件就是煎鸡蛋。不,第二件是说谎,但第三件就是煎鸡蛋了。”
女主人:“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件就是学会住嘴;而害羞么,过了一天就再也学不会了。”
马莉昂:“哎呀!又说起我的舌头来了。我什么也不讲了。我生活在女主人的翼下,而女主人却打击起我来了。我完了——我这个侍女完了。捞一把剩下的油水吧。”于是她摇摇晃晃地往后倒,一头栽在屋里长得最漂亮的人身上,而这人恰好是杰勒德。
“去!去!”他生气地叫道,“得了,别装疯卖傻了!这对我可是个太过分的玩笑。你没见我在跟女主人谈话吗?”
马莉昂做出一个鬼脸,恢复了她的弹性,轻轻地一两跳便蹦到地板的中央,然后做了个足尖旋转舞的动作。“你瞧,女主人,”她说道,“我认输了,您对男人,至少对小男孩还是最有权威。”
“年轻人,”女主人说道,“这姑娘并不像她的举动所表现的那样愚蠢。在看相和煎鸡蛋方面,我们是了不起的。如果在这些技术方面我们不行,那就不好办了,因为这些大致就是我们惟一能干的事。”
“您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太太。”杰勒德说道,“您有经验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一个人的面孔里呼之欲出的老实气,这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您如何只消望望丹尼斯,就知道他的毛病、他的痴愚。他的骡里尔罗斯蒂呢?”可怜的杰勒德越想越生气。
“他的骡——他的什么?”(她带着一种迷信的敬畏感对这一多音节字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别这样,这只不过是我一时高兴为他发明的一个字眼。”
“发明?怎么!像你这样一个娃娃也可以创造不是勃艮第土生土长的字眼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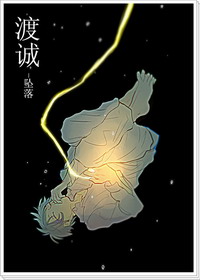
![[主欢乐颂]阿诚的欢乐(悚)之旅[伪装者]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4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