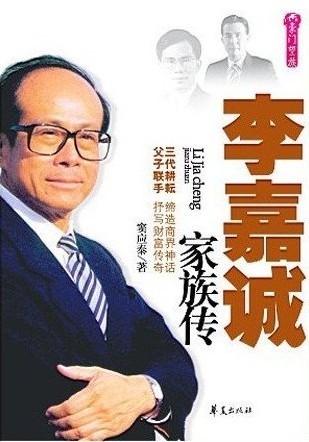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杰勒德做了一个假装要捅的状态,但马上用两只胳脯搂住他的脖子。“你这个大傻瓜!除开这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捅向你的心肝。”
丹尼斯惊叹了一声,然后热情地拥抱他。被这一青春的激情和内在美的突然表现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丹尼斯,以断断续续的声音激动地说道:“你讥笑女人——但你的一些——可爱的性格——就像女人。在你身上还保留着你母亲的乳香。连撒旦也会爱你,要不然——善良的上帝就会因为他羞辱地狱而把他踢出地狱。把你的手伸给我!把你的手伸给我!要是在到达意大利之前我让你离开我一步,愿——”接着是句可怕的赌咒。
在闹了短短的别扭之后,两个忠诚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远不止和解了。
第二天,几个强盗受审。由于受害者的遗骨已经埋葬,罪证数目减少,那小小的市政秘书感到非常气恼。不过罪证仍然颇为可观:匪徒当场被斩断的一只手、一位被谋害的妇女的头发、院长的斧子以及其他作案的凶器、头骨等等东西,这些都由发现它们的衙役宣誓作了证。在当时那个时代和地区,罪状的查证不是那么严的。全部匪徒都供认不讳,只有店主例外。于是曼侬被传来对质,使他无法抵赖罪状。她提供的证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店主妄图通过从她口里引出她自己的情人曾是匪帮的一员,而且他活着时她一直毫不声张这一事实,来动摇人们对她的口供的信任。但是,检察官出来帮助他的证人。他引证说,这是因为刀子对准着她的喉咙,同时她的情人严肃赌咒,要是她出卖他,他就要杀死她。正是这种可怕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怕死,才封住了她的口。
别的匪徒都被判处绞刑,惟独店主被判处车刑。他听到对自己的宣判时,立即发出了一声惨叫。
至于说可怜的曼侬,她马上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舆论也并不完全对她有利。总的说来,分为两大派。说也奇怪,大多数妇女都站在她一边,而男人则均分两方。这可以说是百年难遇的怪事。也许某位女士能解释这一现象。至于我,则有点害怕解释我所不理解的现象。这已经不足为奇了。话说回来,要是曼侬是个喜欢出野风头的人,那么她该感到高兴,因为她已成了全城的话题。然而,这可怜的姑娘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躲避追随她的人群,把自己的头藏在某个地方,好为她“吊死的情郎”痛哭一场——因为眼前的这一切都使她对死者产生了鲜明而深情的回忆。在他被处绞刑之前,他曾恫吓过要杀死她。但她并不属于那种习惯于挑剔的女性,仅因为男人想打她们,踢她们,想杀她们,而对她们奉若神明的男人的爱情有所减弱。相反,只要上述的“关照”伴以偶尔的抚慰,爱情不但不会稍减,反而弥坚。所以说,要是她仅因为这一类恫吓就耿耿于怀,那才真是怪事。毕竟他从来没有用情敌来对她进行恫吓。正因为如此,她哭得十分钟情,十分伤心。
与此同时,旅店充满了渴望见她一面的人。他们饮酒作乐消磨时间,等待她能屈尊露面。她哭了一些时间,便听到一阵叩门声,原来是店主带着一个建议走了进来。“别哭了,好姑娘,只要你愿意,你马上就会走运。只要你说同意,你就可以当上‘白鹿’的侍女。”
“不,不,”曼侬感到一阵新的悲伤,“我决不再在旅店当仆役了,我要回我妈那儿去。”
店主安慰她,哄劝她。她平静了一些,但仍然坚决拒绝他的建议。
店主走开了,但过不多久又走了回来,向她提出另一个建议,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妻子,“白鹿”的女店主。
“你真缺德,还来取笑我。”她痛苦地说道。
“不,亲爱的,我不是取笑你。我这么大年纪了,不会再开无聊的玩笑。只要你同意,你就是我同甘共苦的伴侣。”
她望望他,看得出他是当真的。这时,为了悼念她那“吊死的情郎”,她突然泪如雨下。由于是最后的一阵,颇有倾盆之势。然后她向“白鹿”的店主伸出了许婚的手,并和他共分一个金币作为订婚纪念。
“店里静下来之前,我们要保守秘密。”店主说道。
“对。”她说道,“但在这段时间,请你给我点亚麻布来织织边,或者别的什么活计做做,因为我感到时间像铅块一样沉重难熬。”
她的未婚夫对这一主妇味道的请求马上眼睛炯炯发光。他给她拿来两打大小不一的酒瓶来擦洗。
当她想到由于一种奇异的命运转折,所有这些明亮的锡器都将属于她时,她不由得感到沾沾自喜。
与此同时,店主走下楼去,碰到我们那两位朋友。他把他们拉到旁边的酒吧间去。
接着,他相当严肃地对丹尼斯说:“我们都是老相识了,而且你人也蛮聪明,现在我遇到一个难题,请你当当参谋。我的顾客有点儿减少的趋势。这个曼侬姑娘已成了全城的话题。你瞧今晚客店多么拥挤。她已经拒绝做客店的侍女。我颇有心娶她,你以为如何?我该提出求婚吗?”
丹尼斯只能以瞠目结舌的惊奇作为回答。
店主半征求意见似的转向杰勒德。
“不,先生,”杰勒德说道,“我还太年轻,不能给比我年长。更有身分的人当参谋。”
“没关系,让我听听你的意见。”
“好吧,先生。关于良妻,古人有话说:‘bene quae latuit,bene vixit.’意思是说:毋为人所议论者,贤妻也。不过,‘male quae patuit’也同样说得很中肯。因此,如果你对那姑娘怀有善意的话,干吗不与丹尼斯和我合伙出钱送给她一套嫁妆,送她平安回家呢?说不定她家乡有某个村夫愿意娶她为妻。”
“干吗这么啰唆呢?”丹尼斯说道,“这老狐狸并不像他装佯的那样是个笨驴。”
“噢,这就是你的高见,是吗?”店主生气地说道,“那好吧,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是傻瓜,是你还是我,因为我恰好已经和她谈过,而且她已经表示同意。此时此刻,她已经在擦洗酒瓶。”
“啊啦!”丹尼斯冷漠地说,“原来是打的埋伏。那么,好吧,我的建议是:赶快去找一个公证人,做好准备,让我们三个为新娘的健康干杯,直到我们看见六个酒鬼喝得醉醺醺为止。”
“就这么办吧。现在你算是说人话了。”
还不到十分钟,就当着一位公证人和他的秘书以及我们两位朋友的面,在楼上举行了一个文明婚礼。
再过十分钟,那母白鹿感到闭门不出腻得慌,便在酒吧间里坐上了自己主妇的交椅,开始斟酒忙碌起来,面孔也略带点红晕。
又过了六分钟,她便大骂起一个侍女来,说她不该把一个小酒壶拿歪,把好生生的酒溅洒在地上。
晚间,她又隔着柜台接待了八个求婚者,其中有几个还是地位颇高的市民。这时,店主和我们两位朋友正满有意思地坐在屏风后面,惬意地为新婚夫妇的健康祝酒。上述喜剧不过是被慷慨的命运之神插进来供他们消遣而已。他们听到那一个接一个的求婚,以及缺乏想像力的曼侬千篇一律的回答:“好心人,您来得太晚了。”店主带着一种没有恶意的优越感望着两个先前的顾问,微微一笑,似乎在笑他们的传统观念:男人应当回避“出风头的”,也就是成为街谈巷议话题的任何女人。
不过,丹尼斯几乎没有注意到新郎因战胜他而感到的骄傲,因为他正专注于他自己战胜杰勒德所感到的喜悦。每当一个市民来供献他那忠贞不渝的爱情时,他都使劲忍住,憋得面孔发紫,才没有得意地大笑起来。他一边用肘部捅捅那沉思着的、困惑不解的“古代学者”,一边耳语道:“男人才分文不值。”
第二天早晨,杰勒德急于启程。然而,丹尼斯发誓要亲眼看到那杀害金发少女的凶手被处决。
杰勒德尊重他的誓言,但回避效法他这个榜样。
他到神父那儿去告辞,谋求并获得了他的祝福。中午时分,两位旅伴走出了城门。在南门外,他们从绞架旁走过。绞架上有八具尸体,其中一个已成为骷髅的是曼侬最近还在为之痛哭,而现在正很快置于脑后的情人。其他几具就是差点夺走我们这两个旅伴生命的匪徒。有一只手被钉在横柱上。近旁是一个巨大的轮子,上面卡着那个呜呼了的店老板,身上的骨头都绞得粉碎。
杰勒德转过头,匆匆地走过去。丹尼斯却走走停停,对他死去的仇敌表示胜利的喜悦。“那时我们两人冷得发抖,等待你们七个来割我们喉咙。现在情况不同了,伙计们。”
“去你的,丹尼斯!人一死,旧账全销。要是你对我有丝毫尊重的话,求你别再啰唆,往前走吧。”
丹尼斯听从了这一严肃的劝告。他甚至沉思般地说道:“你比我更有教养。”
下午三时左右,他们来到一个小市镇,看见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在嗡嗡地议论。原来是狼群为饥寒所迫进了城,前晚在大街上吃了两个成年人。于是,有的在责怪被吃的人,“只有傻瓜和无赖才在黄昏之后到处跑”,另一些则责怪法律没有保护市镇居民,还有一些则责怪市政府没有贯彻实施现有的法律。
“去你的!这跟我们没关系。”丹尼斯说道,主张重新上路。
“不,这和我们有关系。”杰勒德反驳道。
“怎么,难道我们是被吃掉的一对吗?”
“不,但我们很可能是下一对。”
“对,街坊,”一个老年人说道,“这是市里没按公爵命令行事的过错。公爵的命令是叫每个店主黄昏时在门口点盏灯,一直点到天亮。”
听到这一说,丹尼斯略带讥讽地问道:“他根据什么设想灯芯草蜡烛能吓走饿狼呢?要晓得,羊脂正是它们最喜欢的。”
“狼怕的不是油脂,牛皮大王,而是亮光。所有邪恶的东西都恨亮光,特别是狼和那些在毛皮底下潜藏着的魔鬼。比方说吧,巴黎城位于一个森林般的地方,狼群整夜在周围嗥叫。但近年来狼群很少上街。为什么呢?就因为在那城市巡夜的,一看到没点灯的门,就狠狠地捶个不停,使得睡觉的人都爬起来点灯。这是我儿子告诉我的。我儿子尼古拉斯是个着实跑了好些地方的人。”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又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他们,在那道命令之前,没有哪个城市比巴黎更受到狼群的骚扰。一四二○年,有个狼群曾袭击了这座城市。一四三八年,仅在一个月之内,狼群就在蒙特马尔特和圣安东尼门之间吃了十四个人,况且还不是在冬天,而是在九月份。至于那些在深夜的斗殴中被杀,或被暗杀而躺在街上的死者,更是经常被狼群吞食。它们还把教堂公墓的新坟刨开,把尸体拖出来。
这时,这个喜爱思索的市民暗示说,最近巴黎狼群之所以受到遏制,恐怕不是因为烛光的关系,而是因为英国人已经从法兰西王国被驱逐出去,“因为就凶恶和贪婪说来,那些英国人本身就是豺狼。在他们的统治下,我们法国的邻居被狼吃又有什么奇怪呢”!这个逻辑是如此切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以至不可能不受到众人的喝彩。但那老人却坚持自己的理论。“我承认这些岛国居民都是豺狼,但都是两条腿的,而且很不大可能给他们四条腿的堂兄弟什么好处。一种贪心的东西会爱另一种贪心的东西吗?我想不会。再说,我也是从我儿子尼古拉斯那儿听来的,狼爵士已不敢在伦敦城露面,尽管它比巴黎还小。伦敦的北城墙紧挨着浓密的森林,里面有大量的野鹿;仲夏时野猪就像苍蝇那样多得吓人。”
“先生,”杰勒德说道,“您似乎很熟悉野生动物。请您给我的同伴和我当个参谋。要是我们能足够安全地到达下一个城市的话,我们很想不走大路来浪费时间。”
“年轻人,我想这是一种无谓的冒险。现在离天黑只剩一个小时了,而你们几乎必须穿过一个潜伏着成千只半饥饿野狼的森林。这些野兽单个行动时是十分胆怯的,但大群行动时却勇猛得像狮子。因此,我劝你们今晚在这儿过夜,明天再及时上路。天亮的时候,这些野兽吼叫蹦跳得够累了,也可能用我们的好街坊(一些不堪教育的傻瓜)的肉把它们的空肚子填得饱饱的了。”
杰勒德但愿未必如此,问他能否给他们推荐一家好旅店。
“嗯!有一家金头旅店,我孙女是店主。她是个mijauree(迷人精),但不像大多数旅店老板那样狡猾。她那旅店也还干净。”
“嘿,那就去金头旅店吧。”丹尼斯插嘴道,显然是被他那无可救药的毛病所左右。
在去旅店的路上,杰勒德问他的旅伴mijauree是什么。
丹尼斯笑他无知。“还不知道mijauree是什么吗?嘿,世界上的人谁都知道嘛。它不多不少就是一个mijauree。”
他们走进金头旅店时,碰到一个年轻的妇人,头戴一顶法律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戴的华丽的紫冠。他们摘下帽来,低低地鞠了一躬。
就在她装腔作势的当中,她忽然发出大声的尖叫,并像只兔子从洞里钻出来那样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倒退着跑出房门,一边细声尖叫,一边用两只手紧紧地绷着裙子,盖住她的足踝,正当她冲出房门的时候,一只老鼠以同样的,也许更有道理的惊恐表情奔回壁板跟前。听到那位女主角的叫声,客人们都焦急不安地站起来看;犹豫不决地站了片刻之后,便笑着坐了下来。在善于体贴的丹尼斯看来,妇人的胆怯既然是女性的特征,就显得是一种可喜可爱的东西。他说他要去安慰安慰她,把她请回来。
“别!别!别!看在怜悯的分上,让她去吧。”杰勒德认真地说道,“啊,走运的老鼠!一定是某位圣徒遣它来帮助我们的。”
在他右手边坐着一位身体结实的中年市民,其举止颇有玩世不恭的味道。在这喧嚷当中,他既没有动一下,也没有停住他的刀叉。这时,他转过身来对着杰勒德,高傲地问他是否真以为那位装模作样的妇人害怕老鼠。
“是的。她叫得真厉害。”
“哪有卖弄风情的女人不会尖叫得活灵活现呢?这些母店主还在装模作样地模仿贵族。某个公主或公爵夫人大概在这儿宿过一夜吧。由于她从小娇生惯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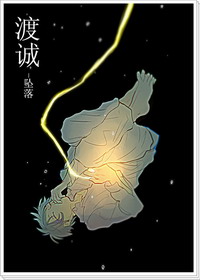
![[主欢乐颂]阿诚的欢乐(悚)之旅[伪装者]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4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