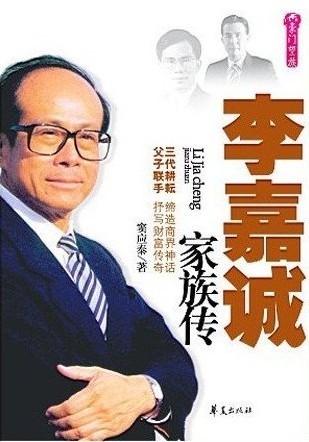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我的老伴,也拿一个金安琪儿给彼得·拜司根斯瞧瞧。告诉他咱家还有十四个这样的哩。注意,你得把它还给我!”
“爹,您先别走,更好的消息还在后面。”杰勒德说道。由于给全家带来了快乐而感到快乐,他的脸兴奋得红了起来。
“更好的!比这个更好的?”
接着,杰勒德谈到伯爵夫人的召见。全家又立刻响起了欢呼声。
“好了,愿上帝保佑善良的夫人,保佑范·艾克女士!一个圣俸?我的儿!我的操心算是有头了。伊莱,我的好友和丈夫,不管我们的死期什么时候到来,我们都可以幸福地去见上帝了。这可爱的孩子将代替我们。这些宝贝儿女将不会有谁没家没亲友了。”
从那时起,杰勒德便被看做是全家的支柱。他是一个特出的儿子。但这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的。他总是一贯正确,而且精益求精。科内利斯和西布兰特越来越忌妒他,渴望他领受圣俸的那天早点到来。这样,他们就能去掉这个宠儿,而尊敬的神父的钱袋还可以为他们打开。对于这种想法,他也采取合作的态度。爱情给他带来的创伤日渐成为一种隐痛。他的成功,以及他父母对他的喜爱和欣赏使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估计,并更加气愤玛格丽特的忘恩负义和不讲礼貌。尽管如此,她还是有足够的魅力使他对别的女子表现冷淡。现在他已有充分的理由指望在通过中间等级的圣职之后便能马上被指定为神父。他对拉丁文《圣经》熟习的程度已超过大多数修士,而且他正在和他的修士朋友们钻研教规和教条。主教头一次到他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就申请当一个驱邪师,即圣职中的第三阶。主教考问他以后便立即授给了他这个圣职。他必须跪着。念了一段短祷文之后,主教递给他一小张写满了驱邪咒语的纸说道:“拿着,杰勒德。你将有权力去治伏着魔的人,不管他们是受过洗的还是愿受洗的!”于是他谦恭地接过咒符,回家时已算是被教堂授予了驱魔的权力。
从教堂回到家里,小凯特在拄着拐棍迎接他。
“嘿,杰勒德,你猜猜,谁派人到家里来找你了?不是别人,是市长本人。”
“盖斯布雷克特·范·斯威顿!他找我干吗?”
“不,杰勒德,我不知道。但他好像急于见到你。你得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好吧,他是市长,我得去。但我不高兴去。凯特,我曾看见他对我很不友好地望了一眼。不要紧。像他那样望我一眼,只会使聪明人事先有所警惕。不错,他知道——”
“知道什么,杰勒德?”
“没什么。”
“没什么?”
“凯特,我这就去。”
第五章
盖斯布雷克特·范·斯威顿是一个狡猾的人。他对这未经世故的年轻人一开始是谈些与他的本题全然无关的东西。“本市的档案,”他说道,“都写得蹩脚难认,墨迹也年久发锈色了。”他愿将誊清档案的荣誉赏给杰勒德。
杰勒德问到报酬如何。
盖斯布雷克特愿出一笔正好能购买笔、墨和羊皮纸的钱。
“可是,市长,我花的劳动呢?这得干上一年才行。”
“你花的劳动?涂写涂写羊皮纸也叫做劳动?我看,那玩意费不了什么汗水。”
“这是劳动,而且还是技术劳动。不管汗水不汗水,在各行各业中技术劳动比粗活报酬高。除此之外,还有我的时间。”
“你的时间?真新鲜,你才二十二岁,时间对你有什么关系?”他把两只眼睛敏锐地盯着杰勒德,观察他这话所产生的效果,一边说道,“你还不如说你变懒了。你在谈恋爱。你身在念经的修道士这边,心却在彼得·布兰特和他的红发姑娘那边。”
“我不认识什么彼得·布兰特。”
这一否认反而证实了盖斯布雷克特的怀疑:这位驱魔师是在玩一个令人莫测的把戏。
“你撒谎!”他嚷道,“我不是看见你在去鹿特丹的路上挨着她身边走吗?”
“唉!”
“唉!前两天还有人看见你在塞温贝尔根。”
“是吗?”
“是的,而且是在彼得的家里。”
“在塞温贝尔根?”
“是的,在塞温贝尔根。”
读者,这就是人们在现代称之为“激将法”的一种手法。这原本是一个猜测,大胆地作为事实提出来,好通过年轻人的回答看他是否真去过那里。
这一计策产生的结果使得这个狡猾的家伙感到诧异。杰勒德竟然带着一种奇怪的神经质的激动表情站了起来。
“市长,”他声音颤抖地说道,“我这三年都没有去过塞温贝尔根。我不知道您曾看见和我在一起的那两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但我的时间是宝贵的。尽管您不珍惜它,可我得向您告辞了。”说罢,就目光炯炯地冲了出来。
盖斯布雷克特气得暴跳如雷,但他又慢慢地坐了下来。
“他不怕我。他知道点什么,即便不是事情的全部。”
于是,他把他忠实的仆人叫了过来,几乎一把将他拽到了一个窗子跟前。
“你看见那边那个年轻人吗?”他叫道,“快!跟着他!但别让他看见你。他虽然年轻,但老奸巨猾。你整天都得盯着他,把他经常到哪儿去,干些什么都报告给我。”
直到晚上,仆人才回来向人报告。
“情况如何?情况如何?”范·斯威顿急切地大声问道。
“主人,那年轻人从您这儿出去之后就到塞温贝尔根去了。”
“到巫医彼得家去了。”
第六章
“省察你自己的内心以后再进行写作!”康德先生说过这句话,世界上的杜鹃也都在响应着这个呼声。劝君往菜茵河最深的地方。泰晤士河最浑的地方望下去,描绘它的底部。劝君把一只手桶沉进自我欺骗的水井中去,打上来的一定是不朽的真实。难道不是吗?然而,首先值得可惜的是亚当的儿子没有哪一个曾经阅读过自己的心灵。即使阅读过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也只是凭借后天获得的习惯以及在若干年中审视别人的心灵得来的知识。甚至就是凭借后天获得的智慧以及经过思考得到的知识,他也只能费劲地读懂和搞清自己的心灵活动,而不能流畅地阅读。到塞温贝尔根去的半路上,杰勒德审视自己的内心,们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去塞温贝尔根。他的内心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是出于好奇,想知道她为什么负情抛弃我,并向她表明这并没有破碎我的心,而我对获得的荣誉和指日可待的圣俸十分满意,并不需要她,也不需要她们那些朝三暮四的女性中的任何一个。”
他很快就找到了彼得·布兰特的茅屋。门口坐着一个姑娘,敏捷地挑着她的织针,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则靠着一把长弓在跟她讲话。看到这人,杰勒德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楚。不过,走近些就可以看出中的决定作用。对庸俗唯物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这人原来已年过半百,是个老兵。杰勒德记得曾见过他以了不起的臂力和技巧射靶。不一会儿,年轻人就站到了他们面前。玛格丽特抬起头来,丢下手中的活计,发出微弱的叫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但这些激情的表现很快就被驱走,而代之以异常的冷淡。要是起先她没有流露出那种激动,想必此刻远不会显得这么冷淡。
“咦!是你,杰勒德师傅?奇怪,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我是过路看见你的。我想和你说说话,表示个意思,也向你父亲问问好。”
“我父亲身体很好。他马上就会来。”
“那么我就等他来好了。”
“听便吧。好马丁,请你到村子里去一下,告诉我爹,就说他的一位朋友要见他。”
“难道就不是你的了?”杰勒德说。
“我父亲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那倒有点令人怀疑。答应好等我,而我刚转过身去就溜之大吉,这可不够朋友。狠心的玛格丽特!你完全没想到我怎样走遍全城找你,没有你我怎样感到什么也不顺眼。”
“这些都是空话。如果你真想和我父亲或者和我在一起,你本该回来。先生,在我表叔家我们给你铺了一张床。他本会十分看重你,而且,谁知道呢,我或许也会十分看重你,那天我兴致很好。我向你担保,不管是你还是别的年轻人,都不会看到我再有同样的心情了。”
“玛格丽特,伯爵夫人一让我走,我就回去找你。但你已经不在那儿了。”
“不,你没有回来。要不,你就会看见我们桌边坐着的那个汉斯·克洛特门了。我们是特意把他留下给你带路的。”
“除了一个摔了跤的醉鬼,我谁也没看见。”
“在我们的桌边吗?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没有怎么注意——是穿的深色衣服。”
听到这话,玛格丽特的面孔逐渐温暖起来。但马上她装出不相信和严峻的样子,提出了许多精明的问题,杰勒德非常诚实地一一作了回答。最后算是拨开了阴云。他们猜出了造成误会的原因。继之而来的是感情的回潮。由于彼此冤枉了对方,这种回潮就显得更为有力。但尤其危险的是彼此之间感情的表白。双方都承认,自那以后,谁也没有高兴过。要不是这次幸运的相遇,谁也不会再感到人世的快乐。
这时,杰勒德看到桌子上有本打开着的拉丁文《圣经》的手稿本,于是他像只老鹰似的扑了过去。手稿本都是他的爱好。但他还来不及碰着它,两只雪白的手就很快地盖住了书页,一张绯红的脸则俯在手的上面。
“不要这样,玛格丽特,请把你的手挪开,让我看看你在读哪一段。我回家去也将读同一段,好让我的灵魂在《圣经》的那页上和你的相遇。你不愿意把手挪开?那我就只好把它们吻走了。”于是,他频频地吻着她两只手,羞得它们慢慢地移了开去。瞧啊!《圣经》打开之处正是:包在银网中的金苹果。
“真是的,”她说道,“我找这句话不知找了多长时间,但刚一找到——就被你发现了!”她略感前后矛盾,用白白的指头把那句话指给杰勒德看。
“是呀,”他说,“但它今天完全被遮盖在那顶大帽子下面。”
“别人都对我说,这是一顶漂亮的帽子。”
“也许吧。不过,它遮藏着的才是漂亮的。”
“不,不,是丑的。”
“就算这样吧,但在鹿特丹是美丽的。”
“是的,那天一切都是美的。”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这时,彼得走了进来,热忱地欢迎杰勒德,并一定要他留下吃晚饭。玛格丽特溜了出去。杰勒德便和彼得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饶有学术味道的聊天。玛格丽特带上她的银发网重新出现,对杰勒德投以半玩皮半害羞的一瞥,在他们旁边轻盈地走来走去摆设晚餐,兴高采烈,春风满面。凉爽的黑夜降临之后,杰勒德哄她出去走走。她先是反对,但还是出来了。杰勒德又哄着她走向通往特尔哥的大道。她先是拒绝,但还是去了。他们手牵着手在大道上逛来逛去。等到他不得不离开她时,他们相互发誓永不再吵架,永不再互相误解。他们长时间地亲吻,以印证他们的诺言。然后,杰勒德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回家去。
自那天以后,大多数夜晚杰勒德都是和玛格丽特在一起度过的。双方感情越来越深厚,以至他们感到,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才是他们真正生活的时光。其余的时间他们都要计数,难熬地忍受着。在这一深厚感情的开端,一切都很顺利。障碍是有的,但在希望、青春和爱情的眼中,这些都显得遥远而微不足道。许多要阻挠这一爱情的人的激烈情绪,并没有发出报警的烽烟来显示其火山般的性质和力量。真诚的爱情的航道舒畅平静,把这两颗年轻人的心永远吸进了它的端流之中。
于是……
第七章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不同寻常的紫袍闪着光辉,不同寻常的羽饰在迎风招展。马蹄亮锃锃地跑过特尔哥的街道。窗口和阳台上都缀满好奇的面孔。这是法国大使骑马过市,去附近的森林打猎。
除开他自己的随员,陪伴他的还有勃艮第公爵的几个仆役,是被借来为他增添荣耀并满足他的喜好的。公爵的筋斗专家面带庄重而沉静的威严骑在他的前面。他的威严使得比他更为高贵的同行者也显得轻浮随便。但有时,当敬畏的气氛接近使人感到压抑的程度时,他就会狼狈而有趣地从马上滚翻下来,甚至使得大使也不由得放声大笑。然后,他又以一种逗趣的方式从马尾巴上爬上去。他就这样扮演着他的角色。靠近这盛装行列的尾部,随行着一个引起人们更多注意的东西——公爵的豹子。一个猎人骑在一匹力大无比的弗兰德高头大马上,腰部携带着一个用精工制作的皮带拴着的长匣。这只伶俐的豹子就蹲伏在匣子的顶部,通过一条链子系在猎人身上。人们赞美着它的毛皮和斑纹,并挤到跟前来。有一两个还想摸摸它,拉拉它的尾巴。这时,猎人便以吓人的声音嚷道:“小心点!在安特卫普时,有人只是向它撒了一把灰,公爵就把那家伙化成了灰。”
“老天爷!”
“我说的是实话。善良的公爵把他关在地下土牢里,老鼠一夜之间就把他的肉啃光,只剩下了骨头。谁叫他惹这可怜的东西呢!活该。”接着,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恐怖的低语声。特尔哥人就再也不敢给他们君主的豹子搔痒了。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们的情绪又高昂起来。行列中殿后的是公爵的巨人,一个七英尺四英寸高的匈牙利人。这个庞然大物,就像某些别的巨人那样,具有音量很小的高而尖细的嗓门。他是个自高自大的家伙,但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也没感觉到自己有何缺点。此刻,他碰巧看见贾尔斯坐在阳台顶上,便停下来取笑他。
“喂,小兄弟!”他尖声喊道,“我差点走过去没瞧见你。”
“您倒是显而易见。”贾尔斯用低音吼道。
“坐到我肩上来吧,小兄弟。”巨人尖叫道,一边伸出大拳头帮他爬下来。
“如果我下来了,我要给你个耳光!”侏儒狮子般吼道。
巨人见这小人火气很大,同时一阵阵的笑喊声也在给他打气,便开始打趣他。再说,他也没有看出人们并不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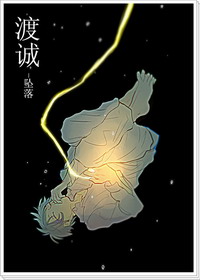
![[主欢乐颂]阿诚的欢乐(悚)之旅[伪装者]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4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