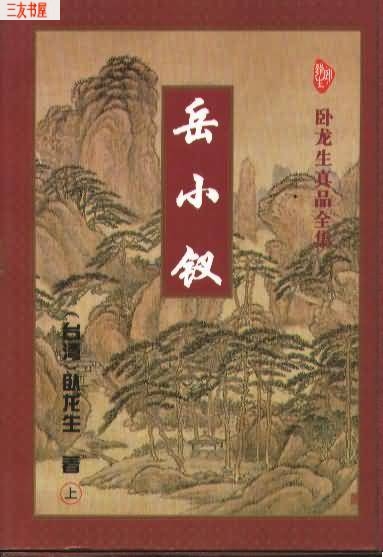断翎雪易钗-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时茶好,江蓠将茶倒入杯中,请李玄矶饮茶。
李玄矶见他还不肯摘下面具,不由笑道:“你难道要戴着面具喝茶?”
江蓠摸摸脸上,“哦”了一声道:“忘了……这东西戴久了,竟有些舍不得,若有一日不戴,便总觉少了什么。”笑着将面具摘下,面具之后却是一张轮廓分明的俊脸,约莫三十来岁,眉黑而浓,目光阴沉锐利,因戴久了面具,肤色略显苍白。
“少了什么?”
“安心,戴着它,没有人看得到这张脸……便不用担心有人窥破心事,是哭是笑是喜是悲,谁又能看得到?如此一来,自然安心畅意。”
李玄矶目中微有一丝怅恍,看了他一阵,道:“有多少年没见着你的真容了?这时看着,竟像回到了当年!”
江蓠浅啜一口清茶,道:“是啊,有些年没同你一起煮茶对弈……一转眼过了这许多年,该死的死了,不该活的也还活着。就好比你那爱徒,分明活不得,你却要生死留着她的命。”
李玄矶眉峰微敛,放下手中茶杯,正色道:“江蓠,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奉城主之命,叫人查了云阳王……”
“怎样?”
“他并没有派人暗杀过洛小丁,幕后主使者另有其人,是他的儿子谷落虹。”
第一卷 22。线索
李玄矶望着江蓠,面上微有疑惑之色:“小丁她,同谷落虹有过节?”
“或许是如此……我如今也还在奇怪,只是,从报上来的消息来看,目前似乎只能做此解。”
“此话怎讲?”
江蓠拎起茶壶斟茶,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谷落虹与你那爱徒是在风竹冷的寿筵上相识,这之前并没有打过交道。寿筵之上,两人不知因何事发生口角,继而便打了一架,谷落虹落下风,负气离去。之后洛小丁在回云宅的路上遭人伏击,被千尺门的曲沉丝打中,这事情大体便是如此……”
李玄矶握着茶杯的手慢慢攥紧,眉头蹙紧,眸光越发暗沉:“这么说,两人还是有过节。”到底是她不知检点,惹来的祸患。
江蓠微微摇头:“我总觉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倘若谷落虹是个无恶不作,斗鸡走狗的纨绔子弟,为这小小过节报复洛小丁,倒也能说得过去,可他偏偏不是。此人虽年幼,却很会做人,平日谨言慎行,宽仁恭孝有礼,也因此甚得云阳王之心,得以袭世子之位。试问如此之人,又岂会因这等小事加害他人呢?”
李玄矶道:“这也难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杀小丁走的是暗路。不过,你既如此说,必有十足把握……他这样处心积虑地杀小丁,到底所为何事?”
江蓠道:“我并没有十足把握,一切都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依目前的消息来看,谷落虹杀洛小丁,还是只能着落在寿筵上,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对。”
“你认为不是寿筵上的原因?”
“我认为不是。”江蓠语气渐渐变缓,有些犹豫不定,“这一次,似乎有人对我瞒报了消息……我已另外派人过去,等有了消息,再向城主禀报。”
李玄矶面沉似水:“竟然有人敢对你瞒报消息……你那些属下,实在该好好调教一番了。”
江蓠微一欠身,道:“江蓠明白。”
李玄矶沉吟道:“依你看来,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江蓠皱眉思虑良久,缓缓说道:“这些年来,云阳王那边我一直派人盯着,发现这谷落虹的来历颇有些蹊跷……他是十岁上进的云阳王府,报请朝廷允充族谱时,言其与生母明安公主相克,故一直养于民间。”
李玄矶心头一动,脑中有什么乍然滑过,望着江蓠默然无语,静待他继续说出下文。
“我又查了他入府的时间,真是好巧,恰恰便是你带洛小丁回浮云城的那一年,只不过晚了几日,也就是说,他与洛小丁是同一年生人。”
李玄矶点头道:“你说的不错,只是,这跟他杀小丁又有什么关系?难道只因他与小丁同年,便要置小丁于死地?必然还有其他什么……”看来,还需再好好问一下洛小丁,她一定还瞒着什么。
江蓠沉了一下,摇头道:“暂时还没有查到,只知道当年是白弘景带他回到云阳王府……至于他是在何处长大,由何人抚养?竟全无线索。”
“白弘景?”李玄矶微微坐直身子,似乎对这个名字颇感兴趣。
“云阳王手下曾有两大高手,其中一个便是这白弘景,此人轻功极高,善潜行隐匿,来无踪去无影,十分了得。不过,此人近些年耽于酒色,已大不如前,如今云阳王待他竟还不如左金鹏。”
李玄矶眼望远处,略微顿了一顿,又问:“另外那个高手便是那死了的凌绍祖?当年,你似乎对我提过此事……”
江蓠道:“正是此人。”
李玄矶凝眉思忖半晌,忽道:“先查查这白弘景再说……另外,不是曾有传言,说明安公主身有痼疾,不能生养么?如何忽然冒出这么大个儿子来?”
江蓠笑道:“这些王室显贵家中总难免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事情着落在白弘景身上,只要把这人身上的谜团解开,这些事情便水落石出了。”
李玄矶道:“这些事情跟小丁遇袭一事,似乎扯不上太大的关系……我多少明白你的意思,你怀疑谷落虹的生世与小丁有关?”
“我只是猜测而已……是与不是,只有再看那边的消息……”
李玄矶“嗯”了一声,表示赞同:“此事就按你的意思办,我唯一只担心……”他唯一只担心洛小丁的女子身份会被人识破,那谷落虹若真与她扯上什么关系,多半要追溯到六年前,倘若两人真的有什么瓜葛,只怕——
他再不敢想下去,推桌而起,走到水边望向远处,远处山峦起伏,云雪烟岚乱糟糟搅成一团堆在山头,一时竟分不清哪里是云,哪里是雪?他心头也是乱纷纷一团,是担忧是烦乱是隐恨,,竟全然理不出头绪。
江蓠道:“我知道城主担心什么……上次我提的那件事,城主有没有考虑过?”
“我想过,只是……她若去了你那里,同死又有什么两样?”李玄矶怅然一笑,怎样都难,放在身边不安心,去远了更不安心,到魅影阁,自此洛小丁这个名字便在江湖上消失,她那样的性子,只怕倒真活不出来了。
江蓠沉默,过了片刻方道:“江洲云绣坊那边,我已派人过去,还没传回信来,城主再耐心等些时候。”
李玄矶走过来,拍拍江蓠肩膀,道:“难为你替我想着这些事。”
江蓠笑道:“你若娶个贤内助,我便不用想了。说起来,你也该娶上一房妻妾,你师父当初只不准你收女徒,却未曾说过不让你娶妻的话,你又何必自苦?总惦着那些成年往事做什么?”
李玄矶皱眉看他一眼:“你倒拿皇帝的三宫六院跟股肱大臣相比,才更妙一些。”他轻叹一声,“这些事说来容易,当真要娶个贤妻却也不易……何况,我孤身一个人这许多年,也已习惯了,若多一个人在身边,反觉绊手绊脚,实在是麻烦。”
江蓠疑道:“当真如此?”
“我在你面前又几曾说过假话?”李玄矶反问。
江蓠摇头:“你这话半真半假,只信得七分……”
李玄矶微笑:“这原是江蓠本色,信人七分,疑人三分,你若完全信我,那便不是江蓠了。”
两人相视一笑,以茶代酒举杯一饮而尽,气氛到这时才变得轻松,江蓠想起旧事,忍不住取笑道:“当初你也并不是个正经人,勾栏青楼没少混过,放浪形骸,什么出格的事情没有做过?你师父险些要给你气死,哈哈哈……我竟想不通,你如今怎么就变成这样?整日拿那些清规戒律困着自己,难道不累?”
李玄矶不作声,很累,整日劳心劳力倒也罢了,还要面对那一摊子乌七八糟的事情,他这个城主远没有旁人想的那么风光,那么多人仰望着他,当他是神,岂能由他任意妄为?
第一卷 23。鼻衄
从蕊香阁出来时,已是正午时分,李玄矶满腹心事回到取松院,郁郁不乐吃了午饭,心里终究想不过,命秦管家传洛小丁来,秦管家早已看出李玄矶心头不畅,连忙前去通传。
过不多时,门外响起脚步声,门帘一掀,洛小丁迈步走了进来,又换了她那件半新不旧的棉袍,洗得都有些发白了,她穿着也不见寒酸。虽是男装,但清容丽姿,兼那纤腰流丸一束,无论怎样看,都只瞧着像是女子。李玄矶心里越发不是滋味,洛小丁躬身打揖问候,均是一概不理。
洛小丁见师父忽然如此,大是不安,只不知自己又做错了什么事?以至于师父这般生气,耳听得身后秦管家在轧轧地关门,心头由不住便是一跳,慌忙道:“师父叫我来,有什么事吩咐?”
李玄矶端坐椅上不动,也不看她,面上阴晴不定,只不作声。
洛小丁一颗心突突直跳,脑中急转,反反复复回思这段时日所作所为,除了私自上小寒山跟昨晚之事,似乎再无过分之举,难道师父竟为这两件事余怒未消?想到这里她再也忍不住,低声求告道:“弟子自知行事鲁莽,今后定然一一改过,再不让师父担心。”
李玄矶这才转目看向她,道:“那动辄自行其事的毛病你若能改,那是最好。我今日只问你一句话……”他的面容越发沉肃,眸光加深,“你如今,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洛小丁心头剧震,一时之间,只觉双膝发软,她竭力镇定,才没让自己跪下去。她迎着李玄矶的目光看过去,双目虽一眨不眨,浓长的睫毛却仍由不住轻轻颤动,轻轻摇头:“没有。”
李玄矶忽地转过头去,似乎在极力忍耐:“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遗漏的事情没有?”
洛小丁良久不作声,好一阵才道:“弟子不知师父指的是哪件事?还请师父提点……”
“提点……”李玄矶终于忍不住大怒,“你还要我提点?在晋阳时,你因何遇刺?”
洛小丁双唇紧抿,说不出话来,师父盯着她,那样锐利的目光,像一把利剑,斩开了阴霾,她精心藏匿的秘密,在这目光下,无所遁形。她再也无法承受,低下头去:“我得罪了云阳王世子……”
“你全都知道的,是么?”李玄矶苦笑,“我不问,你便不说,事事藏着瞒着。在潞州时,你说你去跟踪左金鹏,除此,你还做了什么?”
洛小丁抬头看他一眼,应道:“没有。”语声迅速而短促,竟是半点也没有犹豫,可那眼神却在刹那之间闪得远了。
李玄矶缓缓站起身,走到她面前,冷声道:“你再说一遍没有!”
洛小丁不敢往后退,心头一阵紧一阵慢,只觉背心额上冰凉一片,想是出了一身冷汗,强力自持道:“弟子跟踪到云阳王的潞州别院,中途被人发现拦阻,挨了人一掌,只好退回来,真的不曾再做什么。”
“那你又如何知道是谷落虹派人暗害于你……你还知道什么?”
“师父明鉴,弟子真的再没什么瞒着……”洛小丁脑中嗡嗡响成一片,只觉鼻中热乎乎地有什么东西涌出来,她微勾着头,眼看着两道血线往下直坠,却是一动也不敢动,任其往下直流,一眨眼间地上已是殷红的一滩。
“怎么回事?”眼见她鼻血不止,李玄矶也由不住惊慌失措,虽是恼恨,却也顾不上了,伸手扶住洛小丁后脑,道,“先别乱动,快抬起头来。”
洛小丁这才抬起头来,她仰着头不敢乱动,李玄矶伸指迅速在她颈后一按,点了后颈一处穴位止血,随后便忙个不停,又是拿棉花,又是拿巾帕,终于收拾妥当,将她扶到矮榻上躺好,又开门叫小郭端水进来,绞了个冷帕子敷在她额上。
待小郭将地上血迹收拾干净出去,他才在榻边锦凳上坐下,拉过洛小丁的右手切脉,只觉脉细而行迟,来往艰涩不畅,如轻刀刮竹,竟是涩脉。他微皱起眉,问道:“你这些日子在吃什么药?”
洛小丁微微偏过脸去,脸色虽是苍白,倒也平静,然而长睫忽闪,眼底分明有泪光闪动。李玄矶最知道她的脾性,表面上虽柔和恭顺,实则倔强无比,这一年多来虽常被他斥责怒骂,始终不曾见她在自己面前落泪,便是中了曲沉丝,她也能咬牙忍下来,而今她竟在他面前微露弱态,可见是将她逼得狠了。
李玄矶望着她无声叹气,眼见她伸袖偷偷去拭泪,心头顿时一阵阵酸疼上来,竟是再无主意。他的手从她腕上缓缓滑下去,将她细瘦修长的手指紧握在手中,一字字道:“小丁,如今你与师父生死息息相关,你万不能再瞒着我什么……”
洛小丁心头一热,几乎忍不住要将潞州偷听到的那些话都说出来,才一张口,耳边便又响起江蓠冷冷的声音:“杀了她毁尸灭迹,一了百了。”她浑身一颤,到嘴边的话便再说不出来,若是师父知晓谷落虹说的那些话,她还活得成么?她只觉师父握着自己的双手烫得灼人,心里越发惶恐,手上使力,竟一下子便将手指从他手心中抽了回来。
李玄矶脸上神色微变,随即便站起身来,淡淡道:“那些药你最好别再服了。”他走到门边招呼小郭,“叫鹧鸪来扶三公子回房去。”
一晃便到腊八,腊祭之后,年节便算开场,到腊月二十这天,阙金寒也自晋阳赶回,李玄矶有些日子没见二弟子,自是甚觉欢心,一年多来三个弟子好不容易聚齐,于是便吩咐人设了家宴,师徒四人连带徒媳霍元宵,又请了霍不修夫妻前来,七人共聚一堂,欢声笑语不断,取松院总算热闹了一回。
席桌按长幼顺序排下来,洛小丁左首竟挨着阙金寒,她心里虽是不喜,却也无法,好在右边还有霍元宵。自尚悲云婚后,洛小丁一直未出过门,也没见到这两人,这时再见,只觉霍元宵出脱得更为美艳,形容举止也稳重了不少,想来是尚悲云调教有功。
正胡思乱想,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