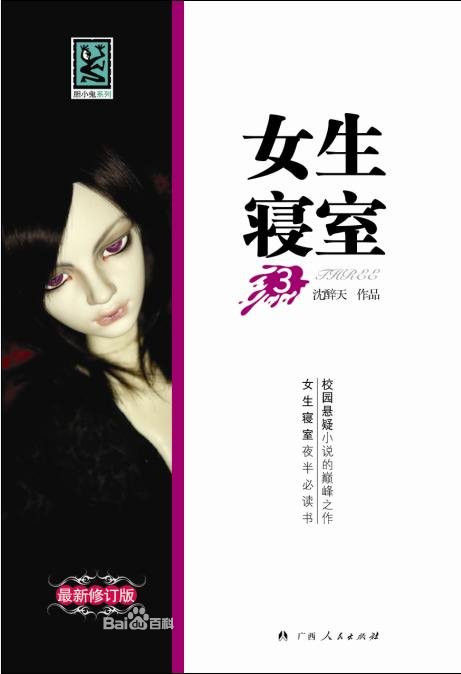另一种妇女生活-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为老字号店铺的简家酱园已经不复存在,昔日的后院作坊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居家院落,长满了低矮的杂草和沿墙攀援的藤蔓,晾衣绳上挂着一些浅色的女人的衣裳,唯一让人想起往事的是五六只赭红色的古老的酱缸,它们或者摞在一起,或者孤单而残破地倚在墙角,缸里盛着陈年的污水和枯枝败叶。两扇被钉死的木门将院子和店堂严格地隔离,也将简氏姐妹清净枯寂的生活和嘈杂尘世划了一道界线。店堂里仍然卖着酱油,是用黄鱼车从酿造厂拖来的统货,按照成色分甲乙两等价格出售,除此之外还有菜油、食盐、米醋、白酒和各种酱菜,店堂里终日洋溢着酱制品的酸甜而醇厚的气味。3个女店员卖酱油都卖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她们的头发、手指和皮肤上也沾满了酱油的气味,她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正午以及午后时分这里经常是空寂而索然的。3个女店员头顶上的楼板便吱吱嘎嘎地响起来,那是简氏姐妹在楼上走动和打扫发出的声音。它们往往是轻轻的小心翼翼的,即使这样,女店员也能从中判断简氏姐妹离群索居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尤其是顾雅仙,她能准确地分辨楼上的姐妹在马桶里解手的声音,甚至听得见针线从绣花棚架上坠落在地板上的声音。但是女店员们很少看见简氏姐妹。简氏姐妹进出走一扇旁门,那扇门异常地低而狭小,恰恰是为纤细小巧的主人特意设计的,男人进门必须低头弯腰,但是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走进那扇门里去。整条香椿树街的居民都知道简少贞和简少芬从未婚嫁,多少年来姐妹俩一直离群索居在酱园的楼上。只有卖酒酿的人经常看见她们,他知道她们喜欢酒酿,每次在酱园前敲打竹梆时,他会看见姐姐或者妹妹的苍白模糊的脸在楼窗上一闪而过,然后是一只同样苍白模糊的手,从窗内放下绳子和吊篮,吊篮里放着一角钱和一只蓝花细瓷的小碗。天气时阴时晴,又是南方的梅雨季节了,从街角垃圾堆孳生的苍蝇一路追逐着空气中酱制品和咸鱼的气味,嗡嗡地飞入酱园来。趁午后店堂清闲了,3个女店员拿起了苍蝇拍到处追打讨厌的苍蝇,经常有被拍死的苍蝇掉进酱油缸里,她们就用手把它们从里面捞出来。这些行为是不符合墙上张贴的食品卫生条例的,但是眼不见为净,买酱油的人从来不计较酱油是否含有细菌。3个女店员中粟美仙是资历最老的,她从17岁来酱园后一直就守着这片曲尺形的白木柜台,她看着店门上方的恒福酱园的牌匾雨打风蚀,最后颓然断裂,差点砸到酱园前摆摊修鞋的老皮匠头上。有时候粟美仙以一种饱经风霜的语调向顾雅仙和杭素玉发牢骚,说现在的酱油和乳黄瓜在从前都是上不了恒福酱园的柜台的,顾和杭都不屑于接粟的话茬,并且觉得这种牢骚发得莫名其妙。顾说管那些干什么,又不是你一个人在吃酱油,好坏大家一个样就没什么可埋怨的,杭则刻薄地说,你嫌它不好就别吃,还省得天天把个酱油瓶带出带进的。杭素玉的话锋直指粟美仙顺手牵羊的陋习,粟美仙难堪地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就用苍蝇拍在柜台上猛拍一记,对着虚拟的苍蝇说,你跑店里来拉屎吗?你以为你很干净吗?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多变的,3个女人互相不睦,但爆发嘴仗的往往是在粟和杭之间,一旦发生口角粟和杭都习惯于争取顾的支持。顾雅仙通常是袒护杭素玉的,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因为顾雅仙不想真正地得罪粟美仙,粟美仙的嘴惹人憎厌,手却巧得令人羡慕,她的针线活在香椿树街的妇女群中是数一数二的,顾雅仙有时候要托她给儿女缝衣裳做棉鞋。酱园也有个店主任,叫孙汉周。孙汉周主要是街西糖果店的主任,兼职领导酱园的3个女人。每逢星期日他就到酱园来站柜台。孙汉周是个不太严肃的男人,喜欢和顾雅仙动手动脚地打闹,前来买油盐的居民在夏天曾经看见一个滑稽的场面,顾雅仙追着孙汉周要扒他的短裤,而孙汉周在黄酒酒坛和酱油缸之间绕来绕去,他的短裤不时地被顾雅仙扒下一部分,露出一块雪白的皮肉,然后又在尖叫和哄笑中掩上了。他们的游戏不愠不恼,而粟美仙和杭素玉在一边观望,脸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这种事情自然会在香椿树街上张扬出去,有妇女在街上拉住匆匆路过的粟美仙,向她刺探顾雅仙与孙汉周的关系,粟美仙微笑着站住,她的神情是洞察一切的。会咬人的狗不叫,粟美仙说,说完意味深长地一笑,好事的妇女干脆把粟美仙拉到自己的家里,她也不推辞,拎着只人造革的蓝包坐下来,一边嗑葵花籽一边娓娓道来。其实顾雅仙跟孙汉周倒是清白的。粟美仙说到这儿就把话头打住,边上的人急于知道下文,但她把那只人造革包的两根褡手打了个结,站起来又要走了。她说,还要回家做晚饭呢,不在这儿嚼舌头了。
那么孙汉周到底跟谁呢?妇女们追着粟美仙到门口问。你们自己猜吧,酱园里有3个女的,你们猜是谁?粟美仙边走边说。总不是我吧?我都老得像根酱瓜了。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有关杭素玉和孙汉周的风流韵事就这样在香椿树街不胫而走。几天后杭素玉的丈夫老宋操着把菜刀闯进酱园,直冲孙汉周而去。杭素玉和顾雅仙两个人合力抱住了暴怒的老宋,孙汉周脸色煞白,摊着两只沾满酱汁的手说,这是怎么啦?好端端的怎么要砍我?老宋从柜台上抓起几块玫瑰乳腐朝孙汉周脸上掷去。我砍不死你就要去告你,告你利用职权玩弄女人,老宋放开嗓门怒声大喊,看你还敢不敢碰我的女人。孙汉周苦笑着抹掉脸上的污渍,他看了眼杭素玉说,杭素玉,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什么时候碰过你?我什么时候玩弄过你?杭素玉的眼睛里一半是泪水,一半是怒火,她夺过丈夫手里的菜刀,在柜台里烦躁地走了一圈,最后她站在粟美仙身边不动了。杭素玉朝粟美仙耳边嘀咕了一句脏话,猛地就将手里的菜刀砍定在白木柜台上。杭素玉厉声说,大家都听着,谁要再敢造我的谣,我就用这把刀把她的舌头割下来,割下来塞她的×缝。
这类事情搞大了也就收场了,并没有彻底澄清的必要。说到底香椿树街也非恪守礼仪之地。后来顾雅仙在谈论此事时采取了一种豁达宽容的态度,她对粟美仙悄悄地说,他们其实也就是掐掐摸摸那一套,你别大惊小怪的,比起肉联加工厂的那些骚货,我们酱园真该竖块贞节牌坊了。孙汉周后来离开香椿树街,在城北的一家煤店当店主任,那里的人都知道孙汉周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调动工作的。他自己也不忌讳这个话题,口口声声说,跟女人在一起有苦说不出,被杀了头都不知道脑袋是什么时候落地的。并发誓说他的煤店再也不要女工了。奇怪的是后来孙汉周的煤店里也是清一色的女工,而且又闹出了类似的风波。这当然是另外的故事了。酱园的柜台里仍然站着3个女店员,在店主任空缺的情况下由顾雅仙负责。有一天顾雅仙给顾客打完一戽酱油,突然想到什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旁边的杭素玉问她笑什么,顾雅仙说,我想起了孙汉周那个倒霉蛋,他是酱园的第几个店主任了?杭素玉白了她一眼,没有说话。而粟美仙很认真地扳着手指算了算,最后说,从公私合营到现在,有十六七个了。我记得很清楚。顾雅仙收敛起笑容,若有所思地说,也奇怪,男人到我们这里都呆不长。她说着扫视着两个女同事,又抬头看了看顶上的铺着报纸的楼板,楼上有简家姐妹轻缓的脚步声。顾雅仙说,大概这酱园的阴气太盛,是男人就不该来酱园吧?透过窗外的霏霏雨线,可以俯视香椿树街的雨中风景。简少芬看见有一辆嫁妆车披红挂绿地经过泥泞的街道,两边有人打着伞遮蔽雨点。简少芬站了起来,她想看看那个在雨天出嫁的新娘,但新娘乘坐的车子也许已经过去了,她只看见一群孩子淋得湿漉漉的,追着那辆嫁妆车疯跪。你在看什么?简少贞说。
结婚。有一辆嫁妆车过去了,6条被子,好像都是真丝和软缎。简少芬听见街东的方向有鞭炮声稀稀落落地响起,她说,好像是学校隔壁那家,那家有5个儿子。这种阴雨天,结了婚也要倒霉的。简少贞的手在绣花棚架上拍了拍,语气很厌烦地说,把窗子关上吧。简少芬应声关上了窗子,这样房间里的光线一下子就变得黯淡了,淅沥的雨声也被隔绝在外面。她重新坐到绣花架旁,分理着绞成一团的彩色丝线。她看见姐姐苍白的有点浮肿的脸上残存着一丝愠色。
开灯吧。简少贞又说,逢上阴雨天我就看不清丝线的颜色,听见下雨声我的心里特别烦。
简少芬就拉了拉身边的灯绳。楼上的这间大房间被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显现出一种古典的繁琐的轮廓。笨重的红木家具环绕四壁排列,镜台上的座钟嘀嗒嘀嗒地响着,北墙上挂着已故的简老板夫妻的发黄的遗照,照片下面就是那张庞大的红木雕花大床,灯光乍亮时简少芬看见一只老鼠从床底下窜出来,最后消失在墙角不见了。
这样幽暗沉闷的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简少芬这一年46岁,她记得姐姐比自己大8岁,那么姐姐已经是54岁了。有时候她静静地注视姐姐佝偻的瘦小的背影,心里就有一种对垂暮之年的惶恐。简少芬在发现自己提前绝经时,坐在马桶上哭了整整一个黄昏。这是一个衰老和灭亡的信号,预示她作为女人的某种权力已经丧失。她觉得自己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她无法抑制从心里喷发出来的哀愁。泪眼朦胧中她看见姐姐站在布帘旁边,无言而关切地注视着她。后来简少贞以一种淡淡的语气说,你怕什么?还有我呢。你怕什么?还有我呢。简少芬记得幼年时姐姐经常这样劝慰她。她记得从前总是被姐姐搂着睡觉,尤其是在父母双双亡故后,姐妹俩总是相依相偎度过每一个漆黑阴沉的夜晚。这种亲昵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简少芬16岁那年,有一天夜里简少芬梦见一块巨石压在她胸前,使她喘不过气来。等她大汗淋漓地醒来,发现巨石原来就是姐姐的手,那只手正沉重而无知无觉地按在她双乳之间。简少芬搬开了姐姐的手,她的初隆不久的乳房有胀疼的感觉,这使她又惊又羞,从此她不愿意再和姐姐睡一个被窝了。她记得她搬了床棉被睡到小床上去,但是黑暗的空间和恶梦加深了恐惧的感觉,她当时16岁,却无法离开姐姐单独睡眠。几天后她又回到了那张红木雕花大床上,她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她睡大床的内侧,让姐姐睡在外侧,每人盖自己的被子,姐姐没有反对,她只是略含幽怨地望着妹妹说,随你怎么睡。简少芬知道姐姐对她是宠爱有加的,特别是在从前。于是姐妹俩分而不离的睡眠习惯就这样延续至今。
简少芬记得从前经常有一些亲戚和邻居来敲门,他们大凡是来提亲的。起初是给姐姐提,姐姐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关自己的。简少贞说,我不嫁人,我嫁了人让少芬怎么办?少芬离不开我。他们又提出几个愿意入赘的人选,简少贞还是摇头,她说,我们家不要外人进门。等到客人离去后,简少芬看见姐姐在厨房间摔摔打打的,脸色很难看。你别以为这些人是好心,他们都盯着爹娘留下的财产呢。简少贞冷笑着对妹妹说,我这辈子就没打算嫁男人。我这清清白白的身子为什么要去送给那些臭男人?及至后来,简少芬长成了一个小巧玲珑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每次去刺绣厂送加工的绣品时,香椿树街上有几个男人的目光灼热地追逐她的背影,她走路时习惯低着头,习惯沿着路边房檐下走,但她还是感觉到了那种目光。她有点惶惑,有点惊喜,更多的则是犹如芒刺在背的不适应。简少芬背着装满绣品的包袱走在香椿树街上,脸忽红忽白,当她走过石码头空地时,她的眼神是一只惊慌的小鹿,阳光一无遮拦地直泻在简少芬身上,人们注意到她的皮肤在阳光下泛出雪白的光泽,就像又薄又脆的蜡纸。酱园简家的小女儿因此给人留下了美丽而又脆弱的印象。后来上门提亲的几乎都是为简少芬而来的,他们耐心地劝说简少贞让妹妹出嫁,而简少芬就躲在房里,她用手指塞住耳朵,塞了一会儿又松开,她想听听外面的谈话,却又害怕听见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你到底想不想嫁?简少贞曾经这样逼问过妹妹,她的表情是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你要是想嫁我也不拦你,我会给你置办一份像样的嫁妆。不。简少芬摇着头说,我害怕,我不嫁。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没有合适的还不如不嫁。简少贞凝视着妹妹的脸,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说,他们就是容不下我们简家,非要把我们姐妹拆散了罢休。你别看他们脸上热心,把那些男人吹得天花乱坠,其实都在骗人,我才不相信他们的嘴,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也不相信,我只相信姐姐。简少芬说。简少芬处处依附姐姐,这在姐妹俩多年的幽居生活里成为一种坚固的定势,而她们有别于常人的生活方式也渐渐消解了岁月和香椿树街上的流言蜚语,一直到红颜消逝,不再有人频繁地踏响酱园残破的楼梯。
一个雨后的早晨,简家姐妹打开了朝西的窗户。西窗是用油毡封钉的,平时从来不开。简少芬擦拭着窗户上的灰尘和毛茸茸的霉斑,忽然发现院子里的那棵桃树上结了果子,两只淡黄色的镶有红彩的桃子就悬挂在窗外,伸出手就可以摘到。她很惊奇,那棵桃树从来是只开花不结果的,你来看,两只桃子。简少芬又让姐姐来看,她发现姐姐站在窗前的眼神是疑惧不安的。简少贞对着桃树凝视了片刻,最后果断地抓起剪刀,探出窗外剪掉了两只桃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