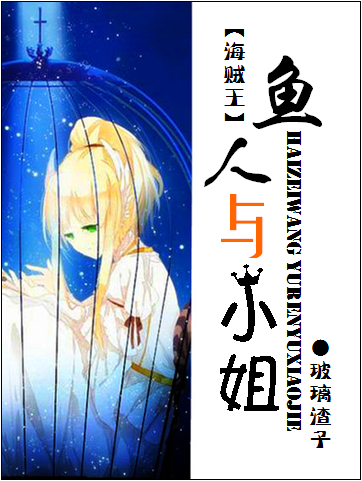人与人以及人与狼的爱恨情仇:雪狼 作者:徐大辉-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最终还要吐出来,带出肠子油,鹰就消瘦下去……
韩把头对爹的驯鹰方法改进了许多,驯鹰房建在悬崖绝壁上,就是他的发明。
“鹰击长空俯瞰人间,不能熬尽它这一天性,那样对打猎不利。”韩把头说。
“老把头!”老姚在山下喊。
“什么事?”吴双出现在驯鹰房窄下的窗口,山太高的缘故,他的脸很小,缩小了几号,“把头在睡觉。”
“有人找他。”老姚指指身边的小松原。
吴双看清是小松原,便缩回头。
韩把头直接走下山来。
“老把头。”小松原上前打招呼。
“太君找我?”韩把头睡眼惺忪,问。
“我们队长找你。”小松原说。
40
一马树的傍晚有了索菲娅,便有了生机。她的笑声如泉如溪,踏着草尖传向远方,是那样无忧无虑。
秋天晒干狼屎泥颜色的土坨上,卢辛和项点脚坐得很近,瞻望遥远的地平线,耳朵灌满索菲娅的笑声。
“女人真是水做的。”卢辛慨叹。
“但愿不是祸水。”
卢辛直愣愣地望着项点脚。
“莫非二弟看到什么,她……”
项点脚摇摇头。
“你是不是认为我把她带回绺子,破坏了规矩?”卢辛不能不在乎水香的话,尤其是在花膀子队背累(背时),他的话更不能不重视。
项点脚拔出嘴里的一段干草,橙色的涎液流出嘴角。
“女人是雪不是水就好了。”项点脚说出句没头没脑的话。
卢辛更加迷惘。
一只被惊起的沙鸡几乎是贴着头顶,突突飞过,他们感觉到了翅膀带起的风。
“啊呀!”卢辛惊呼。
一摊稀白的东西落在卢辛荒丘一样的头顶上,是沙鸡屎。
“母亲的!”卢辛狠骂一句,他总用这样的词汇骂人。
鸡屎突然间落到头上,胡匪视为不吉利。
“一马树不能待了。”项点脚说。
“哦?为什么?”卢辛惑然。
“我有预感……”项点脚说,“郝眯缝眼的眼睛滴溜溜转,我心没底呀!”
“一个吓破胆的扒子,小泥鳅还能翻起大浪?”卢辛问,“我们不去香洼山打白狼?”
“我看还是不去的好。”
“好不容易碰上白狼群,不打可惜喽。”卢辛说。
“眼下保住队伍要紧啊……”项点脚说服了卢辛,“走,立马走。”
“那我们去哪儿?”
“离开爱音格尔荒原,钻大青山。”项点脚说出自己的想法。
一时半晌,一言半语很难说服卢辛离开的。爱音格尔荒原对卢辛,对花膀子队是避风港,一个土丘,一条河流,一片草地,一个村镇都了如指掌,环境的熟悉就意味着安全。
说心里话,项点脚也不愿意离开此地。
“可是我们只这匹马几杆枪,又面临着几家仇人追杀,好汉不吃眼前亏。到大青山养精蓄锐,壮大队伍,等东山再起……”
卢辛和项点脚谈到很晚,狼屎泥颜色的土坨上完全被黑暗覆盖,他们才走下坨子,分别回到宿处。
此时,花膀子队的人和狼夜宿极其相似,分散到各处。
卢辛和索菲娅的宿处,有了女人显得活力和浪漫。一墩红柳丛,经女人的手装饰,变成了美丽的建筑,树枝上系满野花。
他们甜蜜在柳丛里,仰望秋天的花朵。
“今晚你怎么冷冰冰的?”索菲娅感觉异样。
“没呀?”卢辛否认。
“你没叫我马。”
卢辛习惯叫索菲娅马,尤其是那种时候,他更喜欢叫。骑马驰骋的感觉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今晚,卢辛从跃上去,到跳下来,他都没骑马的感觉,没吭一声,默默做完事。
“亲爱的,你没叫我马。”索菲娅抱怨说。
“我们要离开爱音格尔荒原。”卢辛告诉她。
“这里不是好好的嘛,为什么要离开?”索菲娅觉得他的决定太突然。
“这里我们不能待啦,得走。”
索菲娅情绪立刻低落下去。她不愿意离开一马树的原因,是一个秘密,一个连卢辛都没告诉的秘密。
索菲娅想给卢辛生个孩子,她正在拜仙求子。
在叶老憨家她从养母那儿学会求子的方法,供奉送子娘娘“晚上一炷香,清晨三叩首”。
“我求子呢。”索菲娅道出实情。
“求子?”卢辛眼光没离开她的腹部,身子更靠近她一些,说:“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哪里有庙啊?”
“我自设的神坛。”索菲娅抓起他的手,“走。”
他们来到一个土丘上,卢辛看到一盏燃着的灯,灯光昏暗,几样面食供品和已燃尽的香灰。
“跪下,”索菲娅先跪下,叫卢辛:“给娘娘磕头。”
很少受别人支配的卢辛,此时意志完全受她支配,乖乖地跪在索菲娅的身边,双手合一作揖,随着她念叨祈祷语。
然后,他们离开。
“需要二七一十四天,我已经求了九天,还有五天。”索菲娅半路上说,样子十分虔诚。
“你怎么不供佛像,而供一盏灯?”卢辛问。
“这不是一盏普通的灯,是一盏神灯。”
“神灯?”卢辛无法理解那只破旧的马灯,是什么神灯,供奉它,给它磕头烧香做什么?它真的能送子吗?
叶家有一盏神灯,是索菲娅的养母从庙里“窃取”的,9岁的索菲娅参与了窃取。娘和她到观音庙烧香,趁身边没人,娘用事先准备好的包袱皮,裹住佛桌上供奉的莲灯,急匆匆地逃回家。
“娘,偷灯干啥?”9岁的索菲娅问。
“不是偷,是请。”娘纠正女儿的说法。
索菲娅不明白娘偷——请一盏庙里的灯做什么?正像卢辛一样不解。慢慢长大,她才明白娘整日供奉它,是祈求观音送她子女。在民间,“灯”和“丁”谐音,偷来观音的神灯,就会添丁。
同卢辛来一马树,她忽生要一个孩子的念头。自从被养父叶老憨霸占,几年里,有几个男人来耕作,都没有收成。她想起养母,祈求观音让她的肚子里有动静。
“哪里去弄‘神灯’?”索菲娅遇到难题。
附近没有人烟,也没一座庙宇。养母说过:信神有神,信鬼有鬼,不信是土坷垃。她向项点脚要一盏旧马灯,把它当神灯供奉起来。
“我和水香的定好了,后天挪窑(转移)。”卢辛说。
“那你们走,我不走。”索菲娅说。
“不行,一起走。”卢辛口气有些生硬。
“求子还有六天……”
“风紧拉花,一天也不能拖延。”
“风紧拉花?”
卢辛见她不懂这句土匪黑话,解释道:“就是事急速逃。”
索菲娅迷惑不解,什么事那样急需迅速逃走呀?
“你别问了,做好准备,后天离开一马树。”卢辛的口气不容违拗。
“后天什么时候走?”她问。
“干什么?”
“我再给神灯烧最后一炷香。”索菲娅说。
“鸡叫头遍,挑(走)。”卢辛说。
雪狼 第三部分
卷十一 狼怕打
狼怕打,灯怕吹,毒蛇怕石灰。——汉族谚语
41
“卢辛近日要去香洼山。”林田数马说。
背靠狼皮椅子上的韩把头猛然坐直身子,他问:“他们去香洼山干什么呢?”
“打狼,”林田数马说,接着补上一句:“打白狼。”
花膀子队要去香洼山打狼,这个消息让韩把头不安起来。狩猎队迁至玻璃山,就是冲香洼山里的白狼群来的,准备今年冬天围猎。
“听说香洼山是韩把头的场子呀!你们早下了喂子。”林田数马婉转地挑拨。
狩猎的规矩,先来后到,谁占的场子,他方不可随便进入的。
“看来,花膀子队要搅你们的场子啊!”林田数马继续挑拨。
“这不行!”韩把头终于坐不住了。
此前,林田数马游说几个时辰,怂恿韩把头去剿杀花膀子队,韩把头迟疑不决。狩猎队去和土匪打,尽管不怀疑守备队相助,也难免伤亡。捕杀大型动物也有伤亡事故,但那毕竟损伤很小。
“他们打死你兄弟。”林田数马几次提到卢辛的人打死刘五。
刘五之死,一棵复仇的种子在韩把头心田埋下了,已发芽,经林田数马一挑唆,仇恨速成苗儿,猛蹿猛长。
“你要是去打他们,我给你们提供一挺轻机枪。”林田数马说。
马队最怕机关枪,这一点韩把头清楚。
韩把头迟迟下不了决心。
林田数马瞟一眼小松原,暗示他劝说韩把头。
“花膀子队叫狼吃掉大半,剩下十几人,正是报仇的好机会。老把头,去干掉他们吧。”小松原说。
韩把头听进去小松原话的每一个字,朝年轻的日本兵点点头。他本该问守备队长的话,却问了士兵:“你们为什么不去消灭他们?”
小松原侧头望下队长。
林田数马说:“我们是外国人,在你们的土地上动枪动炮,怕引起外交冲突……”
韩把头听明白了,林田数马说他们只是铁路的守备部队,不便直接出头,但可以暗中帮助消灭花膀子队。
“一马树的沟壑仅一个出口,我的守备队埋伏在那儿,哪怕是一只蚊子逃出来,也要被消灭。”林田数马说。
林田数马离开狩猎队下山,立即做了动武准备。
他们商定夜晚出发,用夜幕来做掩护,悄悄接近目标。
花膀子队一点都没察觉,韩把头的狩猎队已经看见月光下的那棵孤零零的榆树,就是说离土匪的宿处数步之遥了。
卢辛睡得很沉,上半夜的疲倦要在下半夜得到恢复,索菲娅挪开他横在她胸口的胳膊,他全然未知。
索菲娅拿上香,她要在今晨出发前给神灯上最后一炷香,做最后一次祈祷。
项点脚躺在马肚子底下,进入一马树以来,他一直这样睡。他是这只队伍中今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者,他沉思默想的是花膀子队未卜的前途,进了大青山暂时摆脱追杀,新的困难立刻出现。人地生疏,马上就进入冬季,弟兄们身上的御寒棉衣还没落实……会不会遭附近官府的围剿。
坐骑忠诚地站着不动,减少声音以免惊扰主人睡眠。事实上,项点脚根本没睡,头枕着草地,耳朵贴在地面上,像一只夜晚护院的狗。
嗵,嗵!脚步声响起。
项点脚抬起头来,觅声音望去。是索菲娅,他发现她夜里经常一个人出去,去给神灯上香。
“女人啊!”项点脚叹息,重新躺下来。
荒原的风冷嗖嗖地刮来,项点脚偏下头,望眼天空。觉得时间还早……睡一会儿,他强迫自己睡一会儿。要赶的路很漫长,充满惊险也说不定。
“上!”韩把头命令。
狩猎队员匍匐前进,不担心他们会惊动猎物。终年累月的捕猎,练就了比动物还狡猾、脚步轻如风中飘纸。
项点脚是在睡意朦胧里听见轻盈脚步的,他虎跃而起,用那只长腿勾住马镫,燕飞上去,未等抖缰绳,坐骑带他向土丘下狂奔。
一个胡匪跟上来。
砰!
与项点脚并驾齐驱的那个胡匪,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穿过胸膛,他在还有力气的时候,极力转过身,想看清是什么朝他开枪。也许他看到了,也许没看到,生命陡然琴弦一样断了,他再也不能向世人叙述他看到的东西。
项点脚也在此时跳下马去,连滚带爬地钻入红柳丛。低矮的柳树遮掩不住他,做了这样的选择有其道理,逃生的明智抉择。这儿有个废弃的狼洞,以前他来过见过,至于此时洞里是否有狼什么的,慌不择路顾不上了,一头钻进去,即使喂了狼,也比死在打狼人枪口下有尊严。
卢辛死在铺位上,连动都没动弹一下,和他平时睡姿差不多。狩猎队员像打一只藏匿洞穴里的兔子,朝洞里开枪,抠了“窝子”。
其他的土匪也在睡梦中丧命,马都幸存下来,韩把头事前交代,万不得已不准打马,土匪的马好,留下狩猎队用。
枪声平息下来,林田数马断定事情已解决,便带守备部队赶过来。
“你的大大的厉害!”林田数马表扬了韩把头一句,率队离去。
韩把头并没走,他的人在打扫战场,待天大亮时再走。
“日本人说卢辛有个女人,怎么没见到她啊!”吴双说。
吴双的话提醒了韩把头,使他想起这一节:“啊,对呀。她应该和卢辛睡在一起。”
卢辛自己在柳条墩子里,身边有女人的衣物。
“她是和他,在一起。”韩把头说。
“一定躲藏起来了。”吴双朝四周望望,黑乎乎的一片,见不到半个人影。他喊:“喂!你出来,我们不会难为你一个女人家的。”
没有任何回声。
“天亮再找吧。”韩把头说。
狩猎队等到天亮再走还有一件事要做:韩把头吩咐埋葬花膀子队的尸体,不能让他们暴尸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打死不要的动物都埋上,何况是人啦。
东方泛起鱼肚子白。
索菲娅因去给送子娘娘去烧香躲过劫难。枪响时,她刚点燃一炷香。她目睹了花膀子队在枪口下毁灭,完全有机会逃走,她没逃走。
卢辛生死不明,她必须知道结局才肯离开。
索菲娅走到供奉的神灯前,身上还带着装卢辛的体温,刚从他的被窝和紧紧拥抱中走出来。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给我们一个孩子吧!”索菲娅祈求着,磕头,她作揖磕第二个头时,她蓦然感到肚子里有动静,是她渴望已久的动静。
“谢谢菩萨,谢谢菩萨!”索菲娅惊喜。
这是一个在荒草甸子间,在马肚子底下诞生的生命,他(她)的血管里一定流淌着青草和枪弹味儿的液体,土匪的血肯定是黑绿色的。
砰!砰!砰!
骤然的枪响,惊得索菲娅目瞪口呆。
转瞬间,花膀子队被歼灭。
索菲娅出奇地平静,没掉一滴眼泪,她在恪守一个诺言。
“有一天我死了,你不要用眼泪给我送行,我不喜欢!”卢辛说。
“我不掉眼泪。”她说。
现在索菲娅做到了,一个面对她的心爱人死去而不哭,可见这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