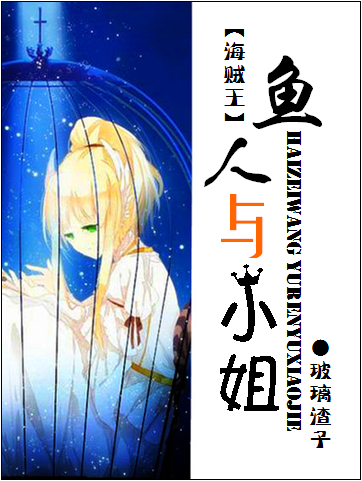人与人以及人与狼的爱恨情仇:雪狼 作者:徐大辉-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快列车直达奉天。
“177次通过!”
调度的命令一站传一站。
火车在通过一个小站后,速度明显加快,两条闪亮的铁轨像被割开口子,前面分开,后面立即合上,这情景船在水上行驶经常可以看到。
林田数马摸了下受伤的眼睛,手便粘上鲜艳的东西。
“队长,你眼睛还出血呢。”小松原经心照料他们的队长。
林田数马论级别并不高,在满铁沿线配置的六个守备大队中,他只是个小队长,管几十个士兵。但是,独立守备队司令是他的亲戚,当他受伤的消息传到设在公主岭的司令部,司令即命177次列车直开奉天。
“到了什么地方?”林田数马闭着眼睛问。
“开原。”小松原答。
林田数马不再说话,开原到奉天还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列车改为特别快车没人通知他,但他感觉到了,亮子里遭袭及本人受伤的消息,他已叫人报告独立守备队司令部了,火车加速又一站不停,一定是司令部做了安排。
眼睛究竟伤的程度如何,林田数马无法确定,疼痛不止让他猜测伤得不轻,至于治疗他不担心,满铁有一流的眼科医生,小松原的亲舅舅生田教授,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顶级眼科专家,成功做了几例眼球置换手术,就是说眼球生田教授都能换,何况治疗他的眼伤。
林田数马没把自己的眼伤看得太严重,至少还达不到换眼球的严重程度。此时此刻,耳边轰隆隆的铁轨声音,让他想的不是受伤眼睛的未来,而是那门对着守备队部开火的土炮。
“花膀子队疯啦,要与我决一死战。”
当林田数马从炮台望出去见到土匪土炮时,有些惊讶。
“他们用炮轰大门!”守备队员惊惶。
木结构大门是固若金汤守备队队部大院的软肋,一但攻破,马队涌入,就难抵挡。林田数马经历过遭遇土匪马贼,与他们交过手,在他眼里,土匪没什么大闹(能耐)。
“加强火力封住大门就是,土匪打不进来。”林田数马指挥抗匪,自己保持镇定。
确定是花膀子队一股土匪来攻击后,林田数马想的最多的是与这股土匪的恩恩怨怨,应该说有怨无恩,而且是积怨由来已久。
林田数马率队驻扎亮子里火车站后,他看出要想铁路相安无事,就得与周边的胡匪搞好关系。荒原上的几绺成气候的胡子,他用小恩小惠安抚住了,只剩下花膀子队,软硬兼施不奏效。
“施计!”林田数马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与花膀子硬克硬,双方都要伤亡,他细算了一笔账,不划算。
“嗾疯狗咬傻子!”林田数马想到关东这句土话,受到了启发。目标明确:傻子是花膀子队的卢辛,疯狗呢?要找到一只听话嗾它就咬人的疯狗,他自然想到了胡子大柜沙里闯。
“沙里闯,你帮我办件事。”林田数马说。
“请吩咐,队长。”沙里闯对他是有求必应。
“绑个人。”林田数马直截了当。
“绑谁?”
“卢辛。”
“卢……卢辛?”沙里闯抠抠耳朵,唯恐自己听错。
“绑卢辛的票。”林田数马肯定地说。
绑票,土匪叫请财神,以钱换命的事,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单就绑票的黑话就有一大串:叫票(讲价)、请观音(绑女人)、熬鹰(折磨票)、叫秧子(审票)、秧子房当家的(管票的头目)……
“可我不明白队长为啥要绑大鼻子的票?”沙里闯问。
林田数马对胡子大柜简单扼要地说了为什么要绑花膀子队的卢辛,沙里闯对日本人为什么要绑卢辛不感兴趣,对日本人许诺绑票成功后给他们几杆三八大盖枪兴趣十足。
“怎么样?有几分把握?”林田数马敲钟问响。
“九成半。”沙里闯还是留有了余地。
“九成半不行,必须十二分把握。”
“队长,你有所不知,卢辛身为大当家的,武艺高强且不说,他深居简出,不容易接近。”沙里闯说到难度。
事实也如此,林田数马心知肚明。容易得手,干嘛要胡子来绑票呢?见到沙里闯为难的样子,就要给他打气,要激他的兴奋点。林田数马说:“我还有一挺轻机枪,你若喜欢……”
“碎嘴子!”沙里闯一听是机关枪,眉飞色舞。
“只要绑来卢辛……”
“干吗只要,”沙里闯说,“一定绑他来。”
有一杆机关枪的诱惑,沙里闯铤而走险了。他不顾四梁八柱反对,决定绑卢辛的票。
“北极熊惹不得啊!”二柜说。
“是啊,二爷说的对,花膀子队的人可不是吃闲饭的……”水香也反对。
沙里闯一意孤行:“我亲自去请大鼻子。”
老天有意助沙里闯,卢辛喝醉了酒想女人发疯,一个人跑到亮子里镇,到“新乐堂”找妓女红妹,盯着他的沙里闯倒没费什么事就绑来了卢辛。
“大鼻子我给你弄来了。”沙里闯洋洋得意。
林田数马亲自验过,是他要找的卢辛。按事先的许诺,给了沙里闯武器。
卢辛落到林田数马的手里,林田只高兴半截,再往下他就是使劲乐也乐不下去了。不久,他手下的三个士兵,包括小松原在内让花膀子队给绑了票。
“八嘎!八嘎!”林田数马气急败坏,谁说得清他在骂谁?是胡子还是他自己。
八嘎一阵后,林田数马冷静下来。蚂蚁上树似的从根到梢寻思这件事,花膀子队在他们的大当家的被绑架后,立即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绑了守备队员。令林田数马费解的是,沙里闯出面绑的卢辛,而后秘密羁押在守备队部里,花膀子队怎么知道的?作为报复他们理应去绑沙里闯的人,却绑了守备队员。
“沙里闯是不是靠不住?”有人给林田数马抠耳朵。
“不,”林田数马绝对相信沙里闯。
“那……”抠耳朵的人疑议。
“是花膀子队里有高人!”林田数马从不轻视对手,“中国有句老话说得有道理,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
花膀子队里的确有高人,项点脚便是林田数马说的高人。卢辛在“新乐堂”的妓女被窝里掉脚(被捉),花膀子队立即开了锅,俄国人不缺少骁勇,嚷着要去和沙里闯火并。
“你们只听到辘轳把响,不知井口在哪儿。”项点脚喝住众匪,他说,“我们与沙里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们说他平白无故绑咱们大当家的干什么?”
众匪只摇头。
“事情蹊跷啊!”一个匪徒说。
“没什么蹊跷的,沙里闯暗地里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说不准这次绑架大当家的,日本人背后指使呢。”
项点脚秘查起来,很快就弄清,是日本人做的扣(设圈套)。
“换票!”项点脚说。
绑票是胡匪的惯技,换票也是他们常使用的方法。绺子里的重要人物被官府兵警俘获,直接要不回人,就绑架官府兵警的重要人物做人质来进行交换。
项点脚策划了绑守备队员的票。
林田数马没料到花膀子队还有这么一手,也真厉害的一手。不放卢辛,他们就不放守备队员,一还一报的,最终妥协的林田数马,他又算了一笔账,卢辛的头不值三个队员的头。
一场煞费苦心的阴谋,以这样的方式结果,林田数马心里始终窝着一口恶气,发泄出来是早晚的事。
守备队部这次遭袭,眼睛又被打伤,林田数马心里憋着的气蓦然变成了烟,正从他的七窍往外冒。倘若不是眼睛受伤,他会到公主岭独立守备队搬兵,剿灭花膀子队。
“队长,进站了。”小松原说。
林田数马回过神来。
满铁医院派来的汽车等候在奉天火车站的出站口。
12
“干杯!”
“干!干!干!”
花膀子队的老巢酒宴在进行。
“痛快,真痛快!”卢辛手舞足蹈,有些醉意了。
项点脚不露声色,稳稳当当地喝他的白开水,也可以说是以水代酒。在整日被酒泡着的花膀子队里,他是唯一的滴酒不沾的人。酒是花膀子队的精神鸦片,卢辛离不了它,全队的人都离不了它。
“酒是我的女人。”一个匪徒的口头禅。
项点脚不沾酒不是自律的原因,他的确喝不了酒,闻到酒他都头晕。刚到花膀子队时,卢辛不解,劝他喝劝他练。
“男人嘛,马、枪、女人和酒,离不开。”卢辛说。
项点脚笑笑:“女人和酒我都不行。”
在卢辛的眼里,不喜欢女人的男人还可以理解,不喜欢酒的男人就无法理解。
曾经有一段时间,卢辛竟然觉得不喜欢酒的男人很可怕。再后来,卢辛因项点脚不沾酒竖起大拇指:“好,很好!”
项点脚不喝酒,尤其是都喝酒的时候他不喝酒,保持头脑清醒。花膀子队因此躲过一次劫难。
让花膀子队在爱音格尔荒原蒸发,林田数马动了不少脑筋。俄国人嗜酒如命,林田数马就阴谋起酒来,灌醉他们再消灭他们。
林田数马在花膀子队中收买一个匪徒,让他趁机往酒里下药。这个匪徒刚进来不久,尚不了解一只腿长一只腿短的瘦小中国人项点脚。
花膀子队截获一车高粱,卢辛高兴,杀猪宰羊,放量饮酒。
项点脚一双机敏的目光扫视喝酒的人,那情景他像狼群里一只担负警戒的哨兵……得意忘形的喝酒人中,项点脚注意到那个为日本人做事的匪徒。
“他心有旁骛。”项点脚心想。
那个匪徒悄悄离开宴席,项点脚便跟随上去。匪徒在院子里上了一匹马,飞鞭跑出老巢。
“砰!”项点脚一枪将那个匪徒掀下马。
卢辛闻声跑出来,见项点脚正审问那个奄奄一息的匪徒。
匪徒道出了实情:“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卢辛命令全队迅速撤离,林田数马扑了一个空……
“喂,你还担心那个林田数马来袭击我们?”卢辛见项点脚心不在宴会上,端着酒杯过来,“来,为林田数马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干杯。”
“干!”项点脚端起水杯,他没扫卢辛的酒兴。
卢辛喝干酒没走,坐在项点脚身旁,他有话要说。
脚项点给卢辛倒满一杯酒。
“我去趟哈尔滨。”卢辛说,“卖掉白狼皮。”
项点脚看出卢辛去哈尔滨不单为卖狼皮,大当家的除了嗜酒,还有一个嗜好:女人。
花膀子队与当地的其他中国土匪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七不夺、八不抢”的行规,成立匪队之初,有一位白俄罗斯女人娜娜,留在马队给卢辛当情人。活动在爱音格尔荒原居无定所,天当被子地当床,他们两人经常在马肚子底下做那事。
山坡、原野、河边、草地,娜娜纵情地叫床,她叫床的声音奇奇怪怪,与马嘶的声音极其相似。那饱含情欲的声音感染了马们,引起它们的共鸣,随之嘶鸣起来。
一匹马叫了,几十匹马随着叫。
“你是一匹母马。”卢辛说。
“叫唤的不都是母马。”娜娜说。
开始马随着娜娜叫床,他们还觉得新奇有趣。想象一下那情景,天高云淡的夜晚,一个女人因兴奋而咴咴叫,顿时数匹马也咴咴叫。那个夜晚还会平平静静吗?
睡在马肚子下面的人纷纷躁动,他们早想叫了,忍着没像马那样叫。他们都是正常的男人,从冻土地带来,温暖的草原气候,把冻僵的一切融化开来,情欲又是最易化开的东西。
水满之溢,熔岩已涌到地面,随处可以喷发。
从马咴咴叫的夜晚始,娜娜便觉得几十双眼睛盯着自己,火辣辣地发烫。她报抱怨说:“他们要吃了我。”
“他们又不是狼。”卢辛说。
实事上,吃人的动物不都是狼,吃法也不是一种方式。卢辛撞见一个人吃他的娜娜,用的就不是牙齿。
被吃者也没大喊大叫,好像挺情愿,也很幸福。
卢辛愤怒的枪口抵在吃娜娜男人的额头,哀求放生的倒不是这个男人,而是娜娜。
“娜娜你?”卢辛大惑。
“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像发情母马一样叫,因为他爱听。”娜娜一字一板地铿锵。
“你们俩过去……”卢辛深一步地问。
“一直,在你之前,在你之后,一直……”娜娜承认得大胆,承认得干脆。
全队的人目光一齐聚拢到卢辛的枪口上。
卢辛如同狼抬起头来对月亮一样,头仰到了极限,突然嗥叫:嗷嗷!——嗷!——!
众目愣然。
卢辛抬起枪口朝天,六颗子弹射出:砰!砰!砰!砰!砰!砰!
他歇斯底里地大喊:“走,你们走!”
一个男人驮着一个女人走了……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伤害,卢辛再也没带女人到花膀子队来。
“女人本就不属于一个男人。”卢辛因娜娜而生发感慨,随即又补充一句,“除非人人都有一个。”
项点脚对女人没感觉,对女人有感觉的男人他倒有感觉。他看到卢辛是条河,有枯水季节的干涸,也有汛期的奔腾,有冰封时的平静,也有桃花流水的涌动……卢辛即使能戒掉生命,也不会戒掉女人。此次去哈尔滨,就有了除卖狼皮以外的内容了。
“我去卖狼皮。”卢辛舌头发硬地说。
“大当家的,”项点脚说他深谋远虑的一件事,“我们得马上挪窑子(转移)。”
“为……为什么?”卢辛思维和他的舌头一样,不是很灵活。
“打了守备队部,就等于掏了狼窝,林田数马怎么能轻易放过我们。”项点脚说,“他要是联合大部队来讨伐呢,我们早早防备好。”
“唔,唔。”卢辛清醒了些,“有道理……那就等我回来,从哈尔滨回来,咱们就挪窑子。”
“不成,赶早不赶晚。”项点脚说。
卢辛睡到夜半酒就大醒了,一睁开眼睛,见项点脚坐在草铺边,迷惑不解:“你在这儿?”
“我等大当家醒来。”项点脚说。
“有什么事不能天亮说?”卢辛坐起来,“是不是挪窑子的事?”
“是。”
“你的意思连夜就走。”
“趁天没亮,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林田数马就休想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