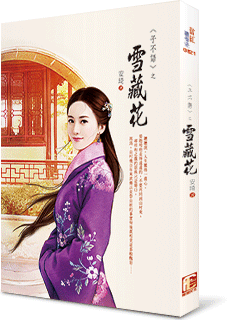苦菜花(冯德英)-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见这床被子还不如咱那床新些,就拿、拿……”
母亲听着听着不觉心里一酸,一把将孩子拉进怀里,泪也掉下来了……
花子等人帮着拉来一些梜萝、松柴捆子,给母亲一家挡着风雪。用松柴枝把地上的雪扫扫光,铺些野草,一家人围着坐在一起,互相用身体取暖。
母亲本来每夜都守着她的小儿子德刚,这次她却把秀子拉在身边,紧紧地搂着女儿,痛惜地轻声说:
“孩子,妈委屈你啦!打的痛不痛?”
秀子也紧抱住母亲,心里的委屈早烟消了,宽慰母亲说:
“妈,不痛。当时俺心里难受才哭的。”
“唉,好孩子!”母亲很感动女儿的懂事,“你记得妈打过你几次?”
“没打。妈,你从没打过我们。这是第一次,不,这次也不算。妈,你一次没打我呢!”
“好孩子!”母亲望着远处的白山头,“好孩子,妈是从不舍得打你们姐妹一下的。倒好,你们也听妈的话。你们若不听,妈整天打骂也没有法子呀!秀子,刚才妈是真气急啦。你知道,妈最恨干那伤害别人的事,哪怕是一点点的。孩子,记住妈的话:无论何时,给别人多作些好事,坏事是一点也不能干。哪怕自己吃亏,也不能占人家的便宜。闺女,懂吗?”
“懂。妈,我要学你,象你一样。”
……
虽然东方在放亮,可是这阴沉的山峦,却还是相当的黑暗。
第十七章
残暴的敌人,到一个村扑一个空,什么东西也找不到,饿急了就杀战马吃。河被冰冻涸,水井被泥沙填平,没有水喝,只得吞雪啃冰。他们如同饿狼扑食未获,越发穷凶恶极,到一庄烧一个庄。烧得浓烟遍野,遮住了冬天的太阳。没跑出的病人和老人、孩子,都被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成灰。凄厉的惨叫声,震撼着天地。
一天傍晚,敌人扑进王官庄。
十字街口,埋着一个草人。草人头上戴着泥坛子,上面贴着纸做的太阳旗,身上贴一张白纸黑字的标语:我是狗强盗,就要死了!
士兵们发现后,报告给长官。日军中队长下了马,瞪着眼珠子问翻译。这时围上一大堆人,后面的看不到直往前面挤,矮个的踮起脚跟伸长脖子,都象看马戏一样。
翻译把上面的字意告诉给中队长。中队长气得脸色发紫,胡子嗤起,骂着“八格牙路”,抬起钉底大皮靴,狠狠踢去……
几乎是同时,轰轰轰!泥雪崩起,烟雾弥漫,一片鬼子应声倒地。
这是民兵们的计策,秀子和玉子扎的草人写的字,十字街口埋下三个地雷,拉弦都拴在草人上。它一起动,地雷就都炸了。
敌人被地雷炸得晕头转向,简直是寸步难行。走到每家门口,先逼着伪军进去。有的家门后挂着手榴弹,有的锅灶里埋着地雷,一推门一烧火就炸开了……一直到小半夜,才算安静下来。
伪军中队长王竹非常沮丧。他回来一个人没抓到,什么东西也没有,自己人却被炸死好多,日军中队长也丧了命。他被大队长庞文叫去狠骂一顿,并逼他去找一个花姑娘来解闷。
这个最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大队长,平时总是吹嘘什么“人道”、“信义”,并自命是天皇子孙日本军人的模范化身。可也不假,庞文大队长真是日本军人的典型。他杀起中国人来,常常要换三四把素称世界第一的日本钢刀——杀的人太多,热血把刀刃烫卷了。他还最喜欢玩女人。有一次找不到年青的,抓到一个五十多岁干瘦的老太婆,他用皮带将她阴部打肿,实行兽性的蹂躏……
王竹憋着一肚子气恼,领着几个伪军挨家逐户去搜索,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见着。走到孔江子家门口,一听里面有人,他就抢先走进去。
这是村中唯一没跑的一家。那老太婆见有人来,认出是王竹,忙笑嘻嘻地招呼道:
“啊,大兄弟回来了。等多时啦,俺家江子没捎东西……”
“什么东西不东西,他也来啦!”王竹没好气地抢白一句,瞪起三角眼,满屋打量着。
老太婆见他来得凶,有点害怕;但一听儿子回来了,一股发财的野心又涌上来。
“啊,人来了!”她喜得象抱上金元宝,“大兄弟,俺家江子在哪呢?”
王竹早不听她叨絮些什么,正要向外走,却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哭叫着妈妈向里间跑。他一怔,也跟着闯进去。见到孔江子的媳妇,松一口气,心想:“这女人还不难看,送去了事……”就冷笑着说:
“哎,到我家去一趟,有点事。”
那媳妇紧抱着孩子,恐怖地说:
“不,不。俺不去,俺不去!”
“怎么不去?去有好事呀,谁也吃不了你!”王竹说着就想动手拉。
“不,不。你,你走开!”她惊慌地向炕里偎。
“他妈的,好说你不听!来人……”王竹跳上炕,一把将那孩子拉出他母亲的怀,抓着她的衣服拉下炕。几个伪军上来扭着她的胳膊向外拖。
那媳妇发疯地又咬又打又叫……
老太婆也扑上来,双膝跪下抱住王竹的脚脖子,哭着哀求道:
“大兄弟啊!看、看我老脸饶了她……”
“去你妈的!”王竹将她一脚踢翻,和伪军架着那媳妇就走。
哭嚎叫骂着刚要出胡同口,迎面逢到一簇黑影,最前面的一个,正是同运输队一块进村的孔江子。
孔江子一认出被抓的是他媳妇,照一个伪军脸上就是一耳刮子,骂道:
“你这小子胆大包天,敢欺负到我……”
“你又怎么样!”王竹气汹汹地抢上来。
“好啊!王竹……”孔江子气怒地抖着身子,忽地抽出手枪。
王竹也早把枪握在手里,恶狠地盯着他,枪口对着对方。
伪军们吓得呆若木鸡。那媳妇躺在地上,哭声哽住,脸色煞白。
一阵扑鼻的粉香掠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玉珍走来了。她卖弄风情地瞥视一眼,尖叫道:
“啊!你们在干么?动武吗?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快把枪收了……”
孔江子把枪插进去,忿忿地骂道:
“你他妈的不够朋友!这是对谁?”
“哼!吃醋啦?大队长要拉人,臭婆娘我王竹看都不稀罕看……”王竹说着也把枪收了。
“哟,就为这个呀!”玉珍松口气,轻蔑地瞅那媳妇一眼:
“哼!噁心人……”
那老太婆哭喊着赶过来,拉着媳妇哭哭啼啼往家走。孔江子浑身抽动着。
玉珍又变得阴恶地问王竹:
“我问你,小娟子一家可抓住了?”
“连根毛都没见着。”王竹丧气地嘟囔道。
“那老东西也没抓到?”
“有那老婆子倒好了……”
“哼!你们就有这本事。”玉珍冷笑几声,“好啦,别为小事生气了。都是自家人,何必那末认真?走吧,哥,和我看看咱们的房子去……”
孔江子看着他们走去的黑影,狠狠啐了一口。
他一走回家,媳妇就哭着扒到他身上,抽抽噎噎地说:“俺要跑,妈拉住不放!差点叫鬼子害了呀!你还当汉奸,连自己的老婆你都不要啦!我的天哪!你再不回心俺就没法活啦……”
唯财是命的老太婆,也顾不得问孩子带回来些什么,呜咽着叫道:
“江子啊!妈的腰也叫踢坏了呀!那王竹不是人哪!打我这把老骨头。嗳哟哟!痛啊……”
孔江子的眼里闪着浑浊的泪花,他重重地叹口气,头渐渐低下去……一声大洋马的嘶叫,惊得他突然抬起头,注视着黑暗沉沉的外面,全身一阵哆嗦……
第二天,敌人就出发了。不知为什么,他们没烧王官庄的房子,奇怪!
大雪飘飘,遮住人的视线。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天上地下,是山是田,四外灰浆浆的模糊一团。
王竹骑在马上,望着南山沟的方向,对王流子说:
“不知叔叔挖的那个洞,藏了什么没有?”
“哪会有?人家也不是傻子。”王流子看也不看地说。
“我看说不定。不藏人也许有些什么东西?他们怎么就料到咱们来?走,看看去!”说着王竹和王流子领着一伙人,向王柬芝的地洞奔去。
这洞王竹知道得很清楚。王柬芝详细告诉过他,以备有急事好联系。
王竹等来到一看,全是一片雪,什么异样也没有。王流子自负地说:
“我说不会有。看看,连个脚痕也看不到。”
“你知道个屁!洞口封好了,被风一刮,多深的脚印也被雪埋平了。别说还下着这末大的雪。”王竹又对伪军们喊道:
“快折松树枝子来,把雪扫光!”
扫去雪,发现洞口不久封过的新土。王竹高兴地叫道:
“快找家伙来挖!哈,一定有人或东西藏在里面。快挖……”
这洞修得可真不坏。洞是从山沟的陡坡向直里挖的。洞口用镶铁的木板盖着,外面敷上一层土就能封得严严的。里面靠洞口有个两丈深的陷井,井底埋着削成锋利尖子的木楔子。不知底细的人,一进去就非掉进去不可,掉进去就没命了。从洞口向里要拐几道弯,不知道的人也会到处碰壁。墙用石灰刷得很白,一般个子的人不用低头即可到处走,里面有几个气眼通出去,空气很流通。烟筒口巧妙地开在山顶上的一个大岩石下,烟刚冒上来就被出风吹散了,因此在洞里面烧火做饭,外面一点看不到。这洞里面又宽畅又干燥,真和幢小房屋一样。这是王柬芝找泥水匠,花了好几个月才修成的。
这几天王长锁和妻子躲在里面,一家三口过得挺舒服。杏莉母亲在灯下做针线,孩子在她怀里吃奶。王长锁躺在她身旁,拉着孩子的小手,引逗他松开奶头,格格地笑一阵。
“咱们过得倒挺好,不用东跑西颠的。”杏莉母亲感叹地说,“唉,这大雪天,娟子快生了,大嫂身子也不好,怎么受得住?我再三劝他们藏到这来,他们却不肯。反倒劝咱也不要待在这里头。他们是怕坏人哪!唉,人家到底不怕受罪。”“是啊!”王长锁接口道,“依我看这里也不太牢靠,被鬼子知道了,跑也没处跑。”
“谁会知道?”杏莉母亲不以为然地说,“那死鬼可精着哩,他肯告诉谁?娟子说怕王竹和王流子,可咱们每次都和那死东西一块躲到这来的,王竹他们谁也没来过……”
“你停停。听,什么响?”王长锁惊异地爬起来。
杏莉母亲停住手里的针线,脸色刹时惨白,惊叫道:
“有人挖洞?!”
沉闷的吭哧吭哧声,越来越响了!
王长锁忙抓起利斧,对妻子说:
“不用怕。看着孩子。我看看去!”
为着坚固,王长锁这次没用木板封洞门,而全用泥和石头堵了一层又一层。
他走到洞口,只听噗哧哗啦一声响,洞口开了一个小窟窿。他忙闪到一旁,心象打鼓般地崩崩跳着。
外面沉寂片刻,一颗戴钢盔的脑袋伸进来,喊道:
“喂!里面有人没有?快出……”
王长锁狠狠地抡斧劈去。崩哧一声,那脑袋和西瓜一样,滚进陷井里了。
外面慌乱一阵,就向里打枪。
王长锁躲在一旁。
外面又开始挖洞,渐渐洞口全开了。一个伪军端着刺刀向里进,噗嗵一声,掉进陷井里。
王竹这才恍然大悟:只顾忙乱,把陷井的事忘记说了。他马上把怎样躲避的法子告诉士兵,命令他们再往里冲。他自己似乎有过教训,站得远远的。
两个伪军抬着一块大木板,胆怯地从洞口向里推。觉着搁上对岸了,就又向里冲。可是上去的一个,刚迈出两步,轰隆隆,连板子带人,又滚下陷井去了。
原来王长锁在暗中看得真切,见敌人踏着跳板朝里进,搭脚猛一踢,把板子和伪军一齐掀进陷井里。
外面又大乱起来,不敢再进,又打枪又摔手雷。可是子弹扎进泥里,手雷掉进陷井,倒把敌人的尸首炸得更烂了。
于是,王竹下令放火熏……
王长锁见洞口堵上草,就提着斧头走回来。
杏莉母亲已哭好长时间,一见他回来,就哭倒到他身上。“孩他爹,咱们要死了!”她悲痛得全身在搐动,“可咱不能看着孩子死啊!他没有罪呀!”
王长锁没有流泪,擦擦脸上的汗,看来是愤恨和胜利的骄傲在主宰他。他把她的缕缕乱发理好,镇静地说:“别哭,哭什么!咱们哭一辈子,这二年才有个笑的日子。你没听姜同志说,在敌人面前哭,那就是软、软弱。咱们一辈子就吃了这两个字的亏,把莉子也连累死了!眼下咱们要死啦,不能让它缠住。死要死个硬气!”他很激动,眼睛有些潮湿。但马上又睁大眼睛,“罪,谁有罪?孩子没有罪。你我有罪?没有。受苦人谁也没有罪!鬼子、汉奸才真是犯了天大的罪!咱们死也要惩治他几个!”
杏莉母亲渐渐辍止哭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被她不惜一切酷爱着的人,说出这一席话。使她觉得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但可爱而又可敬了。她紧紧抱着吃奶的孩子。孩子在母亲那温暖的怀里,渐渐地幸福地睡去了。“我生在富家,嫁在富家。”杏莉母亲抽噎着,轻声地说,“过去我不知道,后来才慢慢明白这些人是些什么东西,是最下流的胚子!外表上四面光八面圆,背地里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他们都是两条腿走路的畜牲!为自己,能不要亲生爹娘;为自己,能把老婆孩子卖掉……反正他们活着,就是为自己,把别人的一百颗心挖出来吃掉,也不觉得心疼。我总算把这些人看清了!”她擦擦悲愤的泪水,激动又悲壮地说:
“咱们一家,死就死吧!做个好人死了,强似劣人活着。大嫂人家为大伙、为工厂,受尽那末多苦,遭了那末多罪,可什么也不说给鬼子。咱们怕什么呢?什么也不怕!死吧,反正有人替咱们报仇!”
王长锁几乎是以胜利者的高傲口气说:
“已经够本了,被我杀死三个!再杀,就是赚的啦!
……”
一股浓重的黑烟冲进来。一切变成黑暗了。洞里没有空气了。人,一家三口人!都在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