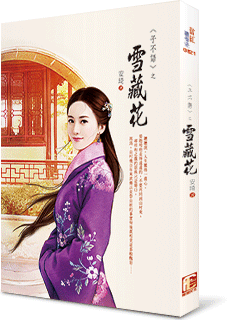苦菜花(冯德英)-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点去的……
王长锁按着王柬芝的吩咐,到村长那里开了张假装到姑家去的通行证,实际上是把一个小包裹送给在道水的王竹。王柬芝说,这是王竹的媳妇和妹妹玉珍托他找人送给王竹的钱和几件衣服。虽说王唯一家是汉奸,可是看在兄弟情分上,加上女人们的苦苦哀求,他王柬芝不能不可怜家破人亡的侄子啊。当然,他也知道他们是坏人,不好亲近,故此为避免外人怀疑和找麻烦,叫王长锁背着别人的眼睛,行动要特别谨慎小心。他又暗示出,万一要是碰上八路军查问,切不可说实话,否则,他们——连杏莉母亲在内,性命也将难保!
杏莉母亲和王长锁,虽然不知道那个包裹里夹的是王柬芝给他上司的密信,但背着人偷偷地到鬼子据点里去,送东西给当了伪军的王竹,这不明明是和八路军做对吗?更何况,王竹当伪军小队长,吃、穿、花是不愁的,用不到家中送钱和衣服给他,王柬芝这不是明明白白在撒谎,叫他去干坏事吗?啊,要是被人家发现了,会当汉奸治罪的,多末危险啊!不去吧,刀柄攥在王柬芝手里,惹恼了王柬芝,他们马上就要完了啊!为着他们的私情不被外人知道,为了他们的孩子杏莉,他们顾不得这件事有多大危险,违背良心去干了。自长锁走后,这两天她真是提心吊胆,坐卧不宁,怎么他还不回来呢,莫非叫八路军捉去了……
杏莉母亲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听到有人敲门,高兴极了,一定是长锁回来了,不然谁会半夜三更来敲门呢!她眼睛里闪着欢悦的泪花,甩开被子爬起身,匆匆忙忙地去开了门。由于黑布帘遮盖着窗户,屋里漆黑一团,什么也分不清。
“啊,你可回来了!”她迎着一股寒气,向前扑去。
来人一声不响,张开两臂紧抱住她那只穿着内衫的身子。这样沉默好一会,对方身上的寒气驱散她身上的温暖,使她从狂热的激情中镇静下来。她开始觉得不对头,这双一刻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赤臂的细腻的手就不对。她一摸到那流油的洋头,象被蝎子猛螫了一下似的,立时惊叫起来:
“你是谁?……啊!你这东西!快滚开……”她急忙挣脱身子,恐惧愤怒地盯着宫少尼。
“嘿嘿!不中意?我不比那个老长工强?”他说着逼向前来。
他的冷笑使她全身发麻,她嘶哑地喊道:
“你走开!快滚!……你干什么?我要叫人来啦!”
他一动不动,冷冷地说:
“好哇,叫去吧!走,找村干部,找姜永泉去。嘿嘿!我倒不怕,有个人当上汉奸,到道水送信还没回来,可要论个什么罪?”
“你说什么,谁是汉奸?!”她惊吓地叫道,可是马上明白了。啊,到底被人知道了!她恐怖地颤悸着。一刹,她又镇静起来:“这坏种早在打我的主意,他是想用法子把我压住……不,他不一定知道……”她想着,转用强硬的口气说:
“你别血口喷人!谁当汉奸?你凭什么证据……”“哼哼,还装佯吗?”他冷笑着,加重语气说,“偷汉子是要活埋的,可你们倒这样舒服!想一想,王柬芝是傻瓜,能这样轻轻饶过你们吗?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王长锁假装走亲戚到鬼子据点给王竹送信,这是假的吗?!”这几句话确实打中要害,她立刻觉得浑身瘫软下来,眼里直冒金星。宫少尼见她软下来,就上前搂抱她。
杏莉母亲再没有反击的力量了。她心里千头万绪,象乱麻一样纠缠着。她懊悔,不该上了王柬芝的当,死就死个干净,可是谁叫自己贪生,又落上当汉奸的罪名。她现在才感到,这汉奸的罪名是多末可怕!王柬芝就是为着这个才饶了她和王长锁的啊!她恨死了他们。她决不能再屈服。她不能给他——这条狗来糟蹋!她又振作起来,把向她伸来的手狠狠摔开。
“好啊,好啊!瞧着吧,我马上报告民兵,抓起你们这些汉奸!你看到王唯一是怎么死的……”他说着就要向外走。
啊,天哪!生死就在这一关,再晚一点,生命线就要断了。那末王长锁和她,还有孩子,不都完了吗?!可怕呀,和王唯一一样!不,不能啊!为他,为孩子!她,她顾不得自己了。她流着苦泪,哆嗦着无力的身子,上前拉住他的胳膊,拚尽全力从牙缝中挤出来:
“表弟,可不能啊!我求求你……”
他淫猥地笑了:“是嘛,只要表嫂看得起我,我还能看着叫表嫂完了?我宫少尼才不是那样狠心的人……”
他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她抱上炕……
柔弱的女人,已失去知觉,变得象根木头一样麻木了……
第四章
敌人打来的消息传得一天紧似一天,象敲破锣一样难听的飞机声,也时常出现在天空。
今年冬天特别冷,雪下的有两尺多厚。早晨起来,风门都推不开。而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象瓦一样,堆叠在一起。鹅毛大雪还在继续下着,看起来老天爷真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那山上地下全盖上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连在一起,白茫茫地看起来怪美的。唉,若是老天爷下这末多白面有多好哇!
真的,据说很早以前就是下白面的,人们就吃它。有一天,天上派下一个特使,要看看老百姓怎么过的日子。这使官变成一个讨饭的病人,走到一个老太婆家里。这婆子真是个吝啬鬼,讨饭的向她要块饼吃她都不给;她却把雪白雪白的面饼给小孩子当尿布铺。这下可气坏了天使,回去禀告给天老爷,再不下白面而是下雪了。从此,大人小孩都咒骂这个自私自利贪而无厌的坏老太婆。
起先人们不耐烦听干部们说什么:鬼子杀人放火呀,东西要埋藏好呀,人要准备跑上山哪!……我的天,这末冷的天,跑出去娃娃不要冻死吗?经过干部们磨破嘴唇的劝说,大会小会的开,积极分子民兵的带头,总算说动了大多数人,把粮食藏起来,人准备着逃上山去。
母亲的南屋里,炕上地下挤满了人,正在开干部会。
人们用力地吱——吱——抽烟,屋里满是灰蓬蓬的浓沉烟雾。娟子、兰子被烟呛得睁不开眼睛,直淌清泪。不顾冷了,娟子把北窗打开一扇,一股西北风冲进来,她长长喘口大气,觉得清凉的多了。
区农救会长姜永泉刚从区上回来,他询问着每个部门的情况,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接着说出自己的意见。众人再讨论一回,一般的事情商量个差不多了,然后他又提出王柬芝的问题:
“从表现来看,他还很开明,咱们是欢迎开明士绅参加抗日的。上级说,知识分子往往很明理,有些气节,咱们应当好好团结他们抗日。团结一切力量嘛,只要是中国人,他不当汉奸,咱们都应当团结他们打日本。不过有团结也要有斗争,他在外面多年,说是教书,可也很难实信。他哥被打死,王竹、王流子还在外当伪军,说不定他安的什么心,咱们要防备些才是。德松,你再到他家看看,藏东西的人手不够咱们可以帮忙。”
“前儿我就到他家去过了。”德松答道,“王柬芝说他已挖好地洞,东西也都藏了。”
“对有些人实在不愿走,咱们也不能强迫。”姜永泉说,“就象秀娟她四大爷吧,也是老实人,就是想不开,也没法子。
唉,这样的人不见血是不落泪的。”
“姜同志,我看再叫俺妈去说说吧。他生她的气呢。我妈向他赔点不是,再劝一顿,也许能行。”娟子恳切地说。她从不叫他老姜,为什么,她也说不上。
“对啦,这倒是个法子。说转这个老人,能影响一些人。”姜永泉很同意娟子的意见,可又担心地说:“就不知大娘肯去不?”
“嗳呀!俺大婶好说话,咱们一动员,她准去!”兰子充满信心地说道。
大家都说这个法子可以试试。接着又详细研究了民兵怎样掩护群众转移……。最后姜永泉又对大家叮嘱道: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去做。这几天要好好加强岗哨。我去看看七子哥怎么样啦……”
姜永泉从狭窄的胡同转到大街。他习惯地向四周扫视一眼。街上冷清清的,看不见行人的痕迹,就是有人走过,脚印也马上被雪埋没了。西面街口上,一个民兵背着枪在放哨,象个雪人一样。民兵不去打掉身上的雪,因为一打掉又下上了,反倒容易化,还不如任凭雪一层层披在身上好些。这时村外走来一个人,走到民兵前停住一刹,马上又朝前走了。
姜永泉好奇地站着等那人走过来。渐渐看出那人背着个白包袱,只顾埋头走路,没发现有人在注意自己。走到跟前,姜永泉认出是王柬芝的长工:
“这不是长锁叔吗?上哪去啦?”
“哦!是你。”王长锁略有些吃惊,接着笑笑说:“唉,好冷啊!走亲戚才回来哩。”
王长锁拐弯向南走了。姜永泉看着他的背影朦朦胧胧地消失在大雪里,就向七子家走去。
七子的家是在街北一个很别扭的深胡同里。姜永泉非常熟悉这条路,很快就走到门口。
一个瘦弱的女人出来开门,一见来人,忙亲热地招呼道:
“嗳呀!真稀罕,多日没见着啦!快里面坐吧!”她忙拿起一把条帚给他扫掉身上的雪。
“谁来啦?”七子问道。
“是老姜啊!”她快乐地回答。
“快上炕来吧!”
七子起身让地方,姜永泉忙捺住他:
“快别起来,我坐这就行啦。”说着坐在炕沿上。
这屋子太小了。一条能睡两人的炕,铺着一张用布补过几块的破席。七子靠墙躺着,身旁放着一辆纺花车。显然,姜永泉没来时,七子的妻子正在纺线。
“好点吗?”姜永泉亲切地问七子。
“唉!还不行。又化了脓。昨黑夜一宿没睡着,身上烧的烫人!”妻子叹口气,痛苦地说。仿佛伤口是在她身上似的。
“也不怎么样。天冷了,就重些。”七子岔开话题。关切地问:“老姜,工作都安置好了吗?情况怎么样啦?”
“工作都安排好了,情况是很紧。你别惦记这些,安心养着吧。”他安慰着,又向前凑凑:
“来,我看看伤口。”
“算了吧,怪脏的。”七子说。
“哎,我怕什么?来,嫂子!帮帮忙。”
姜永泉同她掀开被子,七子的大腿根底下,有个碗口大小的疙瘩,肿的象饽饽一样。在包着的白布边上,还流着黄水。姜永泉用手轻轻按了按,皱起眉头说:
“肿的真不轻。区上也找不到药。我和交通①说了,叫他务必到军队上要点来。”
①交通——负责联络传递信件的人,类似通讯员。 盖上被子后,七子不过意地说:
“就算了吧,还叫人家操心。”他又烦恼起来:“唉,起不来炕真急死人,鬼子又要来了,什么也干不成!”
“你安心养着吧,别犯愁,”姜永泉说,“敌人来了,用担架抬着你跑。”
“这倒不用啦,她给我挖好一个洞。”
“洞,洞怕不保险吧?被坏人看到……”姜永泉疑虑地望着七嫂子。
“没关系,”她笑着说,“谁也不会知道。是德强兄弟和秀子妹夜里帮我挖的……”她凑在姜永泉耳朵旁,告诉他洞的地点,然后又大声说:
“到时我背他到洞里去。这大冷天,出去也不行。”
姜永泉看着他两口子,心里很感动。
他两人在外表看来很不一样。七子是个又粗又高的汉子,方圆的大脸上长满麻子,一对土黄色的眼睛,两边镶着深密的皱纹。女人恰恰相反,又细又矮,干黄的脸,样子象有病,其实是从小营养不足的缘故。她比丈夫小七八岁,是前年跟父亲从莱阳逃难来到山区的。已经三十多岁的七子,还没找到媳妇,大家说合着,她就跟了他。第二年,她父亲就回莱阳老家去了。
从他们结合的那天到现在,两个人从没吵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七子虽力大如牛,性子刚直,可是对待好人,却软绵绵的象个老妈妈。他俩都是在苦难里长大的人,互相体贴;都是一样的心肠,互相疼爱。可就是她不生育,因为她有病,是从小饿坏的。为此她哭过,觉得对不起他。但七子从不怨她,总是叹口气,安慰她说:“唉,要孩子做什么?家里盛不开,也养活不起,这样倒松快些……”其实他何尝不想有个孩子呢!
七子的父亲是烧炭窑的,他自小就跟着喝炭灰。有年春天大地震,窑塌了,父亲和一些工友都砸死在里面。窑东家是王唯一,人死了一个钱不赔。七子娘俩把破柜腿砍去当棺材,把父亲埋了。后来王唯一做出一副慈善相,说是可怜孤儿寡妇,把七子母亲弄来当做饭的佣人,住了半年,王唯一就把她卖给了东海的人贩子。七子十二岁给王唯一放羊,大一点又回到窑里做工。他是姜永泉来王官庄最先发展的一个共产党员。
姜永泉这时看着他,想起他入党时的情景。
一个夏天的中午,太阳炙烈地晒着。姜永泉把牛赶进深草洼里,同七子坐在背荫的岩石上。
“你不怕刀抹脖子吗?”姜永泉问道。
七子瞪大血丝的眼睛,坚决地说:
“咱不怕!过刀山走火海跟着党。松包不是穷人的骨头!”
七子把手中一只野鸡的头,格吱一声扭下来,鲜红的血,喷在他那赤着膀子的黑疙瘩肉上。他把鸡向深山沟用力一摔:
“我七麻子要有三心两意,就和这野鸡一样!……”
姜永泉从回忆中醒转来,又安慰七子一番,才站起身说:
“七子哥,我走啦!有什么事,叫嫂子找我们吧。”
七子拉着他的手,忽然说:
“老姜,你留几个手榴弹给我吧。”
“你要它做什么?”
“不做什么。急着要用的时候,用用。”
“那好,回去我叫人送几个来。……好好躺着,别起来啦。
……嫂子,再见啦!”姜永泉告辞着向外走。
“老姜,再来啊!”七嫂子留恋不舍地亲切地说着,直等他走出胡同拐了弯,才轻轻关上门。
吃过早饭,母亲抱着孩子,手里提着一包鸡蛋,走出家门。嫚子被凛冽的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