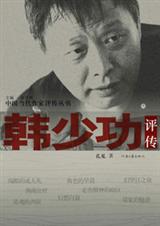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着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不知文”)的糊涂观念。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着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进入中国知识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
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宫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荡,“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流社会的华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的符号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腿无毛加上一根绳子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色官员的身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毛泽东一条毛巾既洗脸又洗脚,一件睡袍补了百多个补丁,对不实用的所谓审美如果不是反感,至少也常有轻视,包括多次指示北京中南海里不要栽花而要种菜。墨子遗风就这样一次次重现于现代的理想主义追求之中。
但墨子失败于他对声象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道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深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乐)而死不服(节葬)
“,日子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是一个象符的弱视症者,代表着中国政治史上最早的感觉自绝。或者说,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部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着大众内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因此,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代沟
就人的基本品性而言,我根本不相信什么“代沟”,正如我基本上不相信性别、族别会构成什么“沟”个人的差别肯定比群类的差别更大。
正如我们在一些现代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墨子的形象和思想,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一些颓废者身上看到杨子的形象和思想先秦时代的杨朱,如果真是《列子》中描述的那样,其利己主义理论体系就比它的后继者们来得更完善、更周密、更雄辩,可惜后继者们没有多少人熟悉。想想看,杨子与今天的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墨子与今天的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几千年之间都没见出多深多宽的“沟”,如何邻代之间就有了什么“沟”?
“代沟”常常是一类外在形态给我们的错觉。我接触过一些少年。他们也是人,一个鼻子两只眼睛,饿了吃饭,困了睡觉,没有特别到哪里去。别看他们头发不是剃光就是长发披肩,头发不是染红就是染蓝,穿着黑亮亮的皮夹克,戴着墨镜和臂上纹了身,一群群飙起摩托来横冲直闯惊天动地烟浪滚滚,活脱脱就是流氓相,其实为人处世还是不乏友善,说起话来还多有腼腆甚至天真,被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子蹬了,同样魂不守舍茫然无措,同样鼻涕眼泪一把流,根本不会去杀人放火炸掉公安局,说不定吃块冰激凌就乖头乖脑去上班打工。也就是像个流氓而已。
他们有时候也比谁都超凡脱俗,义务到公园里去捡白色垃圾呵,骑着脚踏车为青海草原上保护藏羚羊募款呵,一高兴就在吧台上喝着可口可乐起哄要去奥运会当义工呵……好像是一群纯洁天使,生下来就是一个胸怀全人类的命,就是关心奥运会和藏羚羊的命,大票子掏出来眼都不眨,简直让我这个混迹其中的俗人愧死。不过,处久了,也可知道他们这颗爱心大多是远程爱心,在近距离范围内不一定有效。
比方父母这次给钱少了,不能让他的电脑从奔腾三升级到奔腾四,他们同样会大吵大闹。比方说一个老同学穷得没脸面来参加派对,另一老同学打工时落下个骨折,他们说起来也可能是一句“真他妈倒霉”就打发掉,没准备把这些同学当藏羚羊保护一下。
我的感觉是:他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其实同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差不多。血型和基因差不多,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差不多,对食和性的需求差不多,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来观察,他们与其相邻的长辈和晚辈,更像是同代人。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同,不过是他们外形异于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仅此而已。
我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性相近而习相远也”。我曾经将其试译成similar in nature and different in culture,给它押上了韵。我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共时性比较,比如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同样适用于历时性比较,即不同年龄之间的比较。“习”是文化使然,表现为一种生活的形式,比如一种衣着外观的差异,却并不等于各代人之间的自然本“性”相殊。在很多情况下,“有诸内必形诸外”或“形诸外必有诸内”的古训不一定灵验,新一代人无论如何新异,多是外象的更迭,并不意味内质的切换我们不必对任何年长或年少的人疑虑重重。
生命
一个人活着的基本条件,除空气之外,是粮食、净水、衣物、药品,人道主义者及其援救机构都是这样规划的。可能很少人会想到,感觉像粮食一样重要,甚至比粮食更重要。
事实上,一个人忍受饥饿可以长达六七天,如果有特别的养息方法,一个瑜珈功练习者甚至可以成功绝食月余。但一个人常常难以忍受感觉的空无。在极地雪原上,四野皆白,昼夜无别。正像在单人地牢里,满目俱黑,昼夜不分在这样一些感觉不到空间和时间的地方,一个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知识丰富和逻辑严密都不管用,人很快就会神经错乱精神崩溃,若能坚持一周便是奇迹。一个到过南极洲的探险队员就是这样告诉我的。老木也曾心有余悸地告诉过我:他的未婚妻移民到香港去了以后,他去不了,曾经想偷渡,带足了几天的干粮和饮水,藏进某机床厂发运给香港的大货箱里,让协助者重新钉好箱盖,用这种方式躲避边境检查。这种大货箱里装着大型机器设备,是当时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弯头角脑里还有藏人的空间,相当于单人牢房。老木没料到当时中国生产秩序混乱,铁路运输太不正常,很多货箱标签上的日期根本不管用,在站场里一压就是个多月甚至几个月。
这些偷渡者藏身的货箱如果压在货堆的深层,头顶和四周全是笨重如山的货箱,是钢铁组成的挤压和黑暗,粮尽水绝以后,别说想逃出来,就是狂呼乱叫,也可能无人听见。
老木在那里只身躲了几天,可能是五天也可能是八天,因为昏昏沉沉不可能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他发现外面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伸手只能摸到粗糙的箱板和箱架、缠了草垫的机床、自己的水壶,还有黏乎乎的东西,好一阵才嗅出是自己的屎,已经糊满了裤子。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能清醒听到自己的呼吸加快,听到自己脑子里发出嗡嗡嗡的尖啸,听到自己全身血管噼噼啪啪简直是一串炸响了的鞭炮……终于用尽全身气力狂叫一声:“救命呵”眼前一片炫目的白炽,事后才知道那是木箱开了盖,是几个搬运工人出现在面前,是在一个离广州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货站。他说他实在受不住了,幸好出来了,更庆幸自己藏身的货箱就靠着路边,箱缝里传出的喊声容易被人听到。搬运工人告诉他,有些货箱运到香港得停停走走好多天,前不久香港那边的工人开箱时,发现过尸体的恶臭和人的白骨架子。
老木的偷渡经历,使我较为容易理解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某些东欧国家的集中营,还有不久前美国关押阿富汗“基地”组织成员的关塔那摩基地。在那些地方,最有威力和最有效果的刑讯并不是拷打,而是使用一些不损皮肉的文明用品:黑色的眼罩,胶制的耳塞,厚厚的口罩和手套,其目的是强制犯人不看、不听、不嗅、不触任何东西,对外界的感觉被全部剥夺。如果拷打、恐吓甚至饥饿一类邪招不足以让犯人招供的话,感觉剥夺却常常能让他们乖乖地开口,包括大喊一声“救命”。
在狱方使用了这一方法以后,那些刑讯者和被刑讯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生命存在的含义,更理解一声鸟叫、或一片树荫、或一个笑脸:它们是活下去的全部希望。
空间
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张。
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点点呵……”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的轻松气氛和亲近关系,必须在一种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几何形式里才可能扑面而来悄入人心。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逼仄,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他与众多同行们反复观察和试验,发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无大量伤害同类的习惯”,而猴子的互相屠杀、狮子的互相虐待、鸟雀的互相激战、刺鱼的互相攻打,“通常发生在最拥挤的动物笼中,”因此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说,人类不过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猿”;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都市社会,是一些过分拥挤的“超级部落”。这种部落中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恰当的生物学水准,结果必然是:战争、暴乱一类大规模的杀人形式几乎难以避免,奴隶制、监禁、阉割、流产、独身等也不能不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十分残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人们投入这些超级部落,寻求创造的机会或者统治的地位,寻求群体的协作或者独行的自由。他们中间毕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成功也可能只是一种成功感,不过是一种空间比量后的心理幻觉。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为自己的居地而自鸣得意,历数都市里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楼、博物馆、大剧院、音乐厅以及大人物其实他们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享受那些设施,一辈子也可能见不上什么大人物,与乡下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些东西就在身边呵,就在大墙那边呵,就在马路那边呵,这就足以让他们油然多出几分自豪和放心。这种心态也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