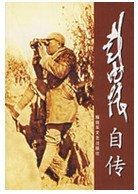自传编零-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幺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党为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幺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面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作。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一九五三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幺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十,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为什幺?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同样是一九五三年,似九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
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沉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幺也没说。为什幺?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⑤,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
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眼湿。给我机会在写作上再来补过赎罪。
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即无任何一个集子肯定意义,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为大会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
这勉励,只增加我感激和惭愧。这经过,即家中人我也没有说,只考虑我应当怎幺办。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室。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
照我这幺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幺多。
另一方面,即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工作不可免遇到许多困难,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出于本身的。来自外部,多由于不明白许多工作是崭新的、创始的,带试探性,不可免会走些弯路,必须不断改正,才可望逐渐符合事实,得出正确认识。正应合了前人所说“民可乐成而难创始”,必见出显明成绩后,才会得到承认。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幺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幺个人兴趣了。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化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幺?因为封面小花锦是十八世纪中期典型锦,什幺“担保”谎话,什幺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刻丝,是全国著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千元一部。六三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有个“天宫”刻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干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干隆题诗,即信以为真。我当时正在丝绣组作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那幺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为什幺?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五、故宫以前化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干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⑥,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士女图》的时代,《韩(氵晃)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
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因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我还是毫无发言权。可是我却深信,为新的文物鉴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试探,由于种种限制,尽管不可免会有各种错误,总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质基础,不是凭空猜谜人云亦云的。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种主要鉴定方法。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作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这里自然包含一点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我的学习,却近于由无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个人血压总在二百以上,一天还有一二小时心脏发痛,搞工作的愿望即再顽强,总还是不免要受体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难以为继。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⑦,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六三年政协大会,我前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⑧,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文化部或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那么一份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放后⑨,还能抢时间,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作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作下去。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作“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如我这个工作,在新社会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还犯了严重过失,就把我改为一个普通勤杂工,以看守陈列室,兼打扫三几个卫生间,至多让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将很愉快、谨慎、认真,来完成新的任务,因为这也近于还我一个本来面目。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作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屈的。如果在新指示推动下,本馆工作将进入人事精简时期,商讨到职工去留,从客观说,我的所学,在新社会博物馆工作中已并没有多大需要,从我体力说,又实在担负不了工作任务,只近于指指点点说空话,凡是要用体力解决的我都已办不了,高血压又已定型,身体报废不过迟早间事,为了国家节约,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人数之内,我也将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馆中新的改陈要遇到一系列常识问题不好解决时,还是会就我头脑中记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外单位美术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应从“劳动文化”着眼,以劳动人民成就贡献占主要地位,求措词得体有分寸,感到难于下笔,要问到时,我的点点滴滴常识,大致还得用,一定也会就记忆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说去。在完全尽义务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点。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