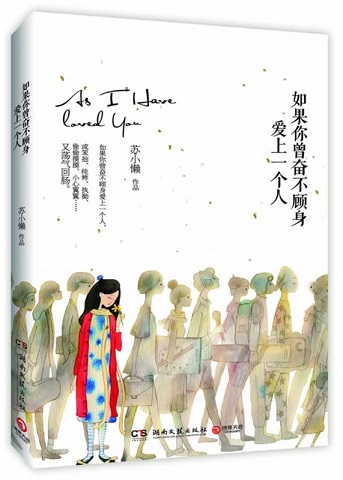个人的体验 作者:大江健三郎-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话的假眼医生那里感到了深不可测的威严,但医生不过问了句:“怎么样了?”
“还活着。”鸟答。
“那么,动手术?”
“说是在等手术,但可能这中间就衰弱死了。”鸟感到自己向上仰着的脸一阵红。
“那很好呀。”假眼医生说。
鸟的脸渐渐红成一片,嘴唇痉挛般抖动不已。鸟的极端反应,使假眼医生的脸也红了。
他的目光直盯着鸟头上的半空,喋喋地说:
“婴儿的脑病,我还没对您夫人说,只说是内脏不好。本来脑也是内脏的,所以不是撒
谎。完全撒谎,可以应付一时之急,一旦谎言败露,就必须再编另一个谎言了。”
鸟说:“啊。”
“那么,再见。如果有什么事儿,别客气。”
鸟和假眼医生相互端端正正地鞠躬致礼,然后侧肩走过。鸟回味刚才医生的寒喧:那很
好呀!等待手术的过程中衰弱而死,也就是说,既避免了抱回一个手术后变成植物人的孩
子,也避免了亲手弄死自己的孩子,只是站在一旁等待孩子在现代化的病房里洁净地衰弱死
去。并且,在这期间,忘掉孩子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是鸟的工作。那很好呀!深暗
的羞耻感又复苏了,他觉得身体僵硬了起来。他和身旁来来往往的那些穿着各式颜色合成纤
维睡衣的孕妇和刚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们,也就是肚子鼓鼓蠕动着的人们和仍未脱离类似记忆
和习惯的人们一样,错着小步向前走着。鸟的大脑里的子宫,仍然包孕着一个不停蠕动的羞
耻感觉的硬块。与鸟擦肩而过的女人们,傲然地盯着鸟,每当这样时刻,鸟总是懦怯地低下
头。这就是目送鸟和奇怪的婴儿乘急救车出发的宛如天使似的那群女人。一个荒唐的念头突
然袭来,那以后,鸟的孩子的一切,可能她们都知道。也许,她们像巫婆一样,在喉咙里这
样咕哝:现在,那孩子被收容在高效率流水作业的婴儿屠宰工场,正安详地衰弱下去,很快
就会死的。那很好呀!
众多婴儿的哭声,旋风似地卷起,袭来,鸟慌慌张张扫视四周的眼睛,与婴儿室并排排
列的婴儿床上的孩子相遇。鸟逃似的一溜小跑。那些婴儿好像都回头盯着鸟。
在妻子病房的门前,鸟认真地闻了闻自己的手、胳膊、肩,然后是胸。如果妻子在病床
上把嗅觉锻炼得很敏税,闻出了火见子的味道,那鸟陷入的纠纷将会多么复杂呢?鸟回头看
看,想要准备好逃路的样子。而那些身着睡衣的女人,伫立在走廊的暗淡角落里,皱着眉,
正盯着鸟。鸟想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但最终只是无力地摇摇头,转过身,怯怯地敲门。鸟
是在扮演突然倒霉的年轻丈夫的角色。
鸟一走进病房,背对着绿叶茂盛的窗子站着的岳母,支着的两腿盖着毛毯,头抬着,黄
鼠狼似的向这边窥视的妻子,在闪闪辉映的绿色中,都一副受到了惊吓的神情。鸟想,这两
个女人惊恐悲伤的时候,脸形和体形的角角落落,都明显显现出血统相承的关系。
“对不起,惊了你们了。我敲了门,但敲得很轻。”鸟这样向岳母解释着,走近妻子的
床边,妻子叹息似的说:“啊,鸟”,渐渐溢满泪水的疲倦的眼睛凝视着他。现在,他的妻
子一点儿妆也没化,皮肤黑黑的,鸟觉得和数年前第一次与这位男孩打扮健壮的网球选手相
遇时的感觉很像。鸟感到自己暴露在妻子的视线里,简直无处躲藏,于是,便把装葡萄柚的
袋子放在毛毯边,弓着腰像要躺起来似的,把鞋贴床边放下。然后,他颇怀怨恨地想,要是
能这样像螃蟹一样,边爬边说话就好了。接下来,鸟勉强露出一丝微笑,直起身子,故意做
出唱歌般轻松的调子说,“哎,疼痛已经完全止住了吧?”
“周期性疼痛还有啊,时不时的还出现痉挛性的收缩。不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情绪
也不好,要是一笑,立刻就疼起来。”
“最糟糕的时候呢。”
“嗯,最糟糕的时候呀,鸟。”他的妻子说,“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假眼医
生解释过了吧?”鸟还是想保持唱歌似的语调,同时又像没有自信而一劲儿回头看教练员的
拳击手似的,把目光溜向岳母。
岳母站在他的妻子对面,床和窗狭仄的空隙间,她向鸟发送秘密信号。鸟不清楚信号的
具体含义,但要他对妻子什么也不要说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孩子究竟怎么样了呢?”妻子说,声音里满含着自我封闭的孤独气氛。
鸟明白了,满腹疑团的妻子,用同样的调子,同样的言词,已经孤独无依地喃喃自语了
数百次。
“是内脏不好啊。医生没有给详细解释。可能还在研究吧,那座大学附属医院,实际上
也够官僚的了。”鸟说,同时他闻到了自己的谎言的恶臭味。
“需要那么认真检查,我想是心脏吧。可是,为什么会心脏不好呢?”妻子无可奈何地
说。鸟觉得自己又想学蟹爬行。于是,鸟故意用一种少年气盛的粗暴语气对妻子和岳母说:
“因为是专家在调查,目前,只能相信他们。我们纵或怎么猜测,也无济于事。”
说完,鸟毫无自信的不安的视线移向床的方向,原来妻子一直闭着眼睛。鸟俯望着妻子
的脸,只见她眼睑肌肉松弛,鼻翼隆起,还有大得不匀称的嘴唇。他不安地想,还能够重新
恢复平素的均衡吧?妻子仍然闭着眼睛,身子一动也不动,像是睡过去了。然后,突然从紧
闭的眼睑涌出了一汪泪水。“孩子生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听到护士啊地叫了一声哟。因此,
当时我想,可能出现了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了。可是,接下来那院长先生好像很高兴地笑了起
来,所以我也不清楚那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麻醉剂效力过后,我睁开眼睛时,孩子已经坐
上急救车出发了。”妻眼睛闭着,说。
那个毛烘烘的院长!鸟的怒火直冲喉咙。这家伙竟在麻醉了的患者耳旁窃笑骚扰,如果
这是他吃惊时的习惯动作,我就提根棍子在黑影里等着,想法让他发出更尖更高的笑声。但
是,鸟不过是一时逞孩子气而已,他知道自己手上什么棍捧也没有,也不会在任何暗影里埋
伏。鸟必须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纠弹别人的必要依凭,为了求得妻子谅解,鸟说:“我带
来了葡萄柚子。”
“为什么要带葡萄柚子?”妻子寻衅吵架般地说。鸟立刻明白自己失策了。
“啊,是呀,你讨厌葡萄柚子的味道呢。”鸟自我谴责说:“为什么我要故意去买柚子
呢?”
“我,孩子,你从没有放在心上,是不是?鸟。你最上心考虑的,不就只是你自己么?
在商量我们结婚仪式的甜点、水果时,为了这个柚子,我们吵了一架,你都忘了吗?”
鸟无力地摇了摇头,然后,他渐渐逃离歇斯底里式的妻子的眼睛,躲到妻子枕边狭窄的
角落里,注视着仍在准备发送秘密信号的岳母。鸟可怜兮兮地恳求岳母援助。
“在食品店挑选水果的时候,我觉得葡萄柚子什么地方有些特别。而它怎么特别,却没
细想,就买了。这柚子怎么处理呢?”
鸟是和火见子一块走进食品店的。他所感觉到的柚子的特别之处,无疑投下了火见子的
影子。他想:从现在开始,我的生活细部里,火见子的影子将越来越浓吧?
“屋里只要有一个葡萄柚子,我就会对那味道焦躁不安呀。”妻子仍然紧追不舍,鸟惶
恐地想,妻子是不是马上就要嗅出火见子的影子了?
“那就把柚子送到护士们那儿去吧。”岳母说着,向鸟发出了新的信号。阳光穿过窗外
茂密的绿叶映了进来,岳母深深凹陷的眼睛,瘦削的鼻梁两侧,都流动着绿色的光晕。终
于,鸟读懂子岳母的信号,是让他给护士送柚子回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等着。
“我去,护士室是在楼下吧?”
“外来患者候诊室的旁边就是。”岳母凝视着鸟,说。鸟抱着装柚子的纸袋走到昏淡的
走廊。走着走着,柚子的味道散发了出来,鸟的胸,脸,好像都染上了柚子香味的粒子。鸟
想,肯定有一闻柚子味就上喘的家伙。随后,他又想,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妻子,眼圈染着
绿晕,发送歌舞伎舞蹈似的信号的岳母,还有正在考虑柚子和喘气关系的自己,无论谁,大
家做的事情都像在演戏。是在演戏,演戏。只有头上长着瘤子,被用糖水换走了牛奶因而不
断衰弱下去的孩子不是演戏。即使如此,为什么不用白水,而用糖水呢?越不给牛奶,不就
越渗透出往冒牌货里掺点什么调料的卑鄙策略吗?鸟把柚子口袋递给闲班的护士,本想寒喧
几句,但像小学时代的口吃病又犯了似的,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鸟狼狈地沉默着,点了
一下头,便匆忙拔腿往回返。身后响起了护士们响亮的笑声。演戏,演戏。无论什么,都像
在演戏,都不是真的。这是为什么呢?鸟歪着头,屏住呼吸,一步三阶地往上走,通过婴儿
室时,他提醒自己留心不要向里张望。岳母拎着药罐,在患者家属和陪护人共同使用的炊事
室前,非常昂扬地挺着上身,伫立着。鸟走近岳母身旁,看到岳母的眼睛四周绿叶返照的光
晕已经褪去,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极度的空虚感。鸟吓了一跳,他感觉到,说岳母昂然挺立,
不如说是她身体的自然柔软消失过程中的疲劳和绝望。鸟和岳母一边张望着对面仅距五米之
远的妻子病房的房门,一边简略地相互问答。当岳母听到鸟说孩子还没死,便责怪说:“不
能早点处理吗?要是她看到了孩子,非发疯不可。”鸟被威吓得默不做声。
“要有亲戚是医生就方便了,可惜!”岳母孤独地叹息着说。
我们是贱民的同盟,是卑鄙的自我保护者同盟。鸟想。然而鸟担心,在走廊两侧关闭着
的一个个房门后,或许就立着默不出声、把充满好奇的耳朵贴在门上的患者。他一边警戒
着,一边报告说:
“喂的牛奶量减少了,还用糖水代替牛奶给他,主治医生说,这几天可能会有结果的。”
这时,鸟看到,环绕岳母身体四周瘴气似的东西都消失了,灌满了水的药罐像沉重的锤
子挂在她的手臂上。岳母慢慢点点头,充满睡意似的细声说:“啊,是么,是么?”随后又
补充说:“一切结束以后,孩子的异常事件就只是我们两人的秘密吧。”
“嗯。”鸟同意这一约定,他没有说已经和岳父讲过了。“如果不这样,她不会再生第
二个的,鸟。”
鸟点头赞同,但对岳母生理反应似的排斥却渐渐高涨了起来。岳母走进炊事室,鸟独自
返回妻子的病房。这样简单的策略,妻子看不破吗?所有的一切都像演戏,并且这是登场人
物只会背诵欺瞒人的台词的戏。鸟想。
鸟走回妻子近前,妻子已经忘记了刚才围绕柚子而发作的歇斯底里,鸟在妻子床边坐
下,妻子突然伸出手,充满爱怜地摸着鸟的脸颊,说:“太憔悴了。”
“嗯嗯。”
“像阴沟里的水耗子一样寒碜呢,鸟。”妻子趁鸟不注意来了个突然袭击,”像只鬼鬼
祟祟想往洞里跑的水耗子呀,鸟。”
“是么,我像个想逃跑的水耗子么?”鸟苦涩地说。“妈妈担心你是不是又开始喝上
了,鸟。你那无休无止的喝法,白天晚上,喝起来没完。”
鸟记起了自己整日整夜沉醉不醒的感觉:火烧火燎的脑袋,干得冒烟的喉咙,疼痛的
胃,沉重的身体,失去知觉的手指,酒精麻痹的大脑。那一连数周闭锁在威士忌墙壁里的地
窑生活。
“如果你又开始喝上了,我们的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会醉得人事不醒的,鸟。”
“我,不再那样没完没了地喝了。”鸟说。
确实,他曾连醉两日,但终于未再求助酒精,就逃了出来。不过,如果没有火见子帮
助,那会怎样呢?他难道能不重蹈复辙,再来一次一连几十小时的黑暗痛苦的漂流吗?因
此,鸟既然不能说出火见子,就实在很难说服妻子和岳母,让她们相信他对酒的抵抗力。
“真的,我希望没事呀,鸟。我有时这样想,在非常关键的时候,你却酪酊大醉,或者
陷到奇怪的梦里,真的像只鸟似的飘飘地飞了起来。”
“都结婚这么久了,你还对自己的丈夫这样不放心啊?”鸟像开玩笑似的亲切地说。但
妻子并没有上他的甜蜜圈套,反而这样摇撼着鸟:
“你常常在梦里用斯瓦希里语喊着去非洲,对此我一直沉默,你确确实实是不想和自己
的妻子、孩子一起生活呀,鸟。”鸟凝视着妻子放在他膝上的瘦削的左手,一言不发。然
后,他像一个孩子,既承认自己淘气,又试着对别人的批评进行无力的抗议,他说:
“你说是斯瓦希里语,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斯瓦希里语呢?”“不记得了,我当时也半睡
半醒,并且我也不懂斯瓦希里语。”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喊出来的是斯瓦希里语呢?”“你那像野兽叫声一样的语言,当
然不可能是文明人的语言呀。”
鸟对妻子认定他的喊声是斯瓦希里语的误解深感悲哀,他沉默不语。
“前天和昨天,妈妈说你住在了那边的医院里,那时我就怀疑,你又酪酊大醉了,还是
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是其中的一个吧,鸟。”
“我没有想这类事情的空闲哟。”
“看,脸全红了吧?”
“那是因为生气呀。”鸟激烈地说:“我为什么要往什么地方逃呢,孩子刚刚出生的时
候。”
“当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你不是被各种蚂蚁群似的念头纠缠着走不出来吗?你真的盼
望孩子吗?”
“不管怎样,这都应该是孩子恢复健康以后再谈的事。不是么?”鸟试探着摆脱窘境。
“是呀,鸟。可孩子能不能恢复健康,和你选择的医院,和你的努力大有关系呀。我自
己下不了床,所以连孩子的病究竟在内脏的什么部位也不清楚。我只能相信你呀,鸟。”
“哎,请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