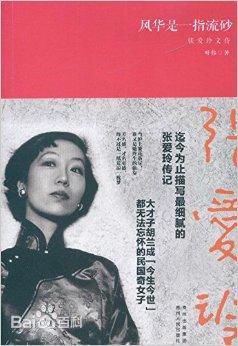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
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
界末日将在纪元一千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
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中国宗教衡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而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
的,同时因为刑罚不甚重而赏额不甚动人,信徒多半采取消极态度,只求避免责罚。中国人
积习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
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
大大地动了疑。
但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难还是:它所描画的来生不是中国人所要的。较旧式的耶
教天堂,在里面无休无歇弹着金的竖琴,歌颂上天之德,那个我们且不去说它。较前进的理
想,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让我们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后,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
显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
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基督教给我们
很少的安慰,所以本土的传说,对抗着新旧耶教的高压传教,还是站得住脚,虽然它没有反
攻,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没有宣传文学,优美和平的布景,连一本经书都没有——佛经极
少人懂,等于不存在。
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
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是谎话,也无伤,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
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
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模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交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
“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
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
,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
或是富兰克林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情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
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
它自己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古人的天的影响,
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
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
不给么?
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性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
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伦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
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
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
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虔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
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
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
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
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
“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
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
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
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
“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塌。”
(一九四四年八月)
诗与胡说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
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菜,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
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重事不能做,单
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
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
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份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
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
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
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
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
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
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
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
》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
,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菜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
倍。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
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
有个表姊,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
《秋海棠》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再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
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
来的有些诗。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
,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
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
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婷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
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无声地,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
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
,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
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份真是好:——
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磅礴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压得紧,更为
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方,“言语似夜行车”,断断
续续,
远而凄怆。再如后来的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
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
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
不是树上拗下来,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
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
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
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
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
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
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
写 什 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末只有阿
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
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
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
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
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
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
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
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
,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地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
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窠,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
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
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
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
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
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
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
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
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
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传奇》再版序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
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
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
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
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