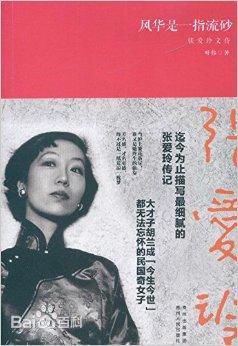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
:“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
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
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
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
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
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
姑姑语录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
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
:“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
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
“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
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起初我当做她是说:因为厌烦的缘故,仿佛时间过得奇慢。后来发现她是另外一个意思
:一个人老了,可以变得那么的龙钟糊涂,看了那样子,不由得觉得生命太长了。
她读了苏青和我对谈的记录,(一切书报杂志,都要我押着她看的。她一来就声称“看
不进去”我的小说,因为亲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实地篇篇过目,虽然嫌它太不愉快。原稿她
绝对拒绝看,清样还可以将就。)关于职业妇女她也有许来意见。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
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
活里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妇女职业,都不是什么专门技术的性质,不过是在写字间里做人
罢了。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凤,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将来她也许要写
本书关于女人就职的秘诀,譬如说开始的时候应当怎样地“有冲头”,对于自己怎样地“隐
恶扬善”然而后来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
,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
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
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从前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
“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
不到一个钱。”
她批评一个胆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说:“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咙了。”
“爱德华七世路”(爱多亚路)我弄错了当做是“爱德华八世路”,她说:“爱德华八
世还没有来得及成马路呢。”
她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
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
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
有一次她说到我弟弟很可怜地站在她眼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吧达吧
达”四个字用得真是好,表现一个无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湿地目夹着眼。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顶
喜欢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是她办公室里省下来的
,用过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页页大小不等,读起来淅沥沙辣作脆响。)信里有一种无聊的
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语气很平淡,可是用上许多惊叹号,几乎全用惊叹号来做标点,
十年前是有那么一派的时髦文章的吧?还有,她老是写着“狠好”,“狠高兴”,我同她辩
驳过,她不承认她这里应当用“很”字。后来我问她:“那么,‘凶狠’的‘狠’字,姑姑
怎么写呢?”她也写作“狠”。我说:“那么那一个‘很’字要它做什么呢?姑姑不能否认
,是有这么一个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说:“现在没有人写‘狠好’了。一这样写
,马上把自己归入了周瘦鹃他们那一代。”她果然从此改了。
她今年过了年之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越是诸事不顺心,反倒胖了起来。她写信给一
个朋友说:“近来就是闷吃闷睡闷长。好容易决定做条裤子,前天裁了一只腿,昨天又
裁了一只腿,今天早上缝了一条缝,现在想去缝第二条缝。
这条裤子总有成功的一日吧?”
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
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
去估价,店里出她十块钱,她没有卖。每隔些时,她总把它拿出来看看,这里比比,那里比
比,总想把它派点用场,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青绿丝线穿着的一块宝石,冻疮肿到一个程
度就有那样的淡紫红的半透明。襟上挂着做个装饰品吧,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样
的颜色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
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面顶相宜——可是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着想,不放,又还要
更好些。
除非把它悬空宕着,做个扇坠什么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头
的一个洞,位置又不对,在宝石的正中。
姑姑叹了口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一九四五年五月)
中国的日夜
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有两趟买菜回来竟做出一首诗,使我自己非常诧异而且快
乐。一次是看见路上洋梧桐的落叶,极慢极慢地掉下一片来,那姿势从容得奇怪。我立定了
看它,然而等不及它到地我就又往前走了,免得老站在那里像是发呆。走走又回头去看了个
究竟。以后就写了这
个:——
落叶的爱
慢慢的,它经过风,
经过淡青的天,
经过天的刀光,
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地上它的影子,
迎上来迎上来,
又像是往斜里飘。
叶子尽着慢着,
装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着个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这儿了!”
秋阳里的,
水门汀地上,
静静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
又一次我到小菜场去,已经是冬天了。太阳煌煌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清湿的气味,如
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地下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
腌菜,一个像酱菜,各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颔下盛胡须的锦囊。又
有个抱在手里的小孩,穿着桃红假哔叽的棉袍,那珍贵的颜色在一冬日积月累的黑腻污秽里
真是双手捧出来的,看了叫人心痛,穿脏了也还是污泥里的莲花。至于蓝布的蓝,那是中国
的“国色”。不过街上一般人穿的蓝布衫大都经过补缀,深深浅浅,都是像雨洗出来的,青
翠醒目。我们中国本来是补钉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
一个卖桔子的把担子歇在马路边上,抱着胳膊闲看景致,扁圆脸上的大眼睛黑白分明。
但是,忽然——我已经走过他面前了,忽然他把脸一扬,绽开极大的嘴,朝天唱将起来:
“一百只洋买两只!一百只洋两只买咧!伙颐!一百只洋贱末贱咧!”这歌声我在楼上
常常听见的,但还是吓了一跳,不大能够相信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因为声音极大,而前一
秒钟他还是在那里静静眺望着一切的。现在他仰着头,面如满月,笑嘻嘻张开大口吆喝着,
完全像Sapa-jou漫画里的中国人。
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那
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叫人伤心。
有个道士沿街化缘,穿一件黄黄的黑布道袍,头顶心梳的一个灰扑扑的小髻,很像摩登
女人的两个小鬈叠在一起。黄脸上的细眼睛与头发同时一把拉了上去,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的脸相。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但是因为营养不足,身材又高又瘦,永远是十七八岁抽长条
子的模样。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
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
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
(连来生也肯卖——那是子孙后裔的前途。)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
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
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粱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
一种惘然。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
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
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
的淤流,像一朵黑菊花徐徐开了。看着他,好像这个世界的尘埃真是越积越深了,非但灰了
心,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一捏就粉粉碎,成了灰。我很觉得震动,再一想,老这么跟在他后面
看着,或者要来向我捐钱了——这才三脚两步走开了。
从菜场回来的一个女佣,菜蓝里一团银白的粉丝,像个蓬头老妇人的髻。又有个女人很
满意地端端正正捧着个朱漆盘子,里面矗立着一堆寿面,巧妙地有层次地摺叠悬挂;顶上的
一提子面用个桃红小纸条一束,如同小女孩头上扎的红线把根。淡米色的头发披垂下来,一
茎一茎粗得像个蛇。
又有个小女孩拎着个有盖的锅走过,那锅两边两只绊子里穿进一根蓝布条,便于提携。
很宽的一条二蓝布带子,看着有点脏相,可是更觉得这个锅是同她有切身关系的,“心连手
,手连心”。
肉店里学徒的一双手已经冻得非常大了,橐橐拿刀剁着肉,猛一看就像在那里剁着红肿
的手指。柜台外面来了个女人,是个衰年的娼妓罢,现在是老鸨,或是合伙做生意的娘姨。
头发依旧烫得蓬蓬松松掳向耳后,脸上有眉目姣好的遗迹,现在也不疤不麻,不知怎么有点
凸凹不平,犹犹疑疑的。
她口镶金牙,黑绸皮袍卷起了袖口,袖口的羊皮因为旧的缘故,一丝一丝胶为一瓣一瓣
,纷披着如同白色的螃蟹菊。她要买半斤肉,学徒忙着切他的肉丝,也不知他是没听见还是
不答理。她脸上现出不确定的笑容,在门外立了一会,翘起两只手,显排她袖口的羊皮,指
头上两只金戒指,指甲上斑驳的红蔻丹。
肉店里老板娘坐在八仙桌旁边,向一个乡下上来的亲戚宣讲小姑的劣迹。她两手抄在口
袋里,太紧的棉袍与蓝布罩袍把她像五花大绑似地绑了起来;她挣扎着,头往前伸,瞪着一
双麻黄眼睛,但是在本埠新闻里她还可以是个“略具姿首”的少妇。“噢!阿哥格就是伊个
!阿哥屋里就是伊屋里——从前格能讲末哉、现在算啥?”她那口气不是控诉也不是指斥,
她眼睛里也并没有那亲戚,只是仇深似海;如同面前展开了一个大海似的,她眼睛里是那样
的茫茫的无望。一次一次她提高了喉咙,发声喊,都仿佛是向海里吐口痰,明知无济于事。
那亲戚衔着旱烟管,穿短打,一只脚踏在长板凳上;他也这样劝她:“格仔闲话倒也覅去老
讲伊老”然而她紧接着还是恨一声:“噢!侬阿哥囤两块肉皮侬也搭伊去卖卖脱!”
她把下巴举起来向墙上一指;板壁高处,钉着几枚钉,现在只有件蓝布围裙挂在那里。
再过去一家店面,无线电里娓娓唱着申曲,也是同样地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
先是个女人在那里发言,然后一个男子高亢流利地接口唱出这一串:“想我年纪大来岁数增
,三长两短命归阴,抱头送终有啥人?”我真喜欢听,耳朵如鱼得水,在那音乐里栩栩游着
。街道转了个弯,突然荒凉起来。迎面一带红墙,红砖上漆出来栳栳大的四个蓝团白字,是
一个小学校。校园里高高生长着许多萧条的白色大树;背后的莹白的天,将微欹的树干映成
了淡绿的。申曲还在那里唱着,可是词句再也听不清了。我想起在一个唱本上看到的开篇:
“谯楼初鼓定天下——隐隐谯楼二鼓敲谯楼三鼓更凄凉”第一句口气很大,我非常
喜欢那壮丽的景象,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我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磁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侧,一
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挽着,吃力得很。冬天的阳光虽然
微弱,正当午时,而且我路走得多,晒得久了,日光像个黄蜂在头上嗡嗡转,营营扰扰的,
竟使人痒刺刺地出了汗。
我真快乐我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