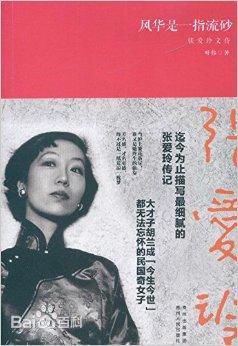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越看到后来越觉得奇怪,憋闷得厉害,避重就轻,一味搪塞,非常使人不满。
这本书虽然是三十年代的,我也是近年来看了第二部影片之后才有这耐性看它。报刊上
看到的关于邦梯号的文字,都没提到发现辟坎岛的经过。在我印象中,一直以为克利斯青这
班人在当时是不知所终,发现辟坎岛的时候,岛上有他们的后裔,想必他们都已终天年。最
后看见密契纳这一篇,才知道早在出事后廿年左右——就在白颜访旧塔喜堤的次年——英舰
已经发现辟坎岛,八个叛党只剩下一个老人,痛哭流涕“讲述这块荒凉的大石头上凶杀的故
事”,讲大家都憎恨克利斯青残酷,“不顾人权”,正是他指控布莱的罪名。绮萨贝拉在岛
上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星期四·十月”,那是模仿《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鲁滨逊星期五
遇见一个土人,就给他取名“星期五”。孩子显然是在叛变后五个多月诞生。次年十月底,
产子一年后,绮萨贝拉生病死了。他要另找个女人,强占一个跟去的土人的妻子,被那土人
开枪打死。
叛舰的故事可以说是跟我一块长大的,尽管对它并不注意。看到上面这一段,有石破天
惊之感。其实也是缩小的天地中的英雄末路。辟坎岛孤悬在东太平洋东部,距离最近的岛也
有数百英里之遥,较近复活节岛与南美洲。复活节岛气候很凉,海风特大,树木稀少,又缺
淡水,多数农植物都不能种,许多鱼也没有,不是腴美的热带岛屿,但是岛上两族长期展开
剧烈的争夺战。叛舰初到辟坎岛,发现土人留下的房屋,与复活节岛式的大石像,大概是复
活节岛人逃避来的。
有一尊断头的石像,显然有追兵打到这里来。但是结果辟坎岛并没有人要,可见还不及
复活节岛,真是一块荒凉的大石头,一定连跟来的塔喜堤人都过不惯。也不怪克利斯青一直
想回国自首。
他在土排岛与大家一同做苦工,但是也可能日子一久,少爷脾气发作,变得与布莱一样
招恨,那也是历史循环,常有的事。主要还是环境关系,生活极度艰苦沉闷,一天到晚老是
这几个人,容易发生磨擦。也许大家心里懊悔不该逞一时之快,铸成大错,彼此怨怼,互相
厌恨,不然他死后为什么统统自相残杀,只剩一个老头子?
老人二十年后见到本国的船只,像得救一样,但是不免畏罪,为自己开脱,反正骂党魁
总没错。——书上没说他回国怎样处分,想必没有依例正法。——当然,岛上还有土人在,
不是完全死无对证。所说的克利斯青的死因大概大致属实,不过岛上的女人风流,也许那有
夫之妇是自愿跟他,不是强占。在缺少女人的情形下,当然也一样严重。总计他起事后只活
了不到两年,也并没过到一天伊甸园的生活。
老人的供词并非官方秘密文件,但是近代关于邦梯案的文字全都不约而同绝口不提,因
为传说已经形成,克利斯青成为偶像,所以代为隐讳——白兰度这张影片用老人作结,但是
只说叛党自相残杀净尽,片中的克利斯青早已救火捐躯——只有密契纳这一篇是替船长翻案
,才不讳言大副死得不名誉。诺朵夫书上如果有,也就不会是三十年代的畅销书,那时候的
标准更清教徒式。但是书上白颜自云十八年后发现叛舰不是逃到拉罗唐珈,而下文不再提起
这件事,这章法实在特别,史无前例。看来原文书末一定有那么一段,写白颜听到发现辟坎
岛的消息,得知诸人下场,也许含糊地只说已死。
出版公司编辑认为削弱这本书的力量,影响销路,要改又实在难处理,索性给删掉了,
给读者留下一个好结局的幻象,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辟坎岛上有克利斯青一干人的子孙。
在我觉得邦梯案添上这么个不像样的尾巴,人物与故事才完整。由一个“男童故事”突
然增加深度,又有人生的讽刺,使人低徊不尽。当然,它天生是个男童故事,拖上个现实的
尾巴反而不合格,势必失去它的读者大众。好在我容易对付,看那短短一段故事也就满足了
。
郁达夫常用一个新名词:“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一般译为“感
伤的”,不知道是否来自日文,我觉得不妥,太像“伤感的”,分不清楚。“温情”也不够
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优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体的情感。另一个解释是
“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近代沿用的习惯上似乎侧重这两个定义,含有一种暗示,
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夸张强调。不怪郁达夫只好音译,就连原文
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西方科学进步以来,抱着怀疑一切的治学精神,逐渐提高自觉性的结
果。
自从郁达夫用过这名词,到现在总有四十年了,还是相当陌生,似乎没有吸收,不接受
。原因我想是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
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
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现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
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
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
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
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
自己的法律。
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近来的新新闻学(ne
wJournalism)或新报道文学,提倡主观,倾向主义热,也被评为“三底门答尔
”。“三底门答尔”到底是什么,说了半天也许还是不清楚。粗枝大叶举个例子,诺朵夫笔
下的《叛舰喋血记》与两张影片都“三底门答尔”,密契纳那篇不“三底门答尔”。第一张
影片照诺朵夫的书,注重白颜这角色,演员挂三牌。第二张影片把白颜的事迹完全删去,因
为到了六十年代,这妥协性的人物已经不吃香。电影是群众传达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
念。密契纳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长,全是史实。所谓“冷酷的事实”,很难加以“三底门
答尔”化。
当然忠实的纪录体也仍旧可能主观歪曲,好在这些通俗题材都不止一本书,如历史人物
、名案等等,多看两本一比就有数。我也不是特为找来看,不过在这兴趣范围内不免陆续碰
上,看来的材料也于我无用,只可自娱。实在是浪费时间,但是从小养成手不释卷的恶习惯
,看的“社会小说”最多,因为它保留旧小说的体裁,传统的形式感到亲切,而内容比神怪
武侠有兴趣,仿佛就是大门外的世界。到了四十、五十年代,社会小说早已变质而消灭,我
每次看到封底的书目总是心往下沉,想着:“书都看完了怎么办?”
在国外也有个时期看美国的内幕小说,都是代用品。应当称为行业小说,除了“隔行如
隔山”,也没有什么内幕。每一行有一本:飞机场、医院、旅馆业、影业、时装业、大使馆
、大选筹备会、牛仔竞技场、警探黑社会等。内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说,讲广告业,是一个
广告商杰利·戴拉·范米纳(DellaFemina)自己动笔写的,录音带式的漫谈,
经另人整理删节,还是很多重复,书题叫《来自给你们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戏拟日制电
视机广告。
行业小说自然相当内行,沾到真人实事,又须要改头换面,避免被控破坏名誉。相反地
,又有假装影射名人的,如《国王》(The King)——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盖博绰
号,写歌星法兰仙纳屈——《恋爱机器》——前ICBS电视总经理吉姆·奥勃瑞,绰号“
笑面响尾蛇”——务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节骨眼上给“掉包”换上一般通俗小说
情节,骗骗读者,也绝对不会开罪本人。这都煞费苦心,再加上结构穿插气氛,但是我觉得
远不及中国的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这名称,似乎是二十年代才有,是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
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
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章
回小说不再振聋发聩,有些如《歇浦潮》还是讽刺,一般连讽刺也冲淡了,止于世故。
对新的一切感到幻灭,对旧道德虽然怀恋,也遥远黯淡。三十年代有一本题作《人心大
变》,平襟亚著,这句话在社会小说里是老调。但是骂归骂,有点像西方青年人的口头禅“
爱恨关系”,形容有些作者对自己的背景,既爱又恨,因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不过在
这里“恨”字太重,改“憎”比较妥帖。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与插图像是十年代末或二十年代初,文笔很差,与三十年代
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梦》还是什么梦的同样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开场仿
佛也都是两个青年结伴到上海观光。后一部写两个同学国光、锦人,带着国光的妹妹来沪,
锦人稍有阔少习气。见识了些洋场黑幕后,受人之托,同去湖北整顿一个小煤矿。住的房子
是泥土地,锦人想出一个办法,买了草席铺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听见隔壁席子赶咐作
声,发现帐房偷开铁箱。原来是帐房舞弊,所以蚀本。查出后告退,正值国民军北上,扫清
了一切魍魉。以北伐结束,也是三十年代社会小说的公式。锦人与国光的妹妹相处日久发生
情愫,回乡途中结婚,只交代了这么一句。妹妹在书中完全不起作用,几乎从来不提起,也
没同去湖北。显然是“国光”的自述,统统照实写上。对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赞成,也不便
说什么。
这部书在任何别的时候大概不会出版,是在这时期,混在社会小说名下,虽然没有再版
,料想没有蚀本。写到内地去,连以一个大都市为背景的这点统一性都没有。它的好处也全
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
,也没富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
《广陵潮》我没看完,那时候也就看不进去,因为刻画得太穷凶极恶,不知道是否还是
前一个时期的影响,又“三底门答尔”,近于稍后的“社会言情小说”,承上启下,仿佛不
能算正宗社会小说。这些书除了《广陵潮》都是我父亲买的,他续娶前后洗手不看了,我住
校回来,已经一本都没有,所以十二三岁以后就没再看见过,当然只有片断的印象。后来到
书摊上去找,早已绝迹。将张恨水列入“社会言情小说”项下,性质不同点。他的《春明外
史》是社会小说,与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有些地方相近,自传部分仿佛是《人间地狱》写
得好些,两人的恋爱对象雏妓秋波梨云也很相像。《人间地狱》就绝版了。写留学生的《留
东外史》远不及《海外缤纷录》,《留东外史》倒还有。
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因为故事集中,又是长篇,光靠一点事实不够用,不得不用创
作来补足。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但是社会小说
的遗风尚在,直到四十年代尾,继张恨水之后也还有两三本真实性较多。那时候这潮流早已
过去,完全不为人注意。
一个是上海小报作者的长篇连载,出单行本,我记性实在太精,人名书题全忘了,只知
道是个胖子,常被同文嘲骂“死大块头”——比包笑天晚一二十年,专写上海中下层阶级。
这一篇写一个舞女嫁给开五金店的流氓,私恋一个家累重的失业青年,作为表兄,介绍
他做帐房,终于与流氓脱离预备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这样平淡的结局意想不到地感动
人。此外北方有一本写北大一个洗衣女,与一个学生恋爱而嫌他穷。作者姓王。又有个大连
的现代钗头凤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泄气得谁也造不出来,看来都是全部实录。
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各地大小报每一个副刊登几个连载,不出单行本的算在内,是一
股洪流。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烈,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
好奇?也难说,题材太没有选择性,不一定反映社会的变迁。小说化的笔记成为最方便自由
的形式,人物改名换姓,下笔更少顾忌,不像西方动不动有人控诉诽谤。写妓院太多,那是
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条路线,而且也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因为一般人太没有恋爱的
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
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
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
,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俗手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
色,反而原味全失。这
仿佛是怪论——
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
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
是人生味。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西谚“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实”,作名词用,一般译为“真
理”,含有哲理或教义的意味,与原意相去太远,还是脑筋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