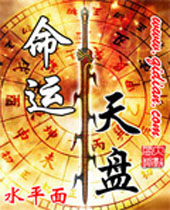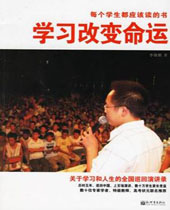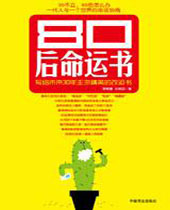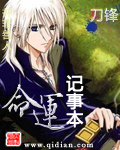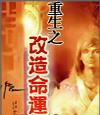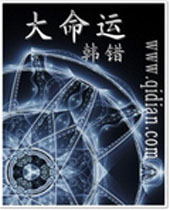西藏命运-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述驻藏大臣的日常工作和具体活动,但是可以想象,西藏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万人口,没有一个上千名官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权力体系(即政权)是无法管理的。仅驻藏大臣手下的属员数量之少,就已经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直接行使权力。事实正是如此,到1959年中共全面建政以前,西藏从来都是由当地政权体系进行统治的。清代驻藏大臣的人力只够与西藏高层统治者打一对一的交道。如果西藏统治者服从驻藏大臣,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指挥政权体系,驻藏大臣才算辗转地有了对西藏的权力。这样的时候不能说没有,如清朝大军在藏期间,西藏统治者可能不得不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然而大多数时间,西藏统治者并不面临被大清帝国武力废黜的威胁,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物质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势单力孤的外来人唯命是从,就没有任何道理。虽然《二十九条章程》规定“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第十条),然而对官场行为稍有了解,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句空话。对西藏政权各级官员来讲,驻藏大臣是一个异族人,文化隔膜,语言不通,人缘不熟,他们不可能把忠诚和服从献给这样的人,而不惜得罪本地统治者,这是基本的官场常识,别说还有民族感情、宗教虔诚和文化认同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以,驻藏大臣无法绕过当地统治者直接指挥西藏政权。但是《二十九条章程》赋予了驻藏大臣任免西藏文武官员的权力,他为什么不可以靠这种权力控制西藏政权体系呢?以对藏军军官的任命为例。当时藏军有六个相当于团的编制,首领为代本,下辖十二个如本(营长),二十四个甲本(连长),一百二十四个定本(排长),再下面还有久本(班长)。按照“二十九条”章程,这些军官都应该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挑选和任命。问题是,驻藏大臣上哪去挑选这数百名军官?他人生地不熟,平时住在拉萨,很少能跟分散在各地的藏军打交道,与代本以下的基层军官更是难有来往。除非他有一个人事部门,平时能代他去各地考察挑选,然而他一共就有那么几个属员,毫无可能。结果就成了只有达赖喇嘛一方能够提出名单。而驻藏大臣面对名单上那些他念都念不顺口的藏文名字,除了同意,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这个道理可以推想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命。当年西藏政府仅在拉萨就有五十多个机构 ,拉萨以外还有众多的宗(县)、奚(区)等基层政权。驻藏大臣一样无从去提任命名单,因此他的任命权也就一样徒有虚名。正如史书所载:“噶伦、代本等缺,向来虽由驻藏办事大臣奏补,但实系达赖喇嘛酌定补放,交驻藏大臣具奏;其余商上孜本、商卓特巴及各大小营官亦均由噶伦等酌拟人数,然后由达赖喇嘛挑定,驻藏大臣俱不过问。”理论上,驻藏大臣至少可以了解经常与之打交道的西藏高层官员,如噶伦和代本之流。他应该能对这一层的任命提出自己的名单。但是前面讲过的然巴之“死”,已经说明了驻藏大臣的无可奈何。不错,然巴如果愿意当噶伦,他可以投靠驻藏大臣,而不是背着死人的名义去度余生。然而三年一换的驻藏大臣就像无根的浮萍来来去去,达赖喇嘛的威严却终生笼罩着西藏每一个人及其家族。在这不成比例的两个靠山之间,当“藏奸”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驻藏大臣因此只能抱怨“番官惟达赖之命是听” ,而绝无可能在藏人中间建立自己的阵营。上述属员少、在藏时间短、与基层绝缘三个特点,还造成驻藏大臣的信息贫困。人少则耳目少,加上语言不通,耳目又多一层遮蔽(联豫奏稿中有“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如果能够长时间地扎根西藏,学会语言,发展地方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却又是三年一换,刚开始了解情况就换上另一拨新人。在这种状态下,除了任人摆布,实在也别无选择。再者,驻藏大臣即使发觉自己受骗,面对那些扯皮推诿软磨硬泡,往往也毫无办法。联豫抱怨:“……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赖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 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完全按自己的而非中国人的意志对西藏进行统治。这就像乘客和司机发生分歧时,司机不需要公开与乘客对抗,他只需以车出了问题,或是需要加油,或是前方不许左转等无数理由,就能迫使乘客服从他,哪怕乘客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司机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比乘客有信息优势。驻藏大臣就处于这种乘客地位。尽管乘客可以怀疑司机是撒谎,但除非乘客自己就是汽车专家,否则肯定理论不过司机。以驻藏大臣的处境,对西藏政权之车又如何能成为专家呢?1904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初始是以要求谈判开端的。当时的英国政府并不支持荣赫鹏上校(Francis Younghusband)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荣赫鹏每向西藏境内挺进一段,就要求驻藏大臣前往谈判。如果早一点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也许能避免后来的结局。而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以及后赴任的驻藏大臣有泰,皆以西藏当局不支应“乌拉”为由而不前往,最终导致对抗逐步升级,英军一直打进拉萨。有泰在拉萨见荣赫鹏时,仍以西藏人不支应“乌拉”为自己没有及早与之见面进行辩解。荣赫鹏为之暗笑,遂将这个辩解当作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的证明 。所谓“乌拉”是西藏地方的一种差役体系,在此主要是指交通运输方面的劳役,由那些承担劳役义务的百姓按照政府的命令为公务人员在西藏境内行走提供人力、畜力和食宿。堂堂清政府的驻藏大臣,在面临边境战争之如此大事时,竟不能调动行路用的区区马匹,还谈何对西藏拥有主权?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几无例外地把有泰这个理由视为托辞,指责其“庸懦无能,辱国已甚”。也许从总体上,这种指责没有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有泰为什么偏偏挑选这个托辞,并不见得全是空穴来风。至少在平时,驻藏大臣经常在使用乌拉方面受刁难,才能随时拿它当作搪塞的理由。我完全相信西藏人当年会利用这个手段对付驻藏大臣。虽然《二十九条章程》专门有一条把派乌拉的权力赋予驻藏大臣,规定“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沿途按执票派用乌拉”(第二十四条)。但即使你开出再多的执票,他要么说马匹太瘦,不堪重负,要么说大雪封山,无法前行,要么对乌拉接力的任何一个环节暗中授意,把你抛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挨饿受冻。既不懂马又不懂路的驻藏大臣除了任其摆布,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靠这种手段,西藏人不需要公开对抗,却能把驻藏大臣的行动完全限制住。倘若连在西藏行路都受制于人,可怜的驻藏大臣又如何谈得上治理西藏呢?我用“接口”比喻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那时的西藏保持完全自治,自成一体。驻藏大臣只是北京伸向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的本地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朝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才能实现。清代中国对西藏有无主权问题,在这里也就有了一种更具体的判断: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服从北京“接口”的指令,中国对西藏就有主权;如果西藏架空北京的“接口”,只是在诸如外交、国防一类大问题上表示服从或不敢违抗,那就只能算是宗主权;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不听从,甚至割断“接口”,那就什么权也没有了。
5、东方式关系
今天,达赖喇嘛的海外流亡政府聘请西方人士担任他们的国际公法顾问,以国际法的标准,从历史上寻找西藏不曾隶属于中国的法律根据。西方学者也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便在清朝最强盛的时期,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从来没有形式化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条约或是其他和谈来确定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北京方面也养了一大群法律、历史等方面的专家,搜罗出许多类似《二十九条章程》那样的证据,并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其中的主权表现,证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历史合法性。挑选出以上这段文字中的关键词──国际法、法律根据、形式化、条约、权利和义务、合法性等,可以发现,双方运用的都是本来不属于东方历史的概念。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历史上都不曾用现代主权的观念认识和约定相互的关系。西方概念被确立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被东方接受认可,并在中藏关系中被双方强烈地意识和争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二者之间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纠缠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东方的历史上。如果一定要用主权、宗主权的概念判断清代的中藏关系,我同意中国那时对西藏的控制更类似宗主权,而缺少主权性质。虽然西藏向中国朝廷表示臣服,在多数时间和多数问题上,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或者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表面上,驻藏大臣被摆在重要位置。如前面引用的孟加拉校长的描述,驻藏大臣尽可以威风凛凛地游行,西藏官员尽可以在出席场面时居于次要地位,甚至驻藏大臣可以拘押西藏头人,鞭打沿街的西藏百姓,然而在对西藏的实际统治中,驻藏大臣却起不了多少实际作用。西藏统治者以其特有的圆滑和耐性,通过架空驻藏大臣维持了实质上的独立。不过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谁胜谁败的结果,反之,也许那正是当时的中藏双方所共同追求、双方都满意的、因而也是最为自然与合理的结果。不错,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常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例如1788年和1791年两次廓尔喀侵略西藏,起因于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叛离西藏,唆使廓尔喀进藏抢劫札什伦布寺的财宝。当时西藏方面既没有向驻藏大臣通报沙玛尔巴的叛逃,廓尔喀第一次入侵后,达赖又自行允诺对廓尔喀赔银赎地,也不与驻藏大臣商量,后因付不起赔款引起了廓尔喀第二次入侵,清朝不得不兴师动众,把大兵派进西藏才算平息。这种劳民伤财使乾隆恼火,因此才严令整顿藏务,制定了《二十九条章程》,以加强控制西藏的外交与边防。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年之间,只有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理解这一点,需要认识中国古代政治观与西方政治观的区别: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的韩格理教授发现,历来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论说,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到当代政治历史、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学者,无不是以得之于西方国家结构的概念,如科层制、世袭科层制、专制政体、独裁政体以及活动于其中的各种角色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国家的属性。这种作法,在他看来,常导致无法确认且误导的结果。根据韩氏的概括,西方的政治结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集中化的权力观念和行政性的政治组织观念。在这里,政治权力基于意志,且由一象征性的中心向四方扩散,所谓“行政科层制”即是由这种命令结构中产生的组织类型。上面提到的各种概念如科层制、官僚、统治者乃至于“国家”,均是由这种关于政治组织及国家合法性的中心主义的观念导引出来。然而,在中国的政治组织里面,这些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权力并非产生于意志,服从亦非基于命令。韩氏认为,【加重开始】中国人的权力观乃是建立在为达成秩序而在和谐中运作的角色以及由礼所界定的角色关系上面。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组织是由具有层级化排列的角色组合所构成,这些角色组织基本上自我维持,而没有与明显的命令结构相联系。【加重结束】
后面几行的加重是我加的。我认为有助于帮助理解古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那时中国周边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中国可以一直保持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视其他民族为“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古代中国不以政治共同体界定国家,只关注一家一姓的王朝,而王朝的合法性在于其必须代表中国文化的正朔,正如梁漱溟所说“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 。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领土、资源、边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礼”。只要那些“夷”“狄”“蛮”“番”对中国文化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不需要过份操心。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从来不以法律界定自己的领土,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表示巨服,就一概被认为属于中国。加上“无为而治”的传统帝王哲学,宁愿让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重内轻外,详近略远,骈举四方以示政权之归于一,则天下在地理上政治上都被认为已完整。至于“四方”的细部,却不是古人的主要关怀。若必以西人说一不二的方式去检验,则古人的“天下”是很难在地图上再现的。历代中国边疆的赢缩常以千里计,倘以西人以固定疆域为国家要素的概念衡之,则中国岂非要到近代许多卖国条约因割地而划定边界后才成其为“国”?但对昔日的中国朝野人士来说,只要本土(main body of homeland)稳定,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中国”概念的完整。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