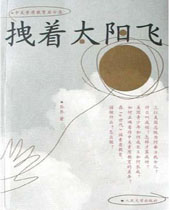千山看斜阳_+番外_by_满座衣冠胜雪-第9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着一声尖啸,有两朵烟花在空中炸开,火星飞溅,划破了白茫茫的雪天,传得很远。
宁觉非立刻警觉,手中刀一刻不停,将那人的左右退路封住,随即吹了一声口哨。
云扬立刻从窗口跳了出来,叫道:“元帅,有何吩咐?”
那人听到这“元帅”二字,猛地直瞪向宁觉非。
他们两人激战了数十招,其实只不过是一眨眼的时间,双方都把全部精力放在对方的动作上,根本没有注意彼此的长相。直到这时,宁觉非才发现,此人有双碧绿的眼睛,目光锐利,直似要把人割得遍体鳞伤才肯罢休。
宁觉非微一愣神,便想起了曾经在何处看到过这样的眼神。
在西武的腾青沙漠围攻蓟国使团的为首之人也有这么一双眼睛。
他一怔之间,手中的刀招不免缓了一缓,那人趁机猛然跃起,刀光暴涨,攻势如雷霆闪电,向他疾扑过去。
宁觉非向后连退三步,不绿迅捷,身法轻灵,始终与那人保持这最适合挥舞长刀的距离,而那人的短刀要递到他身前就比较困难了。
云扬见此人出手不凡,手中刀一扬,便要冲过来加入战团。宁觉非却抢先命令道:“你马上调弓弩手,过去封锁通往雪城的路口。”
“是。”云扬二话不说,立刻回头大叫。“弓弩手,全部过来。”
他们两个小队中有三十个人擅长操作南楚的弩箭,听到命令后,当即脱离战斗,冲出大门,直奔到云扬身边集合。
与宁觉非对战的那人脸色一变,忽然向小路一旁通往雪城的方向窜去。
宁觉非正要追击,空中隐隐传来“嗖嗖”声,有一支黑色的长箭穿过风雪,笔直地向他飞来,后面还紧跟着第二支、第三支,迅猛地划破长空,全部射向他一个人。
宁觉非挥刀猛劈,将几支长箭全部挡开,就这一缓之间,那人的身影便被风雪淹没,隐隐约约看不真切了。
宁觉非拔腿便追,一边在雪地里飞奔一边侧耳倾听。他没有听到马蹄声或大批人前行的脚步声,之看见前面那人狂奔的身影时隐时现。
云扬见他追了过去,连忙紧紧跟上,并挥手让弓弩手跟着自己前进。
异常有力的长箭继续破空射来,宁觉非的脚步不断被箭矢阻滞,渐渐离那人越来越远。衡量一下情势,他之得停下来,俯身将地上的箭全都拾起,返身奔回。
那个箭手便停止了射箭,似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云扬已布置好弓弩手所站的方位,将狭窄的仅供一人通过的山口完全封锁。这里原本安有活动路障,以圆木制成,相当沉重,可有效阻拦敌人的冲击,现在多半是被那些人推进了深谷,使这里无所遮拦。
宁觉非打算先用弓弩手守住这里,如果果然有敌人的援军到来,也能有效地阻截对方,然后立刻派人下山,再调些人马上来,应该就问题不大了。毕竟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最狭窄的地方仅能容一人一骑,易守难攻,对方即便来了再多人也没用。
哨卡里的战斗已接近尾声,云扬却不肯让宁觉非靠近。里面的人都很顽强,个个是亡命之徒,万一来个玉石俱焚什么的,伤及宁觉非,他就万死莫赎了。
宁觉非也不强求,只对他说:“留几个活口,别都杀了。”便占到山壁旁,仔细查看手中的长箭。
这些箭射来的力度和方式他都非常熟悉,至今记忆犹新,他敢肯定,那射箭的人便是那个在乌拉珠穆城主府中夜袭的神箭手。此人的身份神秘莫测,一直查不出端倪,没想到来了这里,而且听命于那个碧眼之人,仅凭一人之力,便掩护他从宁觉非手里逃脱,却是非同凡响。
宁觉非思忖着,抬头看向箭矢飞来的方向。
大团大团的雪花之间,层峦叠嶂,银装素裹,犹如冰河时代,不见人烟,寒冷的风如刀子一般,刮得人搂在外面的手和脸一阵阵刺疼。在那样的雪峰上,人类是很难生存的,宁觉非对那个埋伏在雪山之上,时刻准备保护另一个人的箭手相当钦佩,同时也对那个如恶狼一般凶狠的碧眼黑衣人有了几分好奇,很想与他好好地再交一次手。
不久,云扬过来禀报:“元帅,里面的人都料理了,活着的只有六个人,都是重伤。虽然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不过个个都是硬汉子,没有孬种,叫人好生相敬。”
“是啊。”宁觉非点了点头。“无论死活,都送下山去,死者厚葬,伤者替他们诊治。另外,把他们的马都带下去。”
“是。”云扬转身便去安排。
宁觉非缓步走近哨卡,询问己方的伤亡情况,嘱咐伤者下山去好好修养,为牺牲的战事整理好因战斗而变得有些凌乱的一副,再肃立默哀。屋里变得很安静,鹰军的将士们都跟随他打过很多次仗,深知他对伤者的关切和对死者的尊重,所有没受伤或仅受轻伤的人都放下手中的事情,默然肃立,与他一起向牺牲的战友表达哀思。
过了一会儿,宁觉非才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各自去做自己的事,然后去察看现场以及那些人携带的物品。
两个多时辰后,鹰军的两个百人队上来,分别守住山口与哨卡,宁觉非和云扬这才带着虎头与玉带两个小队撤下山去。
这时,云汀率领的鹰军大队人马已经与自东而来的敌军接站,并有效地组织了对方的行进速度。
不过,虽然敌人的行动变得迟缓,却仍然会在五、六个时辰后到达这里。
宁觉非收到云汀的飞鹰传书后,陷入了沉思。
47
宁觉非离开临淄已经五天了,西线没有任何消息,南线倒是捷报频传。
荆无双和李舒分别与北蓟和南羌争战多年,对于异族铁骑并不陌生,也丝毫不怵,打得有声有色。不过,对方是游牧民族,战法灵活,不拘一格,往往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荆无双和李舒在数日内与他们接战过若干次,消灭的都是小股敌人,并未损伤他们的有生力量,甚而脸个别高阶一些的军官或首领都未消灭或擒获,因而这些捷报只能用来安定民心,稳住朝廷大势,对整个战局却并无太大作用。
对此,无论是澹台牧、云深还是兵部的即位高官都心知肚明,却并不多说什么,只做出适度的欣慰模样,并对荆无双和李舒这两位南楚降将深表赞赏。
战火燃于西南一隅,朝中重臣并没有太多担忧,他们有许多人都在观望,看那位花花太岁鲜于琅最终会有何种结局。
云深日日都在宫中处理政务,再也没有去临淄府衙。宁觉非离开的第三天,澹台牧便下旨,钦定由刑部尚书解体临淄府尹处置鲜于琅的案子,要求他按律行事,勿枉勿纵,将结果从速上奏。
圣旨一下,便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朝臣们纷纷私下议论,猜测皇上的意思,可澹台牧的心思深沉如海,他们又哪里敢妄加断定,于是便将心里的忐忑不安付之于行动。一时间,到右旌侯府和国师府拜会的人川流不息,从下了朝直到入夜,均是如此。
云深始终不动声色,吩咐总管闭门谢客,只接见一些重要的官员,说的都是公事。那些人都是朝中高官,最懂的中庸之道与察言观色,这时只字不提鲜于琅的案子,心中却已有数。
昨天,大檀明回府后,与自己的妻子昭云公主闲聊,故意将鲜于琅辱骂宁觉非的事告诉了她。于是,此事很快便在权贵间的内宅里传开,之后当然便迅速被那些朝廷重臣们知晓。
一开始,这些大臣都不认为侯爷公子伤害了一个下人就会判罪,可现在却不这么想了。鲜于琅出言恶毒,侮辱宁觉非,那就是大逆不道了。皇上将天下兵权尽皆交予宁觉非,可见对他有多么宠信。宫中和兵部更有人传出,宁觉非被辱骂的当天夜里,晕倒在兵部大堂,皇上赶去看他,竟亲手将他抱出衙门,带进宫中,安置在御书房,甚而亲自端汤喂水,照顾得无微不至,荣宠殊甚,已是无与伦比。此后,宁觉非称病不朝,皇上便委任刑部尚书过问此事,圣旨中更是用词眼里,似无转圜余地,那此案最后的结局基本上已是显而易见了。
这么一来,有很多属于云深这一系或保持中立的大臣便暗自拍手称快,而偏向鲜于琅一方和一些皇亲国戚便感到忧虑,纷纷进宫求见澹台牧,为鲜于琅说项,恳请皇上看在澹台和鲜于两族的情分上,高抬贵手,小惩大诫,也就是了。更有人频频去往小仓山下的望北苑,相见宁觉非,却都让云深派到那里的人挡了回来。
朝中暗流汹涌,处于漩涡中心的几位当事人却都是若无其事的模样。
鲜于骏每天都在户部衙门办公,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更全力为前方的军队调运粮草。
云深尽忠职守,忙得连轴转,领导或督促着诸项大事迅速向前推进。
澹台牧每天都是三更眠,五更起,日理万机,又是御书房里的灯更是通宵不灭,伺候的宫女太监则按时换班,动作却都很轻,深怕打扰了这位勤劳国事的君王。
太子澹台经纬也整天守在父皇和舅舅身边,学着参与政事,努力为他们分忧。
宁觉非的元帅府里却特别安静,江从鸾严格约束所有下人,无事不得出府,更不准在外面胡说八道。那日松终于从昏迷中醒来,性命已然无碍,精神却遭受到沉重打击,一直不言不语。其其格和江从鸾对他悉心照顾,温柔劝解,虽然收效甚微,两人倒也不急,打算先把他的身子调养好,再缓缓开解。
淡悠然则保持着商人本色,对政治毫无兴趣,每日里进进出出,筹建临淄的悠然阁。如果江从鸾有空,便会被他拉出去看地方,选各种改建房屋的材料和字画摆饰。淡悠然很诚恳地希望他提供意见,江从鸾非常感动,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两人天天出双入对,看在别人眼里,便有些流言渐渐传了出来。江从鸾有些不安,淡悠然却照样拉着他有说有笑,亲热依旧,江从鸾也就坦然起来,将自卑的心思收拾了,不再去管别人口中的是非。
日子就这么在表面的正常中一天天过去,人人都拭目以待,等着看事情的发展。
当宁觉非离开临淄的第八天,刑部尚书向澹台牧递上了奏折,里面罗列的案由清晰,证据确凿,最后的结论是,根据北蓟的刑律,按罪应判斩立决。
第二日早朝,澹台牧要刑部尚书当着群臣的面将这番话重述一遍。刑部尚书一向刚正不阿,便在朝堂之上直言不讳,将案说明,然后背出北蓟律中的有关条款,清楚明白的说出判决。
他的话音一落,朝中大哗,鲜于骏的脸色变得惨白,抬头看向澹台牧,颤抖着声音说:“皇上,老臣深知犬子罪孽深重,究其根源,全是老臣之过,教子无方,致使他犯下大错。恳请皇上念在老臣一门数代忠良,家门不幸,仅有此一子的份上,饶他一条狗命。老臣愿削职为民,交出侯爵之位,以赎犬子的罪衍。皇上……”说着说着,他猛地跪了下去,连连磕头,已是老泪纵横。
朝堂之上顿时鸦雀无声,群臣束手,等着皇上表态。
沉默片刻,澹台牧缓缓地道:“鲜于卿家,你且起来说话。”
鲜于骏这几日表面平静,其实已是神困体乏,挣扎了一下,竟然站不起来。他身边的云深一声不吭,却俯下身去,伸出双手,用力将他搀扶起来。
他这举动令所有大臣都感到诧异,有人深深钦佩,有人暗骂他虚伪,表面却不言不动,静观其变。
等鲜于骏站稳,云深收回手,恭敬而立,澹台牧这才沉声说道:“诸位卿家都是朝廷柱石,国之栋梁,当深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鲜于卿家,你乃皇亲国戚,身为右旌侯之尊,又执掌国之命脉户部,由此可见,朕一直对你寄予厚望,你就更应以身作则。澹台、鲜于、大檀是我国中三打大显贵家族,世代联姻,朝中恐有三分之一的大臣与这三族有亲缘关系,若是有罪而不究,岂不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行下效起来,这天下岂不是要大乱?鲜于卿家,朕这话在不在理?”
鲜于骏顿时哑口无言。若说皇上无理,那是以下犯上,乃大不敬之罪。若说皇上有理,那自己的儿子就要人头落地。他心里一急,有想要跪下,想起刚才皇上有口谕,要他起来说话,便不敢再跪。他的脸色越来越白,在一片寂静中,忽然倒了下去。
群臣猝不及防,大殿中一片哗然。
云深最先反应过来,立刻蹲下身去,将侧倒在地的鲜于骏,轻轻翻过身来,让他平躺,随即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替他把脉。
澹台牧也站起身来,对身旁的太监说:“快,传御医。”
那太监一溜烟地跑了,太监总管是人精,不等皇上发话,便指挥几个小太监奔去拿来春凳,将鲜于骏抬上去放着。
这么一来,事情也议不下去了,澹台牧只得挥了挥手。
太监总管便高叫一声:“退朝。”
那些大臣们却左右为难,有的觉得应该留下,对鲜于骏表示关切,以免皇上觉得自己凉薄,不关心同僚,有的又害怕留下会被皇上认为自己是鲜于骏一党,受到无谓的连累,这一走一留间,便花费了无限心思,脑中转过无数念头。
云深的言行举止却是一派磊落大方,抬头对澹台牧说:“皇上,鲜于大人这是一时心急攻心,并无大碍,只是,须得卧床静养几日,待御医来了,给鲜于大人好好开个方子,鲜于大人只要依时服药很快便能痊愈。”
“如此甚好。”澹台牧缓步走下丹墀,来到鲜于骏身前,关切地看了看他的脸色,便抬头对围在四周的大臣们说:“众卿家都回去办差吧,有什么事就上折子来,及时奏与朕知。”
“遵旨。”群臣躬身施礼,恭敬作答,这才送了口气,有序地缓缓退下。
这时,一个太监飞快地送上一张铺有软垫的椅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皇上身后。澹台牧却没有坐下,沉思片刻后,示意云深与他一起出殿。
来那个人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看着众位大臣走向宫门的身影,半晌没有出声。
过了一会儿,澹台牧轻叹:“鲜于骏一生清名,全毁于逆子之手,实在可惜。鲜于氏有大功于国,要说起来,也勉强可以饶鲜于琅不死。可是,朕若想正本清源,就绝不能姑息,否则,本是疥癣之疾,却会成为心腹大患。”
“陛下英明。”云深发自内心地说。“鲜于琅作恶多端,其罪当诛。鲜于大人亦并不似往日在蓟都时谨慎从事,严于律己。他与一些南楚旧臣过往甚密,常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更出言不逊,诋毁觉非,鲜于琅耳濡目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