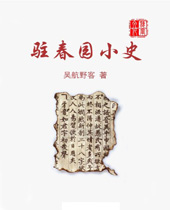乳房的历史-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先缫窖纷髡叨诺ぃ˙arbara Duden)所言,这些女人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触犯了“勿视、勿触”的禁忌。传统上,不管是在医师的诊疗室或病患的卧房里,女患者都必须衣着整齐,不能让医师触诊,只能口头说明病征。
多数乳癌病患总是拖到没办法才找医师,这时病情通常已经进入末期,手术后也活不久。就算及早就医,乳癌病人也未必能够存活,因为当时的手术缺乏消毒,病患往往死于手术感染或败血症,英国女作家艾丝戴尔(Mary Astell)便是一个例子。1731年,63岁的艾丝戴尔发现乳房有肿瘤,她一直等到肿瘤变大、溃烂,才去找著名的苏格兰医师约翰生(Dr。 Johnson),请求他私下为她动手术。根据记载,艾丝戴尔“既无挣扎、也无反抗,甚至没有抱怨磋叹”,便接受了乳房切除术。但是她的勇敢无助于病情,癌症未因手术得到控制,两个月内仍是急速恶化,艾丝戴尔随即死亡。
17、18世纪时,医界仍信奉盖伦的理论,认为乳癌起因于体液的腐败或凝结,因此多以食疗调整体内平衡,包括让病人饮用矿泉水、牛奶,或者鸡肉、青蛙、蟾蜍熬成的汤,甚至使用通便剂或者断食疗法。放血被认为可以除掉多余的体液,恢复体内平衡。外敷治疗则多用湿布与膏药,或者龙葵属、莨菪、车前草等有毒植物的汁液,以及使用砒素、铅与水银制成的敷剂。甚至以烂苹果、尿液按摩贴压胸部,或者生宰鸽子作法治疗。
越来越多医师赞成较积极的治疗手段,他们依据荷兰、法国、英国与德国的医学论文指示,为病人开刀切除肿瘤。在众多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海斯特(Lorenz Heister)的三册巨著《外科通用系统》(General System of Surgery),这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从拉丁文被翻译成德文与英文。海斯特自称摘除过无数“大如拳头”的乳房肿瘤,有的甚至重达12磅!就如同19世纪中期所有手术一样,海斯特的手术也全无麻醉,只靠酒精,或偶尔仰赖鸦片给病人止痛。
最早的乳癌患者自述,勇气可嘉
英国女作家柏妮(Fanny Burney)详细记录了她在1811年10月接受乳房切除术,我们从她写给家乡姐妹的书信中,获得了可贵的病患第一手陈述,它们不是医师观点,也不是后世传记作者的想法,而是一位乳癌病患的主观陈述!
柏妮的丈夫是达尔布莱(Monsieur d’Arblay),法国大革命期间逃亡至英国,娶了柏妮。革命结束后,夫妻俩返回巴黎,受到上流社交圈欢迎。当柏妮的乳房疼痛日益频繁剧烈,她求助于拿破仑著名军医拉黑伯爵(Baron Larrey),拉黑与两位同行研究后,决定为她开刀。巴妮写道:“圣父、圣子、圣灵正式判决我必须接受手术,我感到震惊,也觉得失望,因为可怜的乳房并未变色,甚至不比另一只乳房来得肿大。”柏妮忧惧“病魔深植”、生命垂危,同意接受手术。
医师告诉柏妮,手术前4个小时才会通知她,柏妮认为这倒是好事一桩,她的勇气不致因漫长等待而溃散,可以搏斗“迎面而来的打击”。3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柏妮仍在床上,仆人通知她医师10点来帮她开刀,柏妮坚持手术延到下午,她才有时间准备。手术在她家中进行,柏妮回忆:
我漫步进入客厅,看到它已经布置妥当作为手术房,我连忙退了出来,但随即还是转身进入客厅——自我欺编,又有什么用处?虽然看到堆积如山的绷带、压贴布、海绵、软绷带麻布,让我颇不舒服,我还是来回踱步,直到我的情绪完全平静,某种程度来说,是几近麻木、呆滞的状态。茫然中,我听到时钟敲了三下,涣散的精神突然又回过来,我振笔疾书了几行字给达尔布莱与亚历斯(柏妮的儿子),预防自己在手术中遭逢不测。
那个时代,罹患乳房肿瘤仍是件非常隐秘的私事,只能跟最亲近的人透露,而且多是用词隐讳。柏妮当时已经是个作家,写过小说《艾薇莲娜》(Evelina)及其他作品,她知道自己写给姐妹的书信,一定会转给娘家亲人与好友看,不会被束之高阁,遣词用字非常小心。她写道:
莫洛医师随即进入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还活着。他给了我一杯加味酒,然后走进客厅。我按铃叫女仆与看护进来,但是我还来不及和她们说话,七名黑衣男士便在毫无通告下,突然闯进我的卧房,他们是拉黑医师、杜比尔先生、莫洛医师、欧蒙医师、雷比医师及拉墨医师与杜比尔医师的两名学生。我从茫然中惊醒,觉得被侵犯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请擅入?
柏妮觉得毫无自尊、极端害怕,当医师叫她爬上客厅里的手术床时,她“迟疑了一会儿”,想要转身逃跑。接着她听到医师下令女仆与两名看护离开房间,她回忆:“我大声喊叫:不要!让她们留下来!我和医师们起了一阵争执,从茫然中活了过来,但女仆和一名看护还是趁乱跑掉了,我命令剩下的那名看护趋前,她听命了。这时,杜比尔医师强力把我按到床上,我则抵死反抗。”
顽强的柏妮和命运困兽犹斗,企图以女性的柔弱力量对抗男性的武勇。她的仆人叛逃了,只留下一名女看护,协助她对抗一屋子男性的“屠杀”。在痛苦的奋战中,她模糊地想起了远在英格兰的姊妹,仿若她们是她的保护力量。
柏妮对此场手术的描绘,至今仍是乳癌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她的语调清晰平静,让读者惊讶于她在手术过程中的勇敢,也讶异她在手术后如何鼓起勇气,记录下痛苦无比的经历。
柏妮描写自己平躺在床上,脸上只蒙着一条薄棉手帕,手帕十分透明,柏妮可以清楚窥见所有过程。当她紧闭双眼,逃避“刺眼的金属器材亮光”,听到拉黑医师低沉的声音问道:“谁帮我拿住这个乳房?”柏妮回答道:“我来拿。”这时她才感觉到医师的手指在她的乳房“比画出一条直线,从乳房上方到下方,再画一个十字,然后一个圆圈”,意指整个乳房都必须切除。这时,柏妮再度闭上双眼,“放弃所有的窥视、抵抗、干扰,悲哀地决定全面弃守。”
这时,她感到一股“生平最残酷的痛苦袭来”。
当可怕的金属刺进我的乳房,穿过并割断血管、动脉、肌肉与神经,再也没有任何针剂可以抑制我的狂叫。我凄厉地放声尖叫,整个手术过程,我都哭喊个不停。我甚至诧异现在耳内居然不再回萦着当时的刺耳尖叫!那种痛苦实在太折磨人了,即使伤口切开、器材移开后,痛苦仍未消失,因为空气突然冲进脆弱的肌肤内部,好像无数细小尖锐的匕首在戳刺拉扯着伤口。
柏妮继续回忆痛苦的细节,包括“恐怖的切割”,感觉到刀子挖刮着肋骨。手术虽只进行了20分钟,但是她全程清醒,惟一的麻醉剂只是一杯加味酒。难怪手术后足足一年,柏妮才提起勇气“谈及这件恐怖的事情”,记录下手术的过程,成为最早的乳癌手术患者自述。
医界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
幸运的是,柏妮在手术后又活了30年,另外一位患者就没有这么幸运。就在柏妮接受乳房切除手术的同时,美国也有一位女子接受相同手术,却在2年后死亡,这位患者名叫艾比吉儿·亚当斯史密斯(Abigail Adams Smiths),她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35一1826)的女儿。最近坊间才出版了亚当斯夫人的传记,提及了艾比吉儿接受乳房切除术的故事,说艾比吉儿写信给著名医师罗许(Benjamin Rush,1745…1813,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提及自己的乳癌征状:
我发现右边乳头上方有一个硬块,不时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像是灼热感又像瘙痒惑,有时乳房深处会传来刺痛,乳房的颜色虽未改变,却持续萎缩,变得比以前小,肿瘤逐渐浮现,约莫瓶盖大小,好像要自乳房剥落下来似的……
罗许并未直接回信给艾比吉儿,而是写给她的父亲亚当斯,提议她的乳癌可以“切除”了。艾比吉儿信服罗许50年的行医经验,几个星期内便接受手术。一个月后,亚当斯夫人写信给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说他的妹妹“手术后状况良好,乳房整个都拿掉了”。手术后第一年,艾比吉儿认为自己已摆脱病魔,但是那年冬天,她的健康便开始恶化,于第二年八月平静离开人间,过世前,母亲陪伴在侧。亚当斯夫人哀痛逾恒,在无数的信函中倾吐自己的悲伤,毫不隐讳地讨论在当时仍属私密的乳癌:“丧女之痛撕裂了我,胸前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悲伤的比喻吻合了女儿的恶疾。
当时医师为了教学,手术常在看台式手术室(amphitheatre)里举行,约翰布朗(John Brown)医师永远不能忘怀1830年他仍是学生时,在爱丁堡一个拥挤的手术室里,与许多同学一起观看乳房切除的经验。20年后,布朗在《雷布与他的朋友》(Rab and His Friends)一书里记载了那次经验,患者名叫艾莉,是苏格兰农妇,在丈夫詹姆斯与爱犬雷布的陪伴下,穿着家居服步入手术室。医师迅速地进行手术,雷布见到女主人血迹斑斑,不断嚎叫。手术过程全无麻醉,艾莉以无比的勇气承受痛苦,手术结束后,她“缓慢爬下手术台,眼光搜寻着詹姆斯,然后回头以低沉清楚的声音向医师与旁观的学生道歉,说她如果表现得不够勇敢,请原谅她。”自惭与歉然的态度是当时乳癌患者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家贫的病人,她们关心医师手术过程是否舒适,远胜过关心自己的健康。不幸,这位勇敢的村妇在几天后死于败血症。
虽然19世纪的乳癌治疗方法很残酷,当时的科学家对乳癌的基本结构了解日益增多。首先,德国的谢理登(Matthias Schleiden)与许旺(Theodor Schwann)指出,细胞是动物与植物的基本物质。穆勒(Johannes Muller)继而确定了病变肿瘤也和其他组织一样,是由细胞构成;莱柏(Hermann Lebert)则发现了癌症细胞,其状小而圆,内有椭圆形细胞核。1854年,卫尔浦(Alfred Velpeau)在《论乳房疾病》(Traite des Maladies du Sein)一书中,总评所有的乳房研究医学文献,发现自从显微镜诞生以来,乳房病变研究有长足进步。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科学可以制造奇迹,形成了医学独断主义的氛围,逐渐影响女人的生命。
其实到了18世纪时,医学界已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试想,卡多甘医师写作《哺乳论述》时,他的对象还是医界同仁,但是到了19世纪,医界写作的新潮流是针对女人,不久后,女人便习惯寻求男医师的指导与咨询,放弃产婆、女性疗者等传统支援体系。换言之,大众是在18世纪起开始迷恋科学,不再认为宗教是人生全方位的指弓}。
纳菲博士(Dr。Naphey)在1869年出版《女性生理的一生》(The Physical Life of Woman),广受欢迎。他在此书的生育一章里,主张他的哺乳原则有益所有母亲,建议产妇应当在孩子诞生后马上喂食母乳,因为“妇人产后立即泌乳,而婴儿需要母亲乳房最初分泌的乳汁。”医界终于明白了初乳的重要性。
医学界同时也提出统计数字的证据,指出喂食母乳比奶妈哺乳、使用半固体状的“代乳”要好得多。纳菲指出,里昂、帕特内等欧洲城市养育院的婴儿,普遍由奶妈哺乳。死亡率分别高达33。7%与35%;巴黎、理姆斯、爱克斯(Ax)等地的养育院婴儿则多食用代乳,死亡率更分别高达50。3%、63。9%与80%;纽约市养育院里的孩子也是食用代乳,死亡率更是将近100%。有了统计科学做后盾,纳菲的建议形同“医师命令”,他说:“婴儿出生后的头四个月至半年里,只应从母亲的乳房吸取养分,许多婴儿最好是吃食母乳一年。”从此,母亲对婴儿的责任并未纾减,反而加重,医师仿佛传道士或教士,用“应该”、“责任”、“义务”等字眼命令母亲哺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聘请奶妈哺乳的习惯消失,人们逐渐仰赖奶瓶喂奶,牛乳或羊乳成为最重要的母乳替代品;生母哺乳还是奶妈哺乳的古老争议,也被奶瓶喂食还是哺育母乳的争议取而代之。虽然多数人仍认为母乳是最好的,却很少人认为它攸关婴儿存活。医学统计而言,西方婴儿已不再因奶妈哺乳或饮用未经消毒的动物乳汁而有早夭危险。
但是乳癌就另当别论了,打从19世纪末起,人类寿命延长,癌症罹患率也跟着提高,成为现代医学的焦点,一如中世纪的瘟疫、文艺复兴时期的梅毒,或者19世纪的肺结核。在所有的癌症当中,乳癌的普及率堪称达“流行病”标谁,直到今日,科学家依然不明白乳癌为何会发生。医学界只能确定,乳癌始自乳管内部的异常细胞,这些恶性细胞不断增长繁殖,迅速挤满乳管,乐芙医师(Susan Love)形容它为“水管生锈”。最后,这些狂乱繁殖的恶性细胞冲破乳管壁,侵入乳房组织。如果不治疗,乳癌会持续移转,侵入腋下淋巴结,蔓延至骨头、肝脏、肺部与其他淋巴结。
癌症妇女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
为了治疗乳癌,医界在过去150年里发展出4种疗法,分别是手术、放射线治疗、化学疗法与荷尔蒙疗法。
19世纪下半叶,医界发明了麻醉与防腐剂,让传统乳癌手术出现了曙光。麻醉法发明者为牙医摩顿(William Morton,1819…1868),1846年,他在波士顿的麻省综合医院开刀时,首度使用乙醚为病人止痛。1864年,巴斯德提出细菌理论,医界开始研究消灭病菌法,直到英国外科医师李士德(Joseph Lister, 1827…1912)发明防腐剂。才广泛使用于外科手术上。
1867年,另一个杰出的英国外科医师摩尔(Charles Moore)确立了乳癌外科手术准则,他认为乳癌复发是因为癌细胞未清除千净,为了防止复发,必须切除整个乳房,包括乳房皮肤、淋巴、脂肪、胸部肌肉与感染癌细胞的腋腺。
19世纪末,由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哈尔斯蒂特(William Halsted)医师发展出来的乳房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