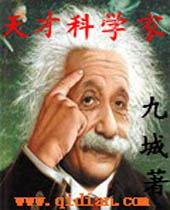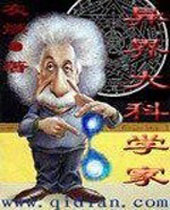77历史学家 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亲叹了口气,靠墙站着,一只脚搭在一块石头上。
我没敢问他对餐馆经理的故事为何反应那么奇怪,但我觉得,对于父亲来说,有些故事比他以前告诉我的要更加可怕。这一回,无需我开口求他,他已经要开始讲了,好像他现在喜欢更可怕的东西。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八章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如果我告诉您,我现在枕着一圈大蒜头睡觉,我虽是无神论者,却在戴着一个项链,上面有金色的十字架坠子,您是否不会感到那么困惑?当然,我没有这样做,但如果您愿意,您尽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样的护身符。在智力上,在心理上,它们都其对等物。至少,我日夜坚守着后者。
让我继续讲述我的研究:是的,我去年夏天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到了伊斯坦布尔。促使我改变行程的是一张羊皮纸。我跑遍牛津大学和伦敦,寻找所有与我那本神秘的空白书上那个德拉库拉有关的资料。为此我做了一捆的笔记。
在我离开希腊出发的前夜,我真地是想要放弃这毫无意义的研究,事实上,就在我把干净的衬衣和旧太阳帽放进旅行包时,我还突然有了一种要向命运低头的感觉,我几乎就要放弃所有这一切了,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然而,我做事总喜欢抢在时间的前面,所以那天我在睡觉起来去赶早班火车之前还有点儿时间,最后一次去图书馆的珍本室,它到九点才关门。那里有份档案我想碰碰运气(尽管我怀疑它会给我的研究带来光明)。在奥斯曼这一词条下有份材料我觉得刚好是属于弗拉德·德拉库拉生活时期的,我看到那里所列的文献大都是中世纪到十五世纪晚期的。
我毫不费劲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里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长的羊皮纸卷,是奥斯曼人手工制作的,都是十八世纪捐献给牛津大学的礼物。每卷上标的都是阿拉伯文。
文献最前面的英文介绍显示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叹了口气,把那些羊皮纸放回到盒子里去,这时,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份简短的清单,是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呈送苏丹的官文,背面是一通随意的涂画,古老的涂画,好像是一张开支的清单——买的东西都记录在左边了,价格写在右边,用的是一种我看不明白的货币单位。
“献给苏丹五百头山狮,45,”我绕有趣味地念道。
“献给苏丹两根金宝石腰带,290。两百张羊皮,89。”
看到最后一条,我手里捧着羊皮纸,不禁毛骨悚然:“龙之号令的地图和军事记录,12。”在它下面标有一个几乎要被抹去的年份,却烙印在我脑海里的:1490年。
我记得,1490年龙之号令已经被奥斯曼帝国击垮。根据传说,这时弗拉德·德拉库拉已经埋在斯纳戈夫湖有十四个年头了。和那些宝石腰带和羊皮相比,龙之号令的地图、记录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实在是便宜。也许它们是商人最后顺手买来的,这里的这个商人是不是一个巴尔干旅行者,能写拉丁文,会说一点斯拉夫语或者从拉丁文衍生的某种方言?不管他是谁,我都祝福他脚下的尘土,因为他记下了这些开支。
我走去服务台,管理员在检查一个抽屉。
“对不起,”我说。“你们这里是否有按国别分类的历史档案目录?比如说,土耳其的档案?”
“我知道您在找什么,先生。大学和博物馆有这样的清单,但肯定不完整。我们这里没有,但中心图书馆的服务台可以给您。他们早上九点开门。”
我记得去伦敦的火车十点零四分才开。我只要大约十分钟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性。如果在这些可能性当中出现了苏丹迈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那么,我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去看希腊的罗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巴托罗米欧·罗西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3日
时间好像在那个高穹顶的图书馆大厅停滞了,尽管我周围人流如故。我读完了整封信。那一叠下面还有四封。我正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又看了看她,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然后,我继续盯着她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但又好像略为显老,眼角有点皱纹,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她读的书——我又看一眼,又一次惊讶不已——是《喀尔巴阡山记的》,而她深色套头衫袖子压的是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对不起,”我连忙说。“您的书——我是说,您在读的这本书——很吸引人。”
她不理会我,耸了耸眉毛,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坚持说。
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
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
“德拉库拉?”她讽刺地说。“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她讲话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换了一种策略。“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我的意思是,为了娱乐?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
“好玩?”她没有关上书,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
“呃,这个话题非同寻常,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我没有说得太快,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事实上,是那两本。”
“真的?”她说。“为什么啊?”
“这个嘛,”我冒险说道。“我从——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一点兴趣,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性的自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
“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他把我交给了我,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脱眼下的——处境——目前这种处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
“我明白了,”她冷冷而有礼地说。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宽肩,有点儿结实。
“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我绝望地问道。
“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转过身去。“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
“去喀尔巴阡山?”我突然觉得,在这场谈话中,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
“不。”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去伊斯坦布尔。”
“天啊,”父亲突然对着充满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
“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又一次,父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
“看,”父亲说,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
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发现上面有个地方,灯光微弱但平稳。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高悬在那里,但又不是在顶峰——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
“是的,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父亲又说了。“我们明天要真正爬山了,即使我们走大路上去。”
我们再次漫步在没有月光的街道上,这时,我感到一种从高处坠落下来的失落感,告别了某种高尚的东西。
我们在古老的钟楼处转弯,我又一次回头看了它一眼,让那点微小的亮光刻在我脑海里。它还在那里,在一面墙上闪烁,墙外是黑暗中的九重葛花。我不觉安静地站在那里好好看了它一会。就在那时,灯光闪了一下,就一次。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九章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我将尽快结束我的讲述,因为您必须从中得到重要的信息,这样我们两个人——啊,至少能幸存下来,能在仁慈和怜悯中继续生存下去。
还是续上前话吧:我从英国到希腊的旅程异常顺利,这样顺利的旅行我平生有过几次。在这样的田园风光中,我都考虑过完全放弃追索德拉库拉这个名字,在我看来这是个恐怖的幻想。我一直把那本古书带在身边,不想和它分开。但现在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打开它了,我觉得自己从它的诅咒下解放了出来。但是有点什么东西——一个历史学家对周密的热爱,或者就是喜欢追逐些什么——让我坚持计划。接下来我还要讲几件事,它们都可能会让您觉得不可思议。我请求您读完。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4日
父亲说,我听从他的请求,读完了每一个字。
那封信再次告诉我罗西在苏丹迈米德二世文件中骇人的经历———他在其中找到一张用三种语言标识的地图,好像指示出弗拉德·德拉库拉墓的方位,后来这地图被一个阴险的官员偷走了,那官员脖子上有两个很小的刺孔。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写作风格缺少前面两封信的严谨,文字单薄,像是受到了什么干扰,好像他是在极度不安中打下这些东西的。尽管我自己也很不安,我注意到他讲述的语言,和两晚前他给我讲那些事时的语气是一致的。
还剩三封信,我迫不急待地去读下一封。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自从那个可恶的官员抢走了我的地图,我就开始倒霉了。我回到房间,发现旅馆经理已经将我的行李搬到了一个更小更脏的储藏室,因为我房间房顶的一个角落有东西掉下来。在搬东西的过程中,我的一些文件不见了,一对衬衫袖的金链扣也不翼而飞。
我坐下来,马上开始根据回忆重写我关于弗拉德·德拉库拉历史的笔记,然后从那里赶回希腊,打算继续我的克里特研究,因为现在空闲时间多了。
到克里特的海上航行真是可怕。我想继续写我的克里特,但是我看了那些笔记完全没有灵感。从镇上的人那里听来的迷信也没有让我稍稍心安。我以前来没太注意,其实这些迷信在希腊广为传播,我应该早就知道的。
按照希腊传统的说法,其他很多地方也一样,吸血鬼的源头叫弗里柯拉克斯,指的是任何死后没有埋葬好的尸体,或者腐烂得慢的尸体,更不用说那些被意外活埋的了。
克里特酒馆里的老人们更愿意给我讲他们二百一十个吸血鬼的故事,而不愿告诉我在哪里找到类似那一块的陶器碎片,也不愿说他们的祖先钻进哪些古代的沉船中掠夺东西。
我把这些写下来,心想也许它们和我遇到的其他情况有儿点联系,至少它们可以告诉您我到达牛津大学时的状态:精疲力竭,沮丧万分,心惊胆战。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脸色苍白,瘦削。在如此的不安中,我在刮胡子时经常笨手笨脚,划伤自己。只要一被划伤,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退缩,想起那个官员脖子上的那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更加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有时,我被折磨得几乎要发疯,好像自己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有某个目标我没法搞清楚。我很孤独,充满渴望。一句话,我进入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状态。
您最痛苦的,
巴托罗米欧·罗西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5日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十章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一直都了解时间馈赠给旅行者的那份特殊礼物:想要故地重游的渴望,想找到从前跌跌撞撞走过的路,重新获得那种探索的感觉。
非常年轻的旅行者不会了解这一点,我自己就不了解,但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他在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修道院的举动让我感到了重复的神秘,我知道他多年前到过这里,而且这个地方把他带入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微妙境界。他想来这里,悄悄回忆曾经来过的经历。我已经明白了,父亲记住的其实不是建筑,而是发生在那里的事情。
一个身着黄色长袍的修士站在木门边,默不作声地给游客派发宣传小册子。
“我告诉过你,这个修道院还开放,”父亲平静地告诉我。我莫名奇妙地确信,父亲在这里出过什么事。
和我的第一个印象一样,我的这个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闪而过,但更加敏锐:他打开小册子,一只脚迈上石头台阶,非常不经意地低头看了看那上面的文字,而不是抬头看我们头顶的动物装饰。我看得出,我们就要迈入这一圣所,而他对它旧有的感情没有消失。
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修道院坐落在海拔四千英尺的山上,走进门去就是圣马太小巧的教堂和它精致的回廊,好像是一位有艺术品位的力士参孙的杰作。我们一进门就被一阵滴水声吸引住了。在那么高,那么干燥的地方竟然有如同山泉一样自然的水声,令人叹为观止。
“隐居的生活,”父亲坐在我身旁的围墙上,喃喃说道。
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怪怪的,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