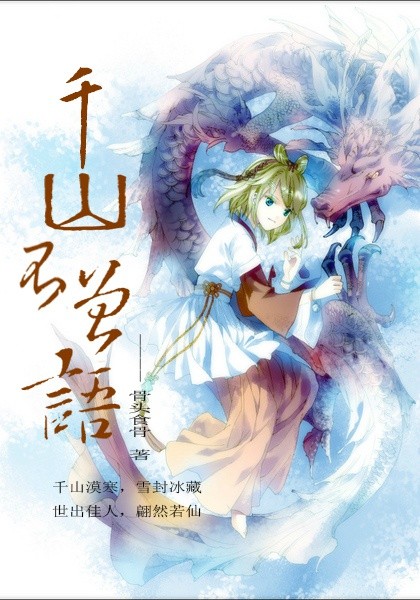千山看斜阳[第一部·南楚篇] (穿越时空)by 满座衣冠胜雪-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些人齐声答应:“是。”
宁觉非带过烈火来,赤龙却嘶鸣了一声,似乎很是不舍。
烈火也频频转头去看它,眼中满是依恋。
宁觉非听说这烈火自小便没见过父亲,倒是很理解它此时的感情,不由得犹豫着,没有硬拉它离开。
独孤及看着他道:“兄弟,不如去鲜于氏的大帐,我们好好喝喝酒。”
宁觉非略一思忖便爽快地点头:“好。”说着,便上马,与他们疾驰而去。
鲜于氏果然是北蓟的三大望族之一,族长的大帐气势雄伟,周围还有数十顶小帐篷,虽是在草原上临时搭建,却也像一个寨子一般,应有尽有,热闹非凡。
宁觉非跟着独孤及一路前行,看到的都是笑脸,不过仔细观察大家的表情,似乎连这里都很少有人真正知道独孤及的身份,只知他是族中的显贵外戚。
独孤及只对人说宁觉非是他的兄弟,大家也都不问别的,只管端出美酒佳肴相待。这一晚,歌舞醉人,酒香怡人,宁觉非与众多草原的汉子推杯换盏,又被豪爽的姑娘们逼着学唱祝酒歌,还追着劝酒,笑闹之中,竟是喝得酩酊大醉。
等到月上中天,众人大都醉倒,独孤及也是醉眼朦胧,呢喃道:“兄弟早些休息吧。”便倒在帐中的地毯上,呼呼大睡起来。
宁觉非撑起身,踉跄着走出帐去。本是内急,待出得帐外,被夜晚的冷风一吹,他已忘了出来的目的。酒劲一阵上冲,不由得低头大吐特吐。等把积在胃里的酒肉吐了个干净之后,却是清醒了一些。
他抬起头来,脑中一片空白,一时已想不起怎么会身在此处。
“烈火”低低的嘶鸣却近在耳边。
迷迷糊糊中,他骑上了马背。
“烈火”老马识途,竟穿越草原,奔回了蓟都,轻车熟路地回到了国师府,停在了府前。
因宁觉非没回来,云深吩咐了家人在门前守候,此时赶紧上前接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将他抬回了屋。
云深惦记着他,本就睡得不熟,此时听到动静,便披衣而起。看着宁觉非大醉而归,他不由得双眉紧皱,赶紧叫人准备热水,侍候他洗漱沐浴。
忙乱间,已有人端来酽酽的热茶。宁觉非正觉渴得厉害,立即大喝了一气。
家人们将木桶注满了热水,便要帮他宽衣。
即使在醉中,宁觉非都似对此类动作十分警觉,立即抬手握住了那双手,喃喃地道:“滚开,滚开。”
那人的手腕被他大力一握,疼得差点叫起来。
云深立刻上前,温言道:“好好好,你先放开他。”
听到云深温柔的声音,宁觉非安静了些,双手便松了开来。
云深知道喝醉了的人重有千钧,便干脆叫家人连衣带人将他扔进了水中。
宁觉非嘻嘻笑道:“游泳吗?温水?恒温游泳池啊?好久没见到过了……”说着,两手已在缓缓地划水。
云深看着他,见他面若桃花,醉眼中波光流转,唇边带着天真的笑意,犹如孩子一般可爱,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他叫家人避出门去,自己挽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嘴里轻声哄着,伸手在水中替宁觉非解下了衣服,随后拿起毛衣,替他仔细地擦过醉意盎然的脸,擦过匀称的身体,只觉得他那细腻却伤痕累累的肌肤下仿若有力量如水银一般流动,就像一只小豹子一样,漂亮而充满了活力。
等到洗完,云深使足力气将他拖出了浴桶,赶紧用干毛巾替他擦干身上的水滴。
宁觉非冷得一哆嗦,忽然恢复了几分清醒。
睁开眼,只见一灯如豆,恍惚地照着一双温柔如水的眼睛。
他怔怔地看着那双熟悉的眼睛,看着那熟悉的温情,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无比辛酸地轻声问道:“是你吗?是你吗?”
云深一听,不由得一愣,抬眼一看,便瞧见了那一双平日里水波不兴的眼中满是绵绵不绝的忧伤。他的手不由得停了下来,情不自禁地想先抹去那眼中的悲凉。
他的手刚刚触到宁觉非的眼睛,忽然腰间一紧,便被沉沉地压在了床上。
宁觉非紧紧地搂住那温暖绵软的身体,将唇压在了那双熟悉的眼睛上,喉间一直低低地呢喃道:“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宁觉非紧紧地搂住了云深的腰,伏在他的身上。他灼热的唇轻柔地吻着云深的眉眼、鼻梁,最后轻轻地贴在唇上。
他的呼吸之间,全是醇酒的香浓。
云深在他搂上来的时候,身体骤然有些发僵,这时才慢慢地放松了下来。他缓缓地抬手圈住了宁觉非的身体,温暖的双手放在他已变得有些凉的背上。
云深身上穿着丝绸的中衣,隐隐地散发着青草一般的清香。宁觉非伏在上面,仿佛觉得自己正趴在春天的草原上,渐渐地有些沉醉。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与云深在唇齿间深深地纠缠着。那柔软的嘴唇,有些犹豫的舌尖,都勾起了他更深的欲望。
他急迫地伸出一只手,想去撩开身下人的衣襟。
云深身上的衣服偏偏长及脚踝,对襟处是一排精巧的蜻蜓盘扣,急切间根本解不开来。
摸索半晌,不得要领,夜半时分,塞北沁凉的空气让宁觉非打了个寒噤,到底清醒过来。撑起身,他看着眼前的人,一时有些发愣。
云深看着他,眼中仍然如水般荡漾。
宁觉非看了他一会儿,深深地叹了口气,索性又伏到他身上,两手再次紧紧抱住他,将脸埋入他的肩窝,闷闷地说:“对不起,我……发神经,你以后别理我。”
云深轻笑了笑,拉过被子来,盖在他光裸的背上,然后抱着他,轻声问:“我是谁?”
宁觉非清晰地答道:“云深。”
云深将脸颊往旁轻靠了靠,依在他的额旁,温柔地说:“很好,至少你不是把我当成了别人。”
宁觉非忽然有些不自在,将他圈抱得更紧了一些,脸却渐渐地烫了起来。半晌,他问道:“你不生我气吗?”
云深缓缓地将抱着他的手收紧了些,微笑道:“不生气。”
“真不生气?”
“真的。”云深看着他,说得非常肯定。
宁觉非呆了半晌,终于将心里的尴尬消除了些,这才溜下来,躺在云深身旁。
房里的那一盏油灯早已灭了,月光透过窗棂照射进来,室内显得十分安静。
两人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月光,都不说话。
半晌,云深忽然说:“我的手。”
宁觉非不解地看向他。
云深抽了一下被他压在身下的胳膊,笑道:“我的手,麻了。”
宁觉非这才察觉,赶紧挺了下腰,让他抽出手去。
看着云深慢慢地揉着手腕,宁觉非问道:“云深,你真的不生气吗?我这样……很不应该的……”
云深侧头看着他,忽然翻身,缓缓地压了过去。
宁觉非感觉到那白色的丝衣随着他的翻动又散发出来的青草香,看着他漾着笑意的脸渐渐地凑过来,心中既没有厌恶,也没有抗拒,只有亲切的温馨。
云深覆上他的身子,用手轻轻地抚过他的眉眼,随后吻了上去。
他学着宁觉非刚才的动作,吻过他微微颤动的眼睛、高挺的鼻梁,最后吻上轮廓分明的双唇。那唇干爽温软,带着馥郁的酒香和一丝丝茶香。
宁觉非一动也不敢动,有些发怔地感觉到他的舌尖轻轻地刷过自己的齿端,如蛇一般卷过自己的舌头,然后退了出去。
云深抬起头来看着他,笑吟吟地问道:“觉非,我这样对你,你生我气吗?”
宁觉非立刻摇头:“当然不。”
云深轻笑:“好了,现在咱们公平了,你心里是不是也好过一些了?”
宁觉非立刻点头。
云深看他忽然变成了一根老实的木头,不由得忍俊不禁,笑着拍了拍他:“嗯,好孩子,真乖,那就睡吧。”
这一句话便让那根老实的木头在瞬间变成了豹子。
宁觉非猛地发力,将云深掀了下去,随即将他摁在床上,狠狠地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谁是孩子?”
云深仰头,开朗地笑了起来:“好好好,是我错了,你不是孩子,是大人了。”这句话的说法却更像是在哄一个急切想长大的孩子。
宁觉非又好气又好笑,看他半晌,却又不能当真做什么,只好无奈地摇头,放开了他。
重新躺下来,他终于感觉到倦意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向他袭来,再也闹不动了,于是闭上了眼睛,轻声说道:“云深,我睡了。你也睡吧,明天你还要忙公务……”
“好。”云深将被子替他掖好,迟疑了一下,没有起身,就也睡了。
第二天,当宁觉非从沉睡中醒来,盯开眼睛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了。
屋里一片明亮,却空无一人。但宁觉非却老觉得鼻端仍然有一缕沁人心脾的青草香。
锦被裹着他赤裸的身体,显得特别舒服,令他想起了云深身上的丝衣贴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怔怔地发了半天呆,他才感觉到饥肠辘辘,于是翻身起床,穿衣梳洗,精神奕奕地走到了饭厅。
云深竟然也正在桌边坐下,见到他,不由得笑了起来:“睡好了吗?”
宁觉非很自然地点了点头:“嗯,睡得很好。”边说边走过去,坐到他对面。
丫鬟们已是含笑给他们端上了饭菜。
云深今天穿的却不是锦衣,是一袭白衣,上面画着粉色的梅花,十分淡雅。
两人吃着饭,云深很自然地替他夹了菜过来,说道:“这是我们云氏族人才带过来的,是新鲜的狍子肉,你尝尝。”
宁觉非便点头,送进嘴里仔细嚼着,随即笑道:“嗯,很不错。”
云深也尝了一口,不由得点了点头:“是不错,那你多吃点。”
“好。”宁觉非吃着,忽然想起来,问道。“我若代表云氏出赛,你们云氏一族同意了吗?族长怎么说?”
云深头也没抬地道:“我就是云氏的族长。我既已说了,他们自然同意。”
“咦?你是族长?”宁觉非大感意外。
“怎么?”云深这才抬起眼来看向他。
宁觉非眼珠一转,不由得失笑:“我一直以为……哈哈……我一直以为族长都是老头子,至少也是半老头儿,怎么会是个毛孩子?”
云深知他报复昨夜的事,便故意哼道:“是老头有什么好?你还要叫我叔叔。”
宁觉非嘻嘻笑道:“这倒没什么,敬老尊贤,一向是我们中……咳咳,一向是我们的美德。”说顺口了,他差点把“中华民族”说出来。
云深瞪了他一眼:“看看,呛了不是?好好吃饭。还有,你现在既然代表我们云氏一族,自然也就是我们的族人,凡事都要听族长的,现在族长告诉你,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参加比赛,勇夺金章。”
“是,是。”宁觉非做恭顺状,努力点头,过了一会儿,却又嬉皮笑脸起来。“那夺了金章有什么好处啊?”
云深倒又一本正经起来:“夺了金章,奖品是一块蓟北南方最好的草地。那里由于山势的原因,四季如春,草肥水美,是最好的牧场。每年谁夺了金章,他的族人就可以在那块草地上放牧一年,直到第二年的赛马节才交出来。”
“哦,那云氏族人都是游牧民?”
“不是。”云深摇了摇头。“我们的族人很少,男人大部分都在军中,妇女、孩子和老人生活在我们家族自己的封地。”
宁觉非一听,大惑不解:“那我争来干什么?又没什么用处,还不如让给别人。”
云深听了,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些丫鬟也都忍不住好笑。专门侍候云深笔墨的大丫鬟梅芯不由得笑道:“宁公子,你争来以后,如果自己不用,可以租给别的家族。”
“租?”宁觉非象是听天书一般,一头雾水。“怎么租啊?”
“譬如,你让给别人去放牧,等过年的时候,可以跟他要一百匹好马、三百头牛、一千只羊,其他野味什么的也可以酌情要一些,事先说好就成。”那梅芯巧笑倩兮,掰着手指,如数家珍。
宁觉非倒吸了口凉气:“要的那么狠啊?”
梅芯一愣,随即笑道:“这只是最普通的了,哪里狠了?那草场你是不知道,如果让别人拿去放牧,一年不知要多出多少骏马牛羊呢。我说的这些连他们收入的一成都不到。”
宁觉非听着,还是连连摇头。
云深看着他:“那如果是你,你要多少?”
宁觉非想了想:“我什么都不要,向所有牧民免费开放。我希望他们家家都有饭吃。”牧民的生活他是知道的,有很多人还是很苦的,特别是入冬,往往一场雪下来,草原上便会饿死数以万计的牛羊。
梅芯大感意外,忽然十分感动地望着他,半晌才说:“宁公子的心地真正好。”
云深望了他半晌,淡淡地说道:“觉非,其实依你的能力,你就是说想要整个天下,别人都不会认为你狂妄。可是你连多一物都不肯妄取,这才是最可贵的。别说你跟南楚人不一样,你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宁觉非被他一夸,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微笑着说:“我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好?我只是比较懒,不愿意多花脑筋,还有,反正你这有吃有住,我才有底气讲这些话,其实还是有些虚伪的。”
周围的大小丫鬟一听,无不掩嘴偷笑。
云深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懒?如果你也叫懒,我真还找不出比你更勤快的人了。”
“你每日天不亮就进宫,常常忙到晚上才回来,那方叫勤快,我算什么?”
“我那是没办法,职责在身,不得不为。你呢?没人逼你,没人要求你,可你仍然坚持每日一早便出去骑马跑步,风雨无阻,那才是真正的毅力。”
“我那……只是习惯而已,每天不动着就不舒服。”
“好习惯。”云深笑着。过了一会儿,他漫不经心地问:“你昨天,在哪儿喝了那么多酒啊?”
宁觉非随口答道:“鲜于氏那里。”
云深拿汤勺舀了一口汤尝了一下,对他说:“这鸳鸯羹不错,你尝尝。”
“好。”宁觉非便也去舀了一勺。
云深看着他,想了很久,眼里满是矛盾,过了半晌,他终于什么也没问,只是温和地道:“酒醉伤身,以后还是不要喝得太多了。草原上有陷阱,有狼,有说不清的什么毒蛇猛兽,也说不定会突来疾风骤雨,危险多得很。你昨夜喝得那样醉,若不是‘烈火’认得回家的路,你说不定就死在草原上了?”
26
赛马节的第一天上午是非常隆重的迎接大活佛的仪式。
一早,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活佛要来的道路两旁,手里捧着各式各样的献祭,神情十分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