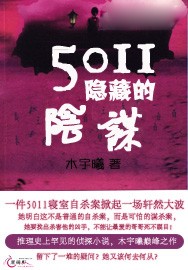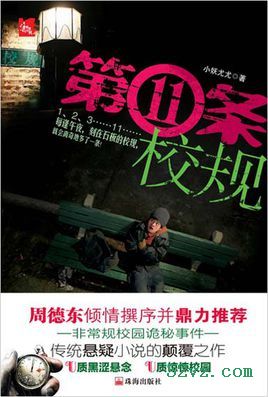115被禁止的基督 保罗·麦卡斯克-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芬尼斯的脸上没有一点反映,他还是看着斯奈特,嘴唇抿得紧紧的,然后放松一点,“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
“巴托夫斯基,”斯奈特的手轻轻一挥。
巴托夫斯基本来靠墙边站着,一步使跨出来,往斯奈特跟前一站,“到,长官?”
“我想请你把你的棍子拿出来,狠狠地朝芬尼斯先生的鼻梁上打。
芬尼斯往后缩了一步。威廉挺直身体,准备看下面要发生的事。
巴托夫斯基的脸色变得苍白。“什么?”他问道,那声音像是从干涩的喉咙深处发出来的,嘶哑而微弱。
“我让你把棍子拿出来——”
“我听见了,但先生——”巴托夫斯基好像找不到词儿。
“你不想动手,我知道,”斯奈特说,声音好像同情巴托夫斯基。“我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可芬尼斯先生不肯帮忙,说实在的,我也不相信光是谈话便能说服芬尼斯先生。
“不过……可是,为什么……必须我?”巴托夫斯基小心地试探。
斯奈特看着巴托夫斯基,好像他一下子变成的小孩,“你不是把犯人给放走了吗?这下得费好多事才能补救得过来呢,对不对?你不会希望在你的档案上写下‘无能失职’或者‘建议立即开除’之类的话吧,是吗?”
“不想,长官。”
“我想请奥康纳先生帮我同样的忙,”斯奈特好像是不经意地说道。
恰普曼的两手握在一起,绞着手指,“上尉,可是,我想……”
斯奈特扬起手,“典狱长,我对你想什么没有兴趣。巴托夫斯基,动手吧,你能做得到的。
巴托夫斯基慢慢地抽出他的警棍,那样子好像就要呕吐了。芬尼斯睁大了眼睛,一面往后退。旁边的卫兵死死地想按住他。威廉的眼睛盯着墨菲——他的样子要硕壮得多。尽管表面上看来他没有任何表示,威廉心眼相信应该是这个人参与了行动。
“怎么?”斯奈特不耐烦了。
巴托夫斯基双手握了棍子,像是举着垒球棒。
恰普曼说:“我要打报告……”
“你最好走开,巴托夫斯基,快点。”
这新来的看守穿着他妻子给熨过的干净衬衫,站在芬尼斯的对面,后者尽量表现出勇敢的样子,可仍在按住他的卫兵手下微微发抖。
“我没有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芬尼斯说,他的膝盖在发抖,腿也发软。
“废物,”斯奈特说,对巴托夫斯基挥手。
巴托夫斯基双手发颤,像投球手那样准备一掷,他扬起手臂。
“动手!”斯奈特下命令道。
威廉的手不自主地按到手枪套上。
巴托夫斯基闭上了眼睛,整个身体向后倾斜。
“不,”墨菲喊道,“住手,他可以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整个逃跑事件是我策划的,他只是个小棋子。”
斯奈特走到墨菲跟前,死死地盯着他看,眼睛一动不动地观察他的灰白而棱角分明的脸。“你是墨菲,”斯奈特说。
“对,我是墨菲,”这人用愤怒得有点沙哑的声调回答。
“又一个见过主的光的人吧,嗯?我敢肯定你在想念引擎的轰鸣和皮鞭的感觉吧。’嘶奈特轻轻地一笑。
墨菲挺直身体,下颌轻轻地一扬。这是一种非常细微的轻蔑。威廉记得他在吉米·卡格尼主演的一部电影中见过这一幕。
“那你说吧,逃走的那犯人的情况。”斯奈特的身体倚在桌子上,下命令道。
“你可以干脆下令枪毙我好了,”墨菲说,“我不怕死,我不会告诉你什么的。”
斯奈特微笑着说:“死亡可是你最不担心的事了,墨菲先生。”他对威廉点一下头。
威廉并不喜欢施行痛苦,无论是对人也好,还是对别的动物也好,甚至他不喜欢杀死昆虫——那怕称作蟑螂的。可这并不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他在学院里学习的时候,他们已经给了他彻底的训练,让他学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针对任何人,怎样通过准确地给身体施加疼痛而获得需要的情报。威廉可以不在乎做一些残酷的事,那种冷漠甚至使他的同学打寒颤。他可以像开关那些在一瞬间转换,前一刻还是迷人的和善的小伙子,转脸便成了不带一点情感刽子手。斯奈特称这些反叛者为蟑螂,但对于威廉,他们只是解剖刀下的一只只青蛙。对付他们只是件例行公事,如此而已,至少威廉一次次是这么说服自己的。
所以当斯奈特给他递了眼色之后,他便站起身来,一边小心翼翼地脱掉身上的夹克,好像是怕把它给弄皱了,然后卸掉斜挎在胁下的枪套,他对墨菲说:“真对不起,墨菲先生,这不是我们私人之间的事。
墨菲那天并没有被打死,尽管威廉可以肯定,墨菲自己是宁可死去的。
《被禁止的基督》作者:'美' 保罗·麦卡斯克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三章
山姆·约翰逊在一天之中遇见了两件足以改变自己生活的事件:一是他给炒了鱿鱼,再就是他在自己那简陋的单身住房的门后,捡到了一封偷偷塞进来的神秘的信件。
山姆猜那封信是在他离开校长的办公室后,穿过校园走回宿舍时,什么人给塞进来的。校长让他去是为了通知他,他已经被解雇了。山姆抬着一个纸箱,里面装他从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取回来的几本书和一些文具杂物。他进门时正好一脚踩在那封信上,要不是他的台历从纸箱上边滑落下来,他便不会注意到这封信。真那样,再等他看到这封信时,也就太晚了。
他心不在焉在把信塞进运动服的兜里,一边把纸箱放到地上。他把手掌按在自己后脑的一侧,稍微用劲揉着,然后把自己那粗糙的浅黄色的头发用手指往后梳过去,想让它们贴在头皮上。他在那张弹簧已经变形了的破旧沙发上坐下来,心里竭力把这一天的遭遇的事理一遍。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也给炒了就鱼。他上了十六年的学,又有七年的教学经历,可竟让这个神经质的校长,让这个他平时连正眼看一下都不屑的家伙给开了!
他竭力地回想那天的情景,由于凝神的缘故,他皱上眉头,结果他那双友好和善的蓝眼睛眯成了一道缝,眼睛周围的雀斑和鱼尾纹更清楚了。那是两个老朋友聚会的闲暇日子。其实山姆不该觉得惊奇的。岂不闻老话总是说:背叛你的人不会是你的敌人,而只能是朋友嘛。
三天以前他和比尔去钓鱼。那天他们不是校长和教授,他们是两个有同样爱好的朋友,站在过膝盖深的冰冷的河水里,一边抽烟,一边漫无目的的聊天。可他们并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呀!比尔一定把他的话,当时就记在心里了。
那天晚上,他们在帐篷外生了火,空气中满是柴烟和附近松树的气味,他们还煮了咖啡,山姆觉得惬意极了,尽情地享受朋友间的温馨气氛。也许他是说了不该讲的话。他承认自己有点倾向相信某种不可能的东西,倾向于考虑上帝,后者将他引向叫做耶稣基督的神秘。其实他说这些话时并没有很认真,或者说并没有多深刻。但他的确说了这些。
现在他才回想起来,当时,当时簧火照着的比尔的脸上有多不自在,那意思等于是说:“你干吗给我说这个,你干吗不闭上你的嘴呢?”
他回想起在比尔的办公室里,在好朋友让他滚蛋,给了他这样的打击以后,山姆居然还问他一句这是为了什么,想讨个说法。
但校长比尔只告诉他,校方经济上遇到了困难,而这是“时代的象征”。不过他们两人都心知肚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那次钓鱼,”山姆说道。
“与钓鱼无关,”校长比尔说,不过语调可不是很坚定,“不过,山姆,你倒是应该只在箱子上钻个洞研究它,而不必钻到里面去相信它。”
的确是时代的象征,山姆心想,他挺直了那足有六英尺高的身躯,怒不可遏地走出办公室,脚下踏得咚咚响。
现在他坐自己的屋里,四周都是乱七八糟的纸箱子,他觉得绝望了——他好像失恋了,不过抛弃他的是校方。这么些年来,只有书本才是山姆的女友、妻子和情妇,牵挂他心的只是一次次的考试,还有那些接学生的校车。只要他往黑板跟前一站,看见班上那些渴望听见他讲课的年轻人,只要他一开口讲起世界著名文学,他便感到满足,就像是行领受圣餐的仪式一样。山姆几乎没有别的需求。即令是新政府封杀了思想,那一张张脸都成了僵硬的死板的样子,他还是尽心尽意地教他的文学,结果他始终不渝钟情的爱人倒背弃了他。
他坐在那里想起了任何人在这种心景下会想起的事情。他本来会有更多的时间把他们写下来的,他本来应该多出去走走的,他本可以走出这种禁闭的环境的。他往后靠在沙发上,两手捂住自己的脸,疲倦现在停滞在他的肩上,他觉得眼睛发涩,甚至有点酸痛。我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
他往后伸直身体,把手探进衣兜。那封神秘的信在兜里飒飒地响。他在绝望中顺手把信掏出来,信封上没有字。他把它撕开。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那纸条说,“收拾保暖的衣物,今晚上10点到卡登大院11号来。”
山姆神情沮丧地笑了笑。打字机打的所有这些字下半部都有些模糊,他自己的系上就有这么一个老掉牙的打字机。是系里边的什么人在警告他?一个学生?或者是系上的那个秘书?他一个一个地回想,是谁呢?可对她,他并没有说过有关基督教的事呀。他倒是有好多次猜想,这女秘书会是一个基督徒吗。
他一下子泄了气,好像拔了汽门芯似的,瘫倒在沙发里。他得集中精力想一想。纸条上约定的时间不可能与他被炒鱿鱼有什么联系,那就太巧了。但总有什么人在想法帮助他,这是肯定的。不过,要这是一个圈套呢?他之开始相信耶稣才是不久前的事,像许多新信教的人一样,他在讨论信仰时,并不会太谨慎。
可是当局干吗要这么不怕麻烦,费这么多工夫来安设这个圈套呢?他们可以干脆上门来,随便找个借口就把自己带走啊。他们只要在警察总部问几个问题,便可以处置他了,他会像许多人一样的消失掉,他的朋友或者邻居有谁会敢去问呢?
时代的象征啊,真是不错。两个学期以前,他的班上也有这个一个学生,她在班上不明智地为基督教辩解了几句。其实那根本算上辩护,她只不过是说耶稣基督说的话,从哲学上看,有些还是有点道理的。他还记得,她说这番话的时候,那样子有些笨拙,但很自信。这是个很有点性格的女孩子。她的金黄色的头发从头上洒下来,遮住了半个脸。她说话时是一副实话实说的样子,就好像她压根儿不知道,在这个国家实话实说只会招来告密。他们需要的是猜疑和恐惧。
班长——他们在每个班上都暗地里指定了一个监视人——肯定把这事报上去了。两天之后山姆正在班上上课——他讲的是国家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那个女孩子冲进教室,眼睛惊恐地睁得很大,她大声呼救。两个警官跟在她后面冲进教室,当着全班人把她拖了出去。“救救我,救救我吧,”她尖锐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山姆觉得自己的良心一阵刺痛,倒不是因为她被抓走,而是因为他和这一班人都像痴呆的山羊似的看着。等走廊外的大门砰然响过后,他们又都回到自己原先的课上头来,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山姆以后再没有看见那个女孩子。时代的象征。
山姆还记得那天夜里的骚乱。他半夜给吵醒了,下面一楼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开始他还以为是那对夫妇在打架。然后他听到还有一个人的声音,再后来是第四个人的声音。说话的人始终保持那种单调的公式化的腔调,保安部队的人说话时都是这样的。那女的在尖叫,男的在抗议,而后是手铐的声音,桌子或什么家俱给碰翻了,玻璃破碎的声音……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满身是汗。他要做点什么。他的自由的本能告诉他,至少应该抗议,说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他想走到楼下过厅里对他们这样说,但他却没有迈步。他扯过毯子裹住身体静静地等待着,楼下的大门砰砰响过了,过厅里的脚步声小一些了,什么东西从地上拖过的声音也消失了,直到一切都静下来。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呢?也许是两个人?这不关山姆的事。一切恢复平静过后,山姆觉得不再有那种莫名的安全感。
马克斯一家住在山姆的隔壁,里昂和马格丽特两口子早就对山姆的说过,如果他不管好自己的那张嘴,总有一天要出事的。
“你们这些当教授的总是这样,”里昂先生挥着手里的汤勺说,那正好是楼下那对夫妇被带走的第二天晚上,他们请山姆一块吃晚饭,“你们想到什么不能憋在心里?总把全世界都当作你们的教室,那两口的事你也要遇上的,你要是不小心点。”
当时山姆有点尴尬,苦笑着,但却没有什么笑声,那晚上山姆和里昂都喝了不少,直到马格丽特催他回自己的屋去,一边把醉倒了的里昂拖到床上。
山姆接受基督以后,最先告诉里昂。里昂尽管是思想开明的人,但却不喜欢这档事,他没有表示赞成,而是皱紧眉头教训了山姆整一个钟头,反复说了他这个选择的危险性。虽然他也很清楚,大概这对山姆不会有什么作用,他改不了他的思想,或者说改变不了他的心。从那天以后,他们很少见面。偶然在走廊上碰上,是也只是点点头而已。这样要安全一些吧。
山姆在心里这么设想:要是自己消失了,里昂会不会说什么,会怎么想。又与上次那两口子消失后一样吗?国家又少了一个敌人?也许里昂什么都不会想,这样要安全一些吧。
他把纸条塞回信套里。也许,这是某个地下组织的人送来的?他对这人知道得很少,他只从报纸上看到过这些人的满怀激情的文章。有两个人,一个叫摩西,另一个叫以利亚,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