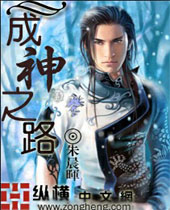科幻之路 (第四卷)作者:[美] 詹姆斯·冈恩-第8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初,奇异的城市,陌生的景象、声音和气息使他们兴致盎然;但是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他们的感官对新奇已感到厌倦,他们起先看到的异域风情现在已是那么令人扫兴。
他们缓缓地穿过由歪歪扭扭的遮篷和用木棍支撑的简陋的拱廊遮阴的市场时,多么盼望迎面能拂来一丝凉风。身穿白色长袍的阿拉伯人在尖声喊叫,眼睛一直盯住欧洲人。无法听懂阿拉伯人在说些什么。有的拉着小车,车上装着肮脏的杯子和壶——水?茶?柠檬汁?那没有什么区别。每个摊铺都有霍乱菌,每个乞丐拉住衣袖时都会传播伤寒。
希尔伯特的妻子有气没力地摇着扇子。她热得几乎快要受不住,即将瘫倒在地。希尔伯特绝望地东张西望,“大卫,”女佣克拉钦轻声说,在与希尔伯特有关系的女人中,她是弗劳·希尔伯特唯一能容忍的一个,“我们已走得够远了。”
“我知道,”他说,“但是我没见到什么——到处都没有——”
“那边有几位夫人和先生。我想那是个进餐的地方。让卡思和我留在这里,找一辆出租车。然后我们就回船去。”
希尔伯特举棋不定。他不忍心让两位无人保护的女人留在这个发疯似的异教徒们的市场中。他也看到他妻子的脸色是何等苍白,她的眼睑垂得多低,她是如何靠向克拉钦的肩膀的,“我来想办法,”他说。他们一起把弗劳·希尔伯格送进一家餐馆,餐馆里不见得凉多少,但是至少天花板上的电扇能送来令人陶醉的清风。希尔伯特向坐在桌旁的一个穿着讲究的男人作了自我介绍,那男人与他家妻子和四个孩子坐在一起。这位数学家用了三种语言才让那男人懂得他的意思。他说明了目前情况,那位先生及其夫人都安慰他,叫他不必担心。希尔伯特便跑出去找出租车。
他的身影翘就消失了。这里没有街道,没有欧洲人心且中的那种街道。建筑物之间盼窄小空间即是小巷,小巷通向小小的广场,便到了终端,另有一些小路弯弯绕绕地通往各个很难辨认的方向。希尔伯特回到一个露天市场,他原以为这就是他出发的地点,就开始寻找餐馆,可是他搞错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露天市场;城里可能有成百个这种市场。他骇怕起来。即使他找得到出租车,他怎么才能将车子引到他妻子和克拉钦等候的地方?
有人在用手拉他。希尔伯特想甩掉那只手。他朝那人望去,见到一张瘦弱、面颊深陷的男人的脸,此人身穿一件条纹长袍,头戴一顶蓝色编织帽。这个阿拉伯人重复说着几句话,可是希尔伯特不解其意。阿拉伯人握住他的手臂,半引半推地将希尔伯特带出人群。希尔伯特听凭他带路。他们走过两个市场,一个是锡制品市场,另一个是家禽屠宰清理市场。他们走上一条石块铺成的街道,随后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广场。广场的远端有一个巨大的、由许多塔楼浑成一体的清真寺,此寺全用粉红色石块砌成。希尔伯特的第一个印象是敬畏;这一清真寺像太姬陵建筑那等壮观。他的向导又将他拥出另一人群,或者说是他在前开路把他带出人群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希尔伯特很快就知道为什么了——广场中央已搭建了一个平台,平台上站着一个男人,手里握着只能是属于刽子手行刑用的利斧。希尔伯特一阵恶心。他的向导已将挡道人——推开,一直将希尔伯特带到平台的脚下,就让他在那里站定。他瞧见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蓄着胡须的老人引出一个姑娘。人群纷纷闪开让他们通过。姑娘看上去十分标致。希尔伯特的目光碰到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仿佛是羚羊的眼睛,”他记得他读到过波斯诗人奥玛开阳的这一描述——又向那未被简朴的衣服掩饰住的苗条身段投以一瞥。她登上台阶时,又径直地朝他瞟了一眼。希尔伯特觉得他的心一阵悸动,浑身猛地一颤。她立即偏转目光。
希尔伯特听到阿拉伯向导的厉声吆喝。这对数学家毫无用处。他在惊恐中看着杰汉跪下,刽子手举起他的办公武器。人群开始大声喧哗,希尔伯特才发现他的衣服已溅上殷红的斑点。这个阿拉伯人又朝他吆喝,将他的手臂抓得更紧,希尔伯特终于痛得叫了起来。这位阿拉伯人仍不松手。希尔伯特用另一只手掏出钱包。这个阿拉伯人笑了。希尔伯特看到在他的上方有几个男人正在把已被砍去头颅的躯体抬走。他付了一笔钱以后,这个阿拉伯人终于放了他。
或许在小巷里又过了一个钟点。杰汉已经退至小巷的最深处,蜷腿坐在一个潮湿的角落,头靠在凹凸不平的砖墙上。她在心底自语,如果她能睡着,夜就会过得更快;但是她不愿睡着,倘若瞌睡虫向她袭来,她定会与之抗争。要是她悄然入睡,醒来时已日高三竿,她的厄运连同她的机会全都早已消失,那又会怎么样?那弯蛾眉月,她唯一的伴侣,已弃她而去;她仰望星座中的一簇簇星星,这簇簇星星她非常熟识,可是现在星光已是那么耀眼,无法分辨出单个的星星。与那些认为反之即正确的人的观点比较,这显得何等格格不入。她叹着气;她不是善于思考的人,深思熟虑对她也不适宜。她判定,这些想法肯定不够深思熟虑;她实在困乏得精神恍惚。慢慢地她的头向前垂下。她的双臂交叉搁在膝盖上,头枕在臂弯处。大半夜已过去,街上一片寂静。离拂晓可能只有三个多小时了……
不久,施劳丁格的波力学证实与汉森伯格的矩阵力学相同。这不但是对这两个人的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整个量子物理学界的肯定。施劳丁格的过分简单的电子波纹图景终于被摒弃了,然而他的数学法则却没有受到诘难。杰汉记得,施劳丁格曾预言他可能将非采取那一步骤不可。
杰汉最后回到了哥廷根,也回到了汉森伯格的身边。他已“宽恕了她的任性”。他兴高采烈地欢迎她,一方面这是出自他对她的真情,另一方面因为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刚刚正式提出一个原则,后来被称之为汉森伯格不确定原则。这首次显示,公正的观察家不得不在次原子的粒子世界中起到至关紧要的、积极的作用。杰汉很快就领会了汉森伯格的概念。其他一些科学家们觉得汉森伯格是在对他们狭小的实验范围以及他们的观察质量吹毛求疵。其实他的概念比那更深刻。汉森伯格的意思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希望在同时了解一个电子的位置和能量。他永远摧毁了无偏见的观察家们的假设。
“观察就是捣乱,”汉森伯格说,“牛顿绝对不会喜欢这样的概念。”
“爱因斯坦就在现在还不喜欢这个概念,”杰汉说。
“我真希望他每次作出那种酸溜溜的‘上帝不与宇宙玩掷骰子游戏’。的话语时,我都作了记录。”
“那就是他对待‘概率波’的态度。电子的轨迹你不看就无法知道;但是一旦你看了,你就会改变信息。”
“所以上帝可能不跟宇宙玩掷骰子游戏,”汉森伯格说。他玩的是二十一点牌,如果他的衣袖里没有一张多余的王牌,他将制作一张——先制衣袖,再做王牌。他将普通的二十一点在手中颠来倒去,得出比统计学许可的更多点数。等一会儿,杰汉!我不是在亵渎神灵。我不是说上帝在欺诈。还是这么说吧,他发明了游戏规则,他继续在发明规则;这就使他远比可怜的物理学家和他们的肤浅的理解优越得多。我们如同村夫,正在观看某人的玩牌魔术,这个人可能是天才,或许是骗子。”
杰汉在沉思这一暗喻,“在索尔维会议上,玻尔介绍了他的互补性观点,即,在未发现前,电子是一种波的作用,后来波的作用消逝到一个点时,你就知道粒子在哪里。接下来就是一个粒子。爱因斯坦也不喜欢那种观点。”
“那是上帝的玩牌把戏,”汉森伯格说,耸了耸肩。
“嗯,崇高的古兰经说,‘他们对汝之暴饮和碰运气之游戏提出质疑。说:二者皆罪过,与人少裨益;然二者之过远胜于益。”
“那就忘了骰子和牌吧,”汉森伯格说,微微一笑,“安拉跟我们玩什么样的游戏会最合适?”
“物理,”杰汉说,汉森伯格哈哈笑了起来。
“汝可曾知悉安拉神圣地规定不准夺人之命?”
“知道,哦英明的人。”
“汝更知安拉对违背此法律者之罚规?”
“是的,我知道。”
“唔,我的女儿,告诉我们汝何以将此可怜之孩童杀死。”
杰汉将沾满鲜血的刀子扔在石块铺成的小巷上。刀子落地时发出沉闷的噪音,随即滚到尸体的一只脚旁,在那里停住不动。“我正在庆祝开斋节,”她说,“这男孩跟住我,我怕了。他做了一些下流的姿势,讲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话。我急忙跑开,可是他紧追不舍。他抓住我的双肩,把我逼在墙上。我想挣脱,却动弹不得。他见我害怕却哄笑不止,。还揍了我许多下。他把我拖过一条最窄的街道,那里很少有人来往;后来就把我拖至这个肮脏的地方。他告诉我,他要奸污我,随后就用污言秽语向我叙说如何如何。说时迟,那时快,我拔出父亲的短刀向他刺去。那晚我是在对他的企图和对我自己所干的事的惊恐不安中度过的,我已向安拉祈求宽恕。”
阿訇将一只颤动的手按在她的脸颊上,“安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宽恕。哦我的女儿,恕吾偕汝返归汝家,抚慰汝父母之不安。”
杰汉在阿訇的脚下跪倒,“万分感谢安拉,”她低声地说。
“赞美安拉,”阿訇、警官和卡迪齐声说。
十余年后,杰汉有了自己的女儿,她给她们讲这件事。但是在那些后期岁月中,孩子们听不进他们父母的告诫,因而杰汉和她丈夫的儿子和女儿们干了许多傻事。
杰汉等啊等,黎明已悄悄地照亮了小巷的路面。她昏昏欲睡又饥肠辘辘,但是她仍站了起来,蹒跚地走了几步。她的肌肉在抽搐,她感觉得出她的心好像在她耳朵里跳动。她把一只手撑在墙上,将身子稳住。她一步步地挪向巷口,悄悄地往外张望。看不到一个人。那男孩既不从左面也不从右边过来。杰汉一直等到有几个人露了面,他们是做新的一天的买卖的。她将刀子再次藏进衣袖,离开小巷。她赶回父亲的屋子。她母亲需要她帮助做早饭。
杰汉现在已四十挂零,她的黑发剪短了,戴着一副制作粗陋的眼镜,她的风韵已被操劳、饮食不良和睡眠不足侵蚀了。她身披一件实验室外衣,手提一块带有夹子的书写板,这些都是她的组成部分,正如她的头衔阿苏菲夫人教授、博士一样。这里已不再是哥廷根;这里是柏林,正在打一场已开始失败的战争。她仍与汉森伯格在一起。他一直在保护她,直到她自己的学术证书可以保护他们自己。那时,纳粹官员不得不给她一个“荣誉”雅利安人的地位,恰如他们对待那些他们需要与之合作的犹太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正因为长期来杰汉对汉森伯格忠心耿耿,才使她能长期留驻德国。她对战争几乎漠不关心;这些人不是她自己的人民,也不是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或美国人。她的唯一兴趣在于工作,在于改进物理学,在于永无休止地期待新的发展。
因而,德国的炸弹工程的控制权从德国军方手中转移至德意志研究委员会时,她很高兴。在众多首先要做的事情中,第一件事是在柏林的凯尔·威廉物理学院召开一个研究会议。会议将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事先不散发任何预先拟订的议题,这样外国代理人可能无法见到诸如“截面裂变”和“同位素浓缩”这类用语,这些用语会使他们猜测这些物理学家们的长远目标。
同时,德意志研究委员会决定同日为政府高级官员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意图是,在凯尔·威廉学院会上演讲的科学家们可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简要地概述他们的工作,使政治和军事要员们对原子武器的进展略有所知。在这些凡夫俗子们的报告以后,物理学家们可以自由组合,用更专业化的术语讨论同样的内容。
汉森伯格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是1942年,更难得到物质、政治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军队想把一切可用的研究资源投入火箭计划;他们争辩说,核子试验没有充分地显示成功的可能。汉森伯格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不是工程师;他可以设法告诉委员会,铀弹的研制必须放慢,必须有条不紊。理论上的每一进展必须经过慎重的检验,而每次实验均费时又费财。然而,德国军政要员关心的只是成果。
一天晚上,杰汉单独耽在德意志研究委员会的行政办公室里,打一份要求对他们的重要的同位素分离技术加以试验的报告。她见到桌上有两叠论文。一叠论文是物理学家们为戈林、希姆莱和其他德国政府部长们准备的一系列提要,这些人没有或只有少许科学背景知识。另一叠上是科学家会议的秘密议程——舒曼教授、博士的“用于制造武器的核物理学”;汉恩教授、博士的。一铀原子裂变”;汉森伯格的“铀裂变能生产的理论基础”,等等。每个参加技术讨论会的人在进入演讲厅后,都分发到一份程序单,并被要求在上面签名。
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杰汉思索了很长时间。她想起了凄惨的童年。她想到了她是怎么到达欧洲的,她后来开始熟悉的人们,她抵这里后的生活。她想到了德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与此同时,她却置身于科学的抽象的堡垒之中,与外部世界无涉。最后她又想到了这一新的德国会就铀炸弹干些什么。她确知她必须如何行事。
她只花了很少时间就把这些科学家们的提要藏进了手提箱。她捡起高度技术性的议程表,将它们——塞进已写好姓名地址的信封,准备送给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高级官吏。她已采取措施,决不让任何人接触这些介绍性的讨论摘要。杰汉可以很容易地料想到那些政治和军界领袖们会对这些难以理解的科学论文有何反应——简短而又礼貌地回答说那天他们将不在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