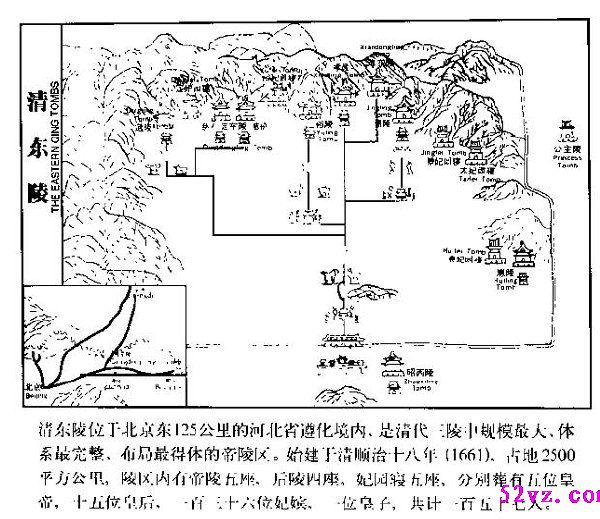06冰柱之谜 作者:[美] 金·斯坦利·鲁宾逊-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 有能力得到操纵费南多一X型级别飞船所需至少12人或更多人员的合作及他们事后的守口如瓶。
(4) 能够在2536至2548年间进入火星亚历山大城实物档案馆副馆319房14A23546—6室。
(5) 能够得到一辆23世纪中期的福特牌越野车,并有财力、物力于2547年10月开始的两周风暴期间将其半掩半露地埋在新休斯敦火山口外。
(6) 有能力从土星外环中隐秘地取走巨大冰块,这对于经常出入土星附近的人来说最为方便。
(7) 建造者必须拥有工具与设备以将冰块切割成巨碑形状,并不留任何痕迹地将它们竖立于冥王星地表……戴维达夫探险队即使存在也不可能拥有上述工具与设备。
(8) 达到上述所有条件必需的财富。
建造者的其他特性与巨碑外形有关:
(1) 对史前不列颠巨碑文化的了解。
(2) 与数字2248某种意味深长的联系。
短文发表后的两周我收到一封信。
埃德蒙·多雅先生 2609年9月18日510信箱路站
亲爱的多雅先生:
请屈尊至敝处一行以商讨与双方有关事务。路站至土星之往返费用将由我负担。如无不便,木卫I的帕达船长可立即携您离开路站;如您能少留1周至10天(切望您能体察此意)她将于新年元旦之前将您送回路站。
您诚挚的 卡罗琳·霍姆丝
土星人造卫星4号
从木卫I的观察屏幕上看土星就像个画有条纹的篮球,可以看见的月亮有五六个,都像白色的月牙。泰坦一眼就看得出来,因为它最大,并且它的大气层使得月牙尖上有点模糊。我看着它,心中的感觉只有一个看见老家的人才能体会到。
帕达船长是个安静的女人,在去土星的途中我很少见到她。这时她用手指着土星上方:“看到那个移动的白点吗?那就是她的卫星。我们将在环下与它相会。”
我注意到她把“她的”这个词说得特别重。我问道:“它有名字吗?”
“没有。只叫土星4号。”
帕达离开房间后我还留下来,把屏幕锁定在土星上。后来那些光环的刃状锋面变得越来越宽,整个画面越来越大,忙乱中我无法固定焦点。
我找到霍姆丝卫星的坐标,把屏幕转向它。
我们正在迅速向它接近。它很大:一个缓慢旋转的花托,一个直径一公里的轮子。朝向太阳的一面有窄窄的一个弯形,由于反射阳光而明亮异常,朝向我的另一侧表面则被土星照亮,呈幽幽的、发亮的黄色。扶手栏杆、闸口以及小小的台架使这弧形的金属制造物表面凹凹凸凸。在与港口相对一侧轮毂上突出一个小小的、古典设计的隙望台,它的望远镜似乎正瞄着土星。把轮毂与轮缘连起来的辐条看起来细得像铁丝。在花托本身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窗户,其中有些呈伸人真空的半球形。窗后的许多房间里都亮着灯,当我们绕着它旋转时我瞥见里面有红色和金黄的墙壁,明亮的褐色家具,大理石牛身像,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总体效果就像是一个19世纪的幻想,一个因偶然错误而投入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空间的探海球。
最大的那个窗户几乎是黑洞洞的……其后的房间只有昏暗朦胧的蓝光……窗后站着一个人,只看得见黑色的轮廓,似乎在注视着我们的到来。
帕达船长通过内部通讯把我叫到转换室去。我们就要开始对接了。
在穿过飞船时我感到对接时的震动,我停了一下,努力控制内心的激动。只不过是个老妇人,我想,只不过是个有钱的老妇人。但这些古老的形容词不起什么作用,当我飘进转换室时仍然感到惶恐不安。
闸门已经打开。
帕达船长在那儿。她和我握握手说:“很高兴您乘我的船。”然后挥手示意我往前走。
我觉得这番礼节有点怪,难道在我逗留期间木卫I的船员们都呆在船上不下来吗?
穿过对接通道,我就进入了霍姆丝的世界。
在我面前是一个男人,以立正姿势站着,穿着滚了金边的红色外套和长裤。他点点头。
“我的名字是查尔斯,多雅先生。欢迎光临土卫4号。我将把你引到你的房间,你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后卡罗琳就会接见你。”
他敏捷地迈开大步跳起,我急匆匆跟在后面。
我们顺着一个大厅降落,大厅墙壁是透明的,上面嵌着来自地球的贝壳,我又一次想到探海球。另一个大厅与这个垂直,使我们能够在轻微的重力下步行:我推测我们已进入了花托本身了。这个过道实际上一直呈弧形向上升起,走了不多远查尔斯就打开了大厅旁边的一个房门。
我们走进的这个房间的墙上挂着微带红色的波斯壁毯,天花板和地板是一种轻质木头。地板分成几级,每级都用宽阔的踏步分开来。
“这是你的房间,”查尔斯说,“那边那块控制板将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任何家具……衣柜,床,屏幕,书桌,椅子。这些机器人也会听你差遣。”他指了指两个装了椅子的箱子。
“谢谢你。”
查尔斯走了,这多少有点让我吃惊。但我以为他马上就会回来,于是走近墙上一块挂毯后面的控制板。
我按了一下床。地板上圆圆的一块滑开了,从下面升起一张圆形的床。我
穿过房间走近床边,重重地往下一躺,然后静待我的行李过来。
我想象我应该对霍姆丝说些什么。我开始明白我对她卫星的这次访问将完全按照她的意志进行,这使我有点害怕。
我又一次苦苦寻思她做这一切的目的、动机,就是想不出来。
冰柱和戴维达夫解释是个需要精心布置的骗局……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是对的,如果尼德兰德和“波赛风”号探险行动所发现的两者之间关系以及整个故事的细节都是霍姆丝编造的……所有最近发生的一切都使我更加深信我是对的……那么我马上就要遇到埃玛·韦尔日志的作者了。我将面对那个创造了曾使我幼小的心灵激动不已的故事的头脑……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与我会面的就是埃玛·韦尔。但细想一下,我现在所了解的与过去截然不同,这种见面真是给人一种奇怪的滋味!
我摇了摇头,对自己说(这句话我在研讨会上说了不止一次):“骗局总是叫人猜不透。”
我坐在床上等着……不止一次躺下来小睡一会儿……等了不知多少个小时。
房间里无法测度时间,控制板上也没有标有“时钟”的按钮。照理说,我可以通过内部通讯呼叫某人,可我又不知道呼叫谁。
最后我的肚子也饿了,心里也越来越烦躁,我忍不住出门来到走廊上,决定寻路回到对接台去,希望能在那儿看到查尔斯或别的什么人,虽说这种希望并没有多少根据。
我来到向上通往轮毂的那个过道,就是那个有着透明墙壁和成百上千贝壳的地方。
当我顺着一堵墙上的黄铜扶手往上攀时,看见一个弯弯曲曲的黑影随我一起往上爬。我以为这是自己的影子,但当我停下一会儿观看一个硕大的鹦鹉螺时,那形象仍在继续移动。
我吃了一惊,追上它然后把脸凑近玻璃。但玻璃很厚,上面又有些波纹,把对面墙上的影像缩成一个灰色的小圆块。
不过,对过的那个小圆块也停了下来。可能它也在凑近玻璃想看清我。它好像穿着深绿色的衣服……头发可能白了。
它又沿着原来方向移动起来,我也跟了上去,直到后来玻璃墙变成了柚木,那影像也就消逝了。
几乎与此影像消失的同时,在过道上我的下方“咔哒”响了一下。
我往下看去,看见一头的灰白头发,一个穿着深绿色紧身连衣裤的女人……当她往上攀时左手无名指上的银指环碰在扶手上发出了声响。
我有点不知所措,把脸贴近最后一部分玻璃墙,再看看这个我先前曾随之而上的影像。
那女人已攀到与我并排,我便扭过头去看她。因为似乎是目睹了一场奇怪的“心灵运输”,恐怕我的嘴巴还吃惊地半张着。而那个女人……就是卡罗琳·霍姆丝……看起来她也有点吃惊。
我猜我看起来不像个科学家……我从不理会自己的头发怎么样,再加上我这张脸,使我得了“路站狂人”的称号……所以别人吃惊的样子以前也见过一两次,倒并不怎么陌生。
但那只是一闪即过。
“你好。”她说,是音调和谐动听的女低音。
她个子很高,灰白的头发在脑后绾成一束,然后披散在背上。由于穿着紧身连衣裤,她显得很瘦。她的脸很美,但有点严厉:深深的皱纹,苍老,略带黝黑,脸颊和上唇依稀可见细细的绒毛。下颌和鼻子的线条异常鲜明,使她显得坚强。眼睛是棕色的。这是一张严酷的脸,上面标识着几个世纪的……谁知道是什么?……
一看到它我就知道面临什么对手了,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气。
“很高兴见到你,”她继续说,“你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
第一次试探。
“我很荣幸。”我说,一边想该再说些什么。这一刻我想象多少次了,现在却愚蠢地不知所措:“你好。”
她说:“我们去一个观察室,然后叫一点吃的怎么样?”
“好的。”
她松开扶手,领我顺过道飘下去,来到花托的主过道里。她的步子很大,每一步都露出了她的赤足。
我们离开过道,走下一层宽宽的旋转楼梯,进了一个大房间。
里面很暗,墙壁和天花板是木头的,地板则是透明的:这就是我来时看到的窗户之一了。土星在一侧像路灯泡一样发着光,而这就是我们惟一的光源,几张长沙发在房间中心摆成一个方形。
霍姆丝在一张沙发上坐下,身体前倾,往下看着土星。她那样子好像已经把我忘了。我在她对面的一张沙发上坐下,也往下看去。
我们正在一根土星轴的上方,从这个角度看土星和它的晕环是它的任何一个天然卫星都办不到的。标在土星(它的一半是黑暗,仅有环上反射过去的一点点亮光)上的纬度环带呈各种浅绿色和黄色,夹着一条条橘黄色。从上面看去它们是一个个完整的半圆;在赤道处的环带呈鲜艳的米黄,更高的纬度处转为黄色,在极地则是灰暗的绿色。
环绕着土星的便是那些光环,有好几十道,全都平滑、浑圆,好像是用圆规画的,其中只有三四道因绞在一起而不那么光滑。这些景象合在一起使我想起了一张镖靶:极点是靶心,光环则是最外围的靶圈。但要把土星想象为平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一半是黑暗的,而且它的阴影遮住了光环在它背后的那部分,这样它就显得像一个中心是形状怪异半球的镖靶。
我们地板窗的整个下方都是这种奇异景象,只有几颗明亮的星星在它周围发着光。可以看到七个土星的月亮,全都呈现规整的半圆形。我们像雕像一样坐在那里看着,同时感到眼前的景象在变化。土星投在光环上的阴影越来越短,所有月亮都变成了弯钩,光环倾倒成巨大的椭圆形;而这一切都很慢,非常慢,就像一种非人类的、大自然的舞蹈。
“永远如此,却又永远不同。”我说。
沉默良久,她说:“心灵的风景画。”
我开始感到笼罩着我们话音的深邃的沉寂。“地球上许多地方比这更美,可没有一处有如此庄严崇高。”
我知道你的地球之行,我心想。然后看着她的脸,心中又有所悟。几个世纪,都写在她脸上……我能说真对她有什么了解吗?她也可能到地球去了不止10次。
“有可能,”我说,“这是因为太空本身具有许多崇高的特性:广袤,单纯,神秘,还有那种恐惧……”
“这些只存在于心中,你必须记住这一点。但太空有很多东西使心灵想起它自己,这不假。”
我考虑了一下。“你真的认为如果没有我们,就没有土星的崇高吗?”
我想她不会回答。
沉默持续着,有一分钟或者更长。然后她说:“有谁会知道它?”
“所以关键是‘知道’二字。”我说。
她点点头。“知道就是崇高。”
于是我想,这是对的,我同意这一点。但……她往后一靠,目光对着我。“想吃点吗?”
“想。”
“阿拉斯加蜘蛛蟹?”
“可以。”
她转过身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叫了一声:“我们20分钟后吃饭。”
一个小小的托盘从她沙发上新出现的孔隙中滑了出来,上面装满了饼干和一块块乳酪。我愕然。另有一瓶酒和两只杯子都各自用单独的玻璃托盘送了出来。
她倒好酒,然后默默地喝着。
我们向前探过身子去观察土星。在这奇异的光照下……来自下面的昏暗的黄光……她的眼眶在阴影中显得很深,脸上的皱纹像是许多年的磨难深深刻进去的。
正餐是查尔斯端进来的,这使我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坐起来吃饭。
脚下的土星和它那无数的卫星仍在转动,像一盏气象宏伟的装饰派艺术灯。
饭后,查尔斯收走了碟子和餐具。
霍姆丝在沙发上挪动一下又朝下面的土星看去,全神贯注,那样子绝不允许打岔。
我一会儿看看霍姆丝,一会儿看看土星,也是一刻也没闲。但沉默持续越久,我就越觉得惶恐不安。
霍姆丝就这样沉思着,直到从地板窗已经差不多看不见了那带着光环的圆球,房间的光线也变成了阴暗的棕黑。这时她站起身说:“晚安。”
口气很友善,就好像我们在一起吃饭已经许多许多年了,一直是这个规矩……然后她就走出房间。
我站起身,心中一片茫然。我能说什么呢?
我又低下头看了很久星星,然后没费什么事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