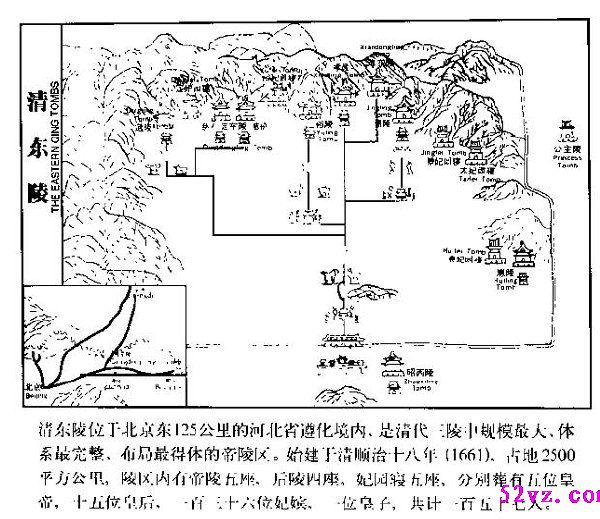06冰柱之谜 作者:[美] 金·斯坦利·鲁宾逊-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一个人走近我,从他的个头和步态我就认出他是琼斯。
“嘿,西奥费罗斯,”我说,“我们到了。”
他伸出手臂,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透过他的脸罩我看见他眼睛发亮,咧嘴笑着。他把我拉过去用力抱了抱,然后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
只剩下我一人和冰柱在一起。
我坐下来细细体味自己的感觉。我盼望来这儿盼了一辈子,现在终于来了。
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抓起一粒石子然后用力捏,可怎么也捏不动。是的,我真的到了,眼前再也不是全息图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与冰柱圈差不多紧密相连的是一个火山口,因年代久远已变得平缓,火山口沿已几乎全被掩埋。这样有些冰柱就立在火山口沿小小的圆包或高地上,造成非常美的效果:似乎每根冰柱都经过再三思考,然后“定位”在最恰当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冰柱圈却又明显地很不规则:冰柱都是四五根一组挤在一起,一眼就看出不在规则线条上,它们宽阔、平滑的柱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朝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刻了字的那根冰柱。
那些文字和2—2—4—8几个数字都深深地刻人冰面,太阳斜斜地照着,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想象巨碑的发现者塞恩·西亚逊是如何抬头仰望这怪异难懂的文字的。
行进,向更深处推进,引导人们向外。这是个很好的信条。
我又想起了父亲说的话:他们没有一人签上自己的名字,真令人不解。
说得真对,我想。如果戴维达夫探险队真的在此建碑纪念,他们为什么不说明这一点呢?在我看来他们必定会说明身份,这样于理才说得通。否则这些话不是故意要弄得神秘莫测,其目的不是明明白白地要让人猜不透吗?
我继续沿冰柱圈外沿走着,并用手轻轻触摸了一下一根三角形冰柱锋利的棱角,然后就来到了那根塌碑散落的碎冰块旁。每道裂口,每一片碎块的痕迹看起来都非常新鲜,有些锋利得像是碎裂的黑曜岩。
冰在绝对温标70度时异乎寻常地坚硬、易碎,被什么东西……这东西是流星,还是建筑工具,我们在今后几周内无疑将查个水落石出……一碰就碎成了几十片并向圈内方向倒去。
我看着一块半透明的冰(有点像霍姆丝家起伏不平的玻璃墙),觉得破裂应发生在不久之前。在这样的低温下冰的升华速度确实非常非常慢,但也不是全然没有;而我除了尖利的黑曜岩棱角外任何痕迹也看不出。我不知道那些科学家对此会有何说法。
然后我继续往前绕圈,隔一阵就蹦跳一阵,像障碍滑雪一样在冰柱构成的弧形中左绕右绕,那情景就好像我是在11岁生日时见到了这些巨碑。
每转到一个不同的方位,阳光和阴影的作用也会随着变化,这使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冰柱阵。
注意到这点以后每走一步我就看到一根不同的冰碑,于是我兴高采烈地绕着它们转呀转呀,直到最后筋疲力尽,再也蹦不起来,只好在塌碑旁一块齐腰高的冰块上坐下。
我真的见到了冰柱阵。
在随后的一两周里,各个小组都建立了各自的考察模式。
那些做冰分析的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登陆艇的实验室里。
胡德博士带领的小组正在分析测定做冰柱用的切割工具。
巴克恩·尼米特和他来自甘尼米德的那批人正沿着一条新的思路调查。他们察看塌碑的碎冰片,看看暴露面和向下被遮蔽的一面受微陨石击打的痕迹是否一样多。我觉得这种调查弄不好会有所发现。
但是最显眼、劲头最足的小组要算布林斯顿的发掘组了。布林斯顿表现了突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不过没有人对此感到意外。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领着他那批人到外面布下挖掘线路标志并迅即开始初步挖掘。他长时间呆在工地上,到各个壕沟去转,检查发掘出来的东西,和大家讨论,然后下达指令。他说话时很有信心。
“巨碑的结构将解释一切,”他说,但同时又警告我们不能期望立刻有所发现,“挖掘是一件慢活……即使在眼下比较单纯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必须小心翼翼,不要破坏所要寻找的证据。目前我们要寻找的就是上一次挖土、填土留下的痕迹,在表土中同样……”
他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他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要谈到。每次和他分手时我都几乎和他一样,对于他将解开这个谜团这一点深信不疑。
工作小组确定了一个共同的工作时间,他们称之为“一天”,在这段时间里工地上到处是忙碌的人影。这个时间一过,外面就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了。
我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可做,我明白这一点,同时感到很不舒服。由我发起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可动手的都是胜任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我无事可做,只能在旁边看看他们发现的东西。于是我很快养成了在下班后来看看冰柱的习惯。有少数人仍留在那里,或回去后又来看看,但他们很快都一动不动地沉思起来,所以我们一般都互不打扰。
在这些时间里,这些巨大的冰碑浸在无边无际的静寂中,在其中漫步,看到留下的那些器具,还有挖出的那么多壕沟、土堆,使人觉得这是一件刚做了一半的工程,一件巨人的工程,由于某种无法得知的理由而中途废弃……剩下来的只是一件伟大工程的骨架或雏形。
我一连几小时坐在圆圈的中心点,了解它在冥王星一天的不同时间里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现在在北半球正是春天……太阳所及之处最寒冷、最漫长的春天……太阳永远停在比地平线略高一点的地方。冥王星自转一周几乎要花上一个星期,同时太阳也就绕地平线转了一圈。但即使速度这样慢,只要我观察的时间长,我仍能看出光线、阴影的移动,使得每一刻冰柱阵都有所变化,就好像第一天我绕着它奔跑时所看到的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没动,移动的是冥王星本身。
在圆圈中心附近是尼德兰德探险队留下的纪念匾。他们把一大块角砾岩化的石头拖进火山口,把顶部削平然后盖上一块白金匾额。
为纪念2248年火星革命
并志其飞离太阳系之行
火星星际飞船协会
的成员们于
2248A·D·
稍后建此巨碑
其光辉业绩将万世永垂
谨立此匾,以表敬意
我呆呆地望着这怪东西,脑子里努力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很明显,那三条小行星采矿船确实在火星革命的前一年失踪了,这件事在很多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都有记载。所以有三条船失踪,这事不错。但它们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同时因为有关它们失踪的文件……其中一部分……在26世纪初就披露出来了,霍姆丝有可能发现了它们,从而决定把她的纪念碑解释为那些采矿船的遗留物……这样就编造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使对火星这个警察国家寡头统治的抵抗得到成功,并为一败涂地的叛乱挽回一点面子。这也就给了设置骗局的人比仅仅故弄玄虚更为深刻的动机……再者,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这种故事的。
这样就有了亚历山大城戴维达夫的档案,还有那辆在新休斯敦奇迹般出土的被掩埋的越野车。那份档案说来也很简单,在尼德兰德查找的前几年它并不在亚历山大的档案室里。他可以争辩说档案馆中资料的位置是变来变去的,可他再怎么说也于事无补。事实是这种变化也总有记载,而从官方记载看,该档案室并未被人搞乱过。简而言之,那份档案是塞进去的,是骗局的一部分。
这就强烈地暗示新休斯敦越野车也是骗局的一部分,预先放在那儿让考古学家们发现的。先前考察斯皮尔峡谷时在那条被掩埋的道路上并未发现任何金属物体;可后来一场暴风雪把考古学家们关在帐篷里,风雪过后在雪中发现的向北的印痕谁也无法解释。所以看来这辆车似乎是在风雪发生时故意放在那里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在火星上正发生着一场争论的风暴。埃玛·韦尔日志……骗局的一部分!……的日期追溯到23世纪中叶,正值革命发生之时……至少日志自身声称如此。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有人则就许多其他问题提出疑问:汽车本身的真实性,汽车表面的锈蚀程度,车内发现了一些较不重要的文件,将汽车暴露出来的塌方的可能性……越野车以及整个戴维达夫理论从每个可能想象得到的角度都受到了挑战,都找到了漏洞,而可怜的尼德兰德就在火星上跑来颠去,像故事里的那个荷兰男孩一样,把手指塞进洞里,企图以此修补那将要整个崩溃的大堤。戴维达夫探险是个虚构的故事。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火星星际飞船协会。这整个是个大骗局。
我愤愤地踢了一下那块匾。它安装得很牢固。我抓起两大把表土撒在上面。抓了几次后就成了一大堆,好像一大块平石板上用细石堆起来的圆锥形。
“愚蠢的想人非非的故事,”我嘟囔道,“利用我们喜欢听的心理……”
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在无人工作时间作此沉思的惟一一个常伴就是琼斯。他选择这时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这时巨碑才恢复了它孤寂的雄伟,它拖着阴影的庄严。不过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人在场时他工作起来不自在。
他也在工作,用的是一支距离测量枪,而且做得非常认真、仔细。他正在测量这些巨碑。如果我把内部通讯调到公共频道,就能听到他对自己念叨的一些数字,或哼的一些音乐片断。他安排好了让登陆艇在他工作时向他播送音乐;有时我也调到那个频道,一般播放的都是勃拉姆斯的交响乐。
有时他也会请求我的帮助。这时他就站在一块碑旁用测量枪对着我,我手中则拿着一面小镜子,镜子对着另一块碑。然后我们又换一块碑重做一遍。我看着火山口对过那小小的人影感到好笑。
“66乘以66,要一一量完可不容易,”我说,“你这到底是干什么?”
“数字,”他回答说,“建碑的人对数字非常讲究。我想仔细研究这些由巨碑产生的数字,看能不能找出那块碑。”
“哪块碑?”
“我觉得这种组合形式意在突出其中某一块碑。”
“啊。”
“因此我必须设法找出他们建碑用的度量单位。注意,它既不是米,也不是英尺,也不是英寸。很久以前,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汤姆的人发现北欧所有石碑用的都是同一种测量单位,他称之为石碑码。一石碑码大约有74厘米。”
他停下手上的活,我看见他枪口那微粒般的红点顺着我左边的巨碑转过去。“但是,除了我谁也没注意到北欧的这种石碑码和古西藏的度量单位长度几乎完全相等……”
“毫无疑问,还有埃及金字塔的度量单位。但难道这不是因为它们都是早期文明通常使用的从肘关节至手指的长度吗?”
“可能吧,可能吧。但既然这里的扁平圈结构是美国巨石阵常用的模式之一,我想最好还是查核一下。”
“结果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
我笑了起来。“你到‘雪花’号的计算机上几秒钟就弄清了。”
“是吗?”
“我很高兴你能和我们一起来,琼斯,我真的很高兴。”
他也笑出了声。“你喜欢这里有人比你还疯狂。但是等一等。即使在我进行这些新的测量之前,冰柱群的数字关系也一直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如果从塌碑开始逆时针方向按素数计算,那么每块碑的宽度都增加1.234倍?还有,每4块连在一起的碑长之和要么是95.4米,要么是101米;还有,每块碑的长度除以宽度所得商是一个素数……”
“这些都是谁说的?”
“是我说的。你肯定没有读过我写的《冰柱的数学与玄学》这本书吧?”
“看来我是把它给漏了。”
“那是我写得最好的书之一。知道你有多少不懂的东西了吧?”
这样很快就过了几个星期。
虽然布林斯顿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他脸上却开始有了些微焦虑的神情。看来当时每竖一块碑都曾挖了一个大圆坑……然后把冰柱立在坑底,坑底无一例外都是基岩,最后又把坑填平。此外他们惟一的发现便是那六根大碑并不是一碑一坑。可能因为它们挤得太紧,所以六根只挖了一个大坑,形状仍然是圆的。布林斯顿小组量了一下这个大坑的周长,发现它相当九根冰柱的周长。
“可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无恼怒地坦白说。
就是布林斯顿公布这条消息的同一天,琼斯拉我到工地去。他显得很激动,可就是不告诉我为什么。
工作时间已过,只有我们两人在外面。我们穿过环形山来到极点,从那儿观察整个冰柱群。
葛罗斯金博士第一次来这里勘察时为了方便曾在旋转的轴心上竖了一根短短的金属杆,比肩膀略低一点,现在仍然立在那儿。
太阳照在巨碑的另一侧,使它们显得比通常更为模糊……只是回光中淡淡的影子,笼罩一切黑暗中的一片片昏暗的光。我感到脚下的沙砾冷冰冰的。
“我们现在正像陀螺一样转着,”琼斯说,“感觉到了吗?”
我轻轻一笑。不过再坐一会儿,我突然好像可以看到冥王星是一个旋转的小球,顶部钉着几根冰签,旋转轴上则坐着两个小得像蚂蚁的小动物。
我移动一下,太阳也就隐到了一块巨碑的后面。我感到那种古老的恐惧……日蚀,太阳的死亡。
静静地坐了很久以后,琼斯从他保护服的腿兜里掏出测距枪,将它打开,他把它瞄向冰柱,在第3根,即最高的那根上,出现了一个红点,比阳光要亮一些。琼斯移动着红点在这根冰柱上画个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