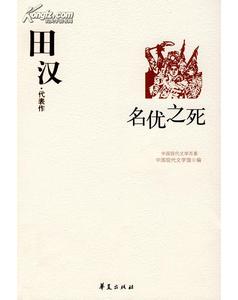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徐贵祥:历史的天空 不全-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十一章(一)
徐贵祥
一个露水挂枝的清晨,救护所的院子里来了很多人,急匆匆地搬着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像是在搬家。
韩秋云醒了,眼皮动了几下,没有睁开。她听见外屋里那个半洋半土的医生正在跟什么人说话。前面说了些什么她听得隐约,再往后说,她就听得分明了,是高队长高秋江来了。 在凹凸山,这个名叫乔治冯的医生是一个特殊人物,外科方面的精湛技术首屈一指,他曾经
给刘汉英和刘汉英的上峰作过手术,作得长官们感恩戴德。乔治冯到凹凸山来参加抗战完全是凭他自己的兴趣。只有乔治冯一个人可以不喊刘汉英“旅座”或者“长官”,而是大大咧咧地称呼其为“刘先生”。乔治冯同刘先生有约在先,不仅可以不穿军服,而且来去自由。要是弄得他不快活,他谁的账也不买,拍拍屁股就走人。而刘汉英极其不希望这个救命的菩萨轻易离去,想了很多办法,并且让左文录挑选漂亮的姑娘安在乔治冯的身边供职,试图以美女牢固地圈住他。但是乔治冯不吃这一套,乔治冯甚至对于这些女人来从军都很反感。
女人们都说,比起别的男人,乔治冯最懂得怜香惜玉,多次向刘先生提出建议,要解除对于战地女子服务队的野战训练,而集中力量让她们进行医务护理方面的练习。乔治冯的观点是,上帝造就了女人,是让她们做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女人本来是不应该操枪弄炮的,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女人所从事的职业应该是教育、医疗、艺术和服务,这些才是女人的角色。打仗是男人的事,在文明社会,男人打球、打猎、打仗。像战争这样极其需要意志和胆量的暴力行动,确实应该由男人来承担。战争是男人的舞台,女人的舞台在战争的幕后。
战争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使男人更加男人,而使女人更加女人。
但是这些建议却被刘汉英含糊了。作为凹凸山地区国军最高长官,刘汉英自然也有他的道理。
韩秋云认为乔治冯是一个好人。 在这个清晨,韩秋云听见医生说:“真是不可思议,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嘛,你们让她去战斗去流血,别说她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会打,心理也承受不了嘛。”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平静地说:“是不可思议。大夫,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韩秋云听见那位满肚子怪里怪气学问的好人医生说:“高女士,我听说你是一个巾帼英雄,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该死的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请你真实地告诉我,你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高秋江笑了:“我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大夫你所描绘的,去搞教育或者医疗,或者干脆在家当一个好妻子。”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高秋江却笑出了声:“你不相信是吧,你听别人说什么了,说我是魔鬼吗?你看我像个魔鬼吗?大夫你是个医学家,站在医学的角度,你看我和别的女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嘛。”
乔治冯说:“当然,我并不是说女人就不能打仗。战争爆发后,英、美、法、俄许多国家的妇女都拿起武器,同法西斯蒂进行战斗。当然,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战争是个魔鬼,它使我们美丽的女性不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性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女人应该远离战争。”
“我相信你的理想是美好的,可是这种理想离我们是何等的遥远啊。”
韩秋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哦高队长,那是多么严厉的人啊。可是今天,在韩秋云听来,高队长的话语却是那样的温柔和亲切。她又听见高秋江说:“我能看看我的部下吗?”
“不行,她的病还没有痊愈,我不能这样把她交给你们。”医生的话很坚决。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来领她走的,我只是来看看她。”
“那也不行。她的病情很特殊,你会使她受到刺激的。”
没有声音了,医生的话显然触动了高秋江,她沉默了。过了很长时间,高秋江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道:“大夫,能告诉我她得的是什么病么?”
“高女士,这位姑娘患的是帕尔尼森氏幻想综合症,这种病多是惊吓致厥后遗症,在欧洲很常见,在亚热带地区目前尚属罕见。该症特征是时断时续,而且多数为外部环境诱发。这位姑娘豆蔻年华,正处在青春期,身体十分敏感,容易诱发复症的有十几种花粉,一旦她嗅上那些花粉,她体内的一些细胞……我说的是情欲,你懂吗?”乔治冯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听,多少还夹带着一些沪腔,满有味道。
“我明白了……她是不该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在目前她的病情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你还是不见的好。”
“可是医生,我是她的队长啊。而且,也许……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韩秋云非常奇怪高秋江会用这样的语调说话,她突然觉得高队长变了,变得有些陌生了。
果然,医生也察觉到了这一点,问道:“高女士,你是怎么啦?你的话好……伤感。我能帮助你吗?”
韩秋云听见高秋江笑了,是微笑。“谢谢,我没什么,我不过是要离开这里了。”
“能告诉我你将去什么地方吗?”
“不能。我只能告诉你,你给女人分配的角色真好。我是多么想像你描绘的那样,当一个母亲、妻子和女儿啊。可是,看来我是做不到了。这包东西请你转交给她,无论身处何地,我都会为她祝福的。” 说完这番话,高秋江走了。
韩秋云从窗前看见了高秋江远去的身影,这才发现,高队长今天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袭湖绿底黑碎花的旗袍。穿旗袍的高秋江与往日的高队长判若两人,那副修长姣好的身躯在明媚的丽日下,益发显得丰采旖旎。
第十一章(二)
徐贵祥
高秋江就是穿着这样一身湖绿色的旗袍离开舒霍埠的。 旗袍的面料是享有盛誉的梅山丝绸,质地细腻高贵,手感柔润如水,且款式雅致,做工精细,从颜色到缀绣,再到线条,都搭配得恰到好处,落落大方。如此成色的上乘之品,由一个身材匀称曲线流畅的女人来享用,彼此都算找到了知己。穿着这身旗袍,移动脚步,雪白如凝脂的肌肤,便同光洁细密的衣面摩挲出丝丝缕缕的温馨,还有那种若隐若现时真时幻的酥痒的惬意。一副被军装笼罩了很长时间的身躯终于又焕发出本来的美丽,甚至在服饰淡雅的清香浸润之后,变得更加新鲜和
美丽了。旗袍因了女人而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高贵和优良,女人则因了旗袍而得以最大程度地闪耀出自己性别的光辉。 美好的感觉和美好的体验以及美好的梦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同阳光一样照射着高秋江的心灵,直到祥和绸庄的杜老板将一个沉甸甸的盒子交到她手上,她才幡然记起已经被淡忘的使命。
盒子是墨绿色的,四方锦绣绵软,上顶有“文房四宝”四个古色古香的正楷,笔锋遒劲有力,骨架协调血肉丰满。打开盒子,却是一柄亮锃锃的勃朗宁牌袖珍手枪,静静地卧在雪白的丝棉衬垫上。
这已经是高秋江到达洛安州的第三天了。她现在的身份是祥和绸庄杜老板的侄女,是从石家庄到江淮来做丝绸生意的。从这一天起,高秋江就频繁出现在洛安州各个角落的绸庄布店里了。尽管她本来的特长同做生意这个行当相去甚远,但是凭借女人与生俱来的对于服饰的兴趣,在杜老板的简明的点拨下,她还是很快地掌握了行情,并且能够娴熟地掂量各种绸缎的质地和价码。
自然,这些活动都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铺垫,是为她熟悉洛安州的街巷和接近打击的目标所做的战前准备。
任务是绝密的,在凹凸山,除了刘汉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包括专门从事秘密活动的吉哈天和她以心相托的莫干山。惟其绝密,从而更加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就连刘汉英交代任务,也选择了一个极其隐秘的方式。从时间上,是冬天明确的任务,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在暗中进行了几个月,这也就决定了此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对于完成这项使命,高秋江并无多少担心。无非就是刺杀一个名叫川岛长崎的日军医官。
刘汉英跟高秋江交底说,川岛长崎正在研制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细菌武器,一旦研制成功,将对凹凸山的抗战局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高秋江却对刘汉英的这种说法心存疑窦。刘汉英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他的队伍还没有进入凹凸山之前,高秋江是在蒋文肇集团军的情报处供职的,那时候她的手上就掌握了川岛长崎的资料。川岛长崎是一个以医官身份作掩护的日军高级谍报人员,他曾经收治了一个负伤被俘的国军副军长,从这位副军长的嘴里,挖出了不少情报,有些甚至涉及到高层苟合的铁幕。蒋文肇以前曾经派了两个行动小组潜进洛安州,欲除川岛长崎,但是都因对方防范严密而未能下手。
事隔两年,刘汉英又十分慎重地部署了刺杀行动,并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色彩。无独有偶,在高秋江同莫干山雪地幽会那天,在莫干山的一再追问下,高秋江含糊其辞地暗示莫干山,她不久可能是要到洛安州重建被日军破坏的谍报机关,莫干山当时也曾咬牙切齿地嘱托她,如果机会恰当,就干掉日军医官川岛长崎。莫干山没有明说他对川岛长崎的仇恨,但是莫干山告诉她,共产党那边也对川岛长崎很头痛,江北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都在寻机除掉这个魔鬼。这个魔鬼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如此一来,这次行动的背景就空前的复杂起来。高秋江对于对方的价值作过如下判断:一,川岛长崎掌握了国军高级将领与武汉汪伪政权的微妙联系,尤其是蒋文肇下属人员与汉奸姚葫芦的暗中交易。二,东条山事变之后,刘汉英的部队曾经故意“丢失”一份情报,向川岛长崎的特务机关暴露了原七十九军余部的位置,企图借刀杀人。但是日军为了更为深远的战略,并没有对那一百六十二人下手,而是让他们继续像钉子一样插在刘汉英的心脏上。
而且这份“丢失”的文件也被川岛长崎作为白纸黑字锁在了自己的药械箱子里。三,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在弹尽粮绝并且无路可走的时候,川岛长崎曾经指示进攻日军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双方并且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消灭和制约刘汉英的默契。所以莫干山也有除掉川岛长崎的动机。
四,川岛长崎在掌握了国共两方几路人马的重要隐秘之后,不急于兜售,而是静观默察待价而沽。如今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出现重要的转机,川岛长崎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已经向他的买主们开价了,于是便引来了来自几个方向的杀身之祸。
第十一章(三)
徐贵祥
年初的那个雪天里,就在高秋江即将彻底绝望之际,莫干山的最终出现,冰释了她情感深处的所有痛楚。她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溢满了温暖的春风,她记得她是飞奔着迎上去的,她在扑进莫干山的怀里的时候两个人都滑倒了,然后就那么纠缠着拉扯着拥抱着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莫干山的住所,就在那盆通红的火塘旁边,她畅快淋漓地大哭了一场。她像是一个失去家园的孤儿,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找到了惟一的亲人,于是便有了江河一般滔滔不绝的倾诉。她委实经受了太多的感情磨难,她的心里盛装着太多的幽怨,她的委屈可以车载
斗量。当年,他们尽管稚嫩却也真实,他们在爱情的蛊惑下疏忽了传统礼教的巨大的摧毁力。姑且不论他们的“表姑”和“表侄”的亲戚关系在彰德府平原上不容他们“有伤风化,有悖人伦”,即使没有这层关系,高家在彰德府北的首富实力和莫家的小农地位,也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悬殊。他们的情爱注定了是在喜剧中开幕而在悲剧中结束。
七年前雨地返乡之后半年,高家老太爷终于察觉了这对青年的“不轨行为”,颤抖着银白的胡须郑重宣布,从此禁止高秋江大嫂娘家的任何人再到高府,“孽障”莫干山倘若再对小姐心存妄想,势必要打断他的贱腿。小姐倘若不守闺训,再做出丢人现眼的事情,就施行家法,交族人协议处死。 于是乎,这对男女年轻的信念被家族的高压迅速地摧毁了。莫干山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到河北武培梅军队当兵吃粮去了,并且由于骁勇善战重义轻死而屡建战功,很快升为连长。 高秋江在此后的两年里,则以死相拼先后拒绝了若干豪门的求亲,并于日军攻打姑子关的那年秋天,跟随一群流亡学生,投奔了蒋文肇的队伍。东条山事变发生之后,这对旧时恋人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相遇,可是此时莫干山已经成亲,并且将高家的所作所为迁怒于高小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就是冷嘲热讽,甚至故意将他的漂亮妻子接到军营,对高小姐施行羞辱。
高秋江的一把伤心泪,全都流进了肚子里。心灰如死,恨从天来。在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她渐渐地变得穷凶极恶起来。她酗过酒,打过人,甚至吸了一段时间白面。可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能排遣内心与日俱增的苦痛。突然有一天,她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突围的路径,那就是——射击。
哦,射击,这当真是一件令人眩晕的事情。
当她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指,触到冰凉而圆滑的扳机的时候,当那一团骤然而至的火光在眼前炸开的时候,当一个精巧的金属物体按照自己的意志以超凡的速度飞向某个假想的敌人时,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刹那间变得充实而饱满。那种愉悦和快感是难以诉说的。
是青干班那位姓吉的教官独具慧眼,最早发现了这个女子在射击方面的激情和天赋。从此,一柄玲珑的七音小手枪就再也没有离开她的腰际。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截住了莫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