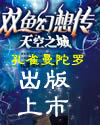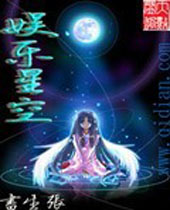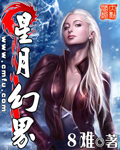索拉利斯星-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沙那罕探险队的三艘飞船到达索拉利斯后,将一艘留在轨道上,继续绕行星飞行,另外两艘在稍作尝试后,双双着陆在一个方圆 600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探险队在行星上停留了18个月,除一次设备故障引起的不幸事件外,整个探险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伴随探险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科学界的论战又起,分成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焦点集中在对海洋性质的判断上。当时,基于考察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即索拉利斯的海洋是一种有机态物质,是双方都认同的——当然,还不敢说它已经具有生命。但是,以生物学家为首的一派认为:那海洋仅仅是一种原生态物质——一个巨型原生质,一个液态细胞,是“生命前物态”,它独特怪异,硕大正比,以一种胶体膜的形态包围着整个星球,有的地方厚达数英里;而以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为首的另一派则声称:行星海洋必定是有机组织,一种经过非凡进化的有机物形式。其结构组织异常复杂,甚至可能超过陆上生命,因为它已经有能耐对行星施加强大作用,左右其运行轨道。这个推断有一定说服力,至少还没有人找到别的证据,可以对海洋的异常表现做出他种解释。更令人鼓舞的是,天体物理学家已经发现,原生态海洋的变动与当地引力的实测数据之间,存在这样一种联系,即后者会根据海洋的“变形”而发生相应改变。
结果,正是这些物理学家,而不是生物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学说——“原生质机能说”。根据这一学说,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物态,它也许没有我们所说的生命,却具有生命的机能,能对外界施加有目的的作用,而且是天文学尺度上的作用——这最后一点尤其值得强调。 此次大论战引起了广泛反响,并迅速波及科学界权威,过去八十多年里未遇挑战的加莫夫·沙普里学说,第一次动摇了。
也有部分学者继续坚持加莫夫·沙普里学说,他们的论点大致如下:这个海洋既非“超生命物态”,也非“生命前物态”,而是一种地质物态——当然,这种物态极端罕见——它具有一种独特能力,无论所受引力如何变化,它都能稳定索拉利斯的运行轨道。勒夏特列原理①也被搬来支持这种论点。
【① 勒夏特列原理是说任何稳定化学平衡系统随外力的影响,无论整体地还是仅仅部分地导致其温度或压缩度(压强、浓度、单位体积的分子数)发生改变,若它们单独发生的话,系统将只作内在的纠正,使温度或压缩度发生变化,该变化与外力引起的改变是相反的。】
为了挑战这种保守态度,形形色色的假说被提了出来,其中最为煞费苦心的莫过于西维托·维塔假说,该假说声称:索拉利斯星上的海洋生命是物质辩证发展的产物。它的早期形态是一种溶液,由一些反应缓慢的化学元素构成。由于轨道变化威胁到它的生存,迫于这种环境外力的强大作用,它的自然演化过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跳过了所有陆上生命必经的各个进化阶段——单细胞与多细胞阶段,植物与动物阶段,以及神经与大脑系统发育阶段,一下跳到了“自平衡海洋生命”阶段。换句话说,普通陆上生命是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为此经过亿万年时间的进化,最后达到物种进化的顶峰——灵智生命;而索拉利斯海洋生命却不这样,它一步登天,反倒主宰了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这个假说富有创见,然而它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即那被其称为“自平衡海洋生命”的胶体膜以何种手段稳定行星的轨道。尽管人类发明引力发生器已近一个世纪,获得人造磁场和人造引力场已成易事,但谁也无法猜想,索托利斯那无形无状的黏稠胶体如何运用复杂的核反应技术,驾御超高温度,取得引力发生器所能产生的巨大效应。当时的各家报纸,充满了关于“索拉利斯之谜”的各种轰动新闻,加油添醋,离奇怪异,耸人听闻,激起外行人的好奇和科学家的愤怒。有一个记者甚至突发奇想,走得最远。他声称,索拉利斯海洋至少也算地球动物电鳗的远亲。
在索拉利斯学的研究中,情况总是这样,新学说新理论不断推出,每一种似乎都能成功解释索拉利斯的矛盾现象,但结果却无非是以一个谜团代替另一个谜团,问题始终末获解决,甚至被搅得更为复杂。
观测结果显示,索拉利斯海洋在改变行星引力时,所采用的原理并不同于我们的引力发生器。这在我们人类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但它就是成功地做到了。它周期性地改变行星的引力,直接控制住行星的运转轨道。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实测数据表明,在索拉利斯的同一条子午线上,不同地点的时间竟然有差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索拉利斯海洋不仅“知道”爱因斯坦·博埃维亚理论,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发挥此理论,利用其尚不为人类所知的某些推论。
随着这一假说的公开发表,整个科学界陷入本世纪一场最具颠覆性的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之中。许多被人们普遍接受、奉为神祗的科学理论被颠覆了,专业文献充斥着离经叛道、荒谬绝伦的论文,“灵性海洋”、“调节引力的胶体”等概念处于论战的旋涡中心,成为时髦用语,炙手可热。
这一切发生在我出生前多年,到我读书时,关于索拉利斯的研究已进一步深入,观测数据更为翔实,人们已经大致认同一点,即索拉利斯存在生命。哪怕它仅有一个居民。
我继续浏览休斯和欧格尔的著作《索拉利斯史·卷二》。此书内容深奥独到,系统严谨,而又不失轻松幽默。例如,它给索拉利斯海洋生命的动物学分类就很有意思: 目——多孔目; 纲——合胞纲; 种——变形种。 有关巨型物种的传说,我们听说过的(可谁也没见过),何止千万,但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只有索拉利斯这一个——它重约7000亿吨。
我继续埋头在书页间。那些五颜六色的插图、生动如画的图表、分析透彻的总结和色彩艳丽的光谱图在手指之间轻快地飞过,它们不仅详细展示了索拉利斯海洋生命变形的化学反应情况,而且说明了变形的方式与周期。接下来,书的内容转入严密的数学推理,将结论建立在坚实的数学论证基础之上。现在是四点钟,索拉利斯星短暂的夜晚来临了。在基地的钢铁外壳下数百码的某个地方,躺着那个变形巨物,夜色已将它掩蔽。关于它,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已经了解很多,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确信索拉利斯海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甚至是灵性动物。我把厚重的大书放回书架,又取下旁边的一本,继续看。这一本分两部分,前一部分简述人类试图与索拉利斯海洋建立联系的种种尝试。那时我己上学,那些尝试曾经是孩子们日常谈论的话题,其中不乏趣事、笑料和俏皮话。总之,对这个问题的求索启迪了人类的思考,正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催生了科学启蒙运动一样。书的第二部分近1500页,专门罗列有关索拉利斯学的文献书目,数目之巨,收罗拢来,只怕这间舱房也堆放不下。
最初,人类采用特制的电子设备,试图与海洋建立联系。在每一次尝试中,海洋本身扮演着一个活跃的角色,它重构我们的电子设备,使其功能发生改变。但它其体是如何操作的,尚不为人知。准确地说,海洋的“参与”活动是这样的:它修改了我们放置在水下的电子仪器的某些元件,结果,那些仪器的放电频率受到干扰,只记录到大量奇怪的信号。那些信号似乎暗示,水下有异常活动,但并不确切。总之,与海洋联系沟通的目的并未达到。令人费解的是,海洋发出的那些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时的刺激反应,仰或有规律的电磁脉冲?那脉冲与海洋正在建造的某些巨物是否有关联?而它们又正好位于探测区域的对跖地①?或者,电子仪器所记录的,正是海洋万古奥秘的隐晦显灵?它在向人类昭示自己最深层的构造与活动?这些疑难,有谁能破译解读呢?对人类发出的每一次沟通信号,海洋的反应都不一样:有时强烈,反馈信号几乎让接收仪器爆炸;有时无动于衷,完全沉默;每一种现象决不重复出现,要捕捉相同信号根本不可能。总之,情况似乎总是这样:反馈信息不断增加,专家们已经走到破解的边界,但最终却未能完全破解。这神秘的海洋,人类功能无边的电子计算机尚不能与其斗法,莫非它真有什么怪招,超乎人类的智能么?
【① 星球上两个处于正相对位置地点或地区.比如地球上的北京和智利首都布宜诺斯艾刺斯就是对跖地。】
当然,零星的成果还是有的。作为电磁脉冲和引力的发生源极,海洋也不可避免地以数学的语言,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自己。利用深奥的统计学分支的分析工具,人类有可能做到对捕捉到的海洋放电频率的一定频段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发现,海洋也存在一些构造同源现象,与人类物理学家已知的同类现象并无二致,如物质与能量、元素与物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转换关系等。这种构造上的一致性让人类科学家们确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上苍赋予了超常智能的巨大实体,一个包裹着整个行犀的原生质海洋大脑,它放纵思维,沉溺于对自然原理的冥想中,消磨着亘古以来的光阴,相对于人类那一点渺小可怜的认知来说,它对宇宙奥秘通透的解悟,简直近乎奢侈和浪费。人类电子仪器所截获的,不过是这一巨脑深处那宏大无边、奔流不息的思维长河中的流沙一粒,毫无疑问,其中所藏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的认知。
这就是数学家的论断。有人说,这样的假说低估了人类的智能,这是向未知低头,是“笨蛋就是笨蛋”这一古训堂而皇之的复活。另一些人则说,数学家的这些假说是缺乏想像的、危险的无稽之谈,无非是借巨脑这一概念制造又一个现代神话。其实,原生质也罢,电子脉冲也罢,这些形式都不重要,就生存这一终极目的来说,巨脑都是真正的生命。
然而,有人并不这么想,尤其是那些准专家们,他们人数众多,且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25年的发展,索拉利斯学已高度专业化,各个学科、各个派别之间,鸿沟壁垒,相互阻隔,已难沟通。例如,“接触”学派的思想就与其他学派格格不入;一个控制论专家与一个对称论专家,虽同为研究索拉利斯学的学者,前者就很难让后者明白自己的理论。我上学期间,就有宇宙学协会的主席维毕克曾打趣说:“你们彼此间尚不能沟通,如何奢望与索拉利斯海洋互诉衷肠?”虽是玩笑话,却也一针见血,道出了真理。
把索拉利斯海洋归为变形类并非随意而为,它起伏不定的表面能变幻出无数匪夷所思的形态,与地球的地表形态决无相似处,而且,这些突然爆发的原生质“活动”的性质和作用,仍是一个谜团,不为人知,也许是适应性的,也许是探测性的,或其他什么。
书翻完了。我一边用手捧着书将其放回书架,一边暗自思忖:关于索拉利斯,我们人类的全部知识,图书馆积累的全部信息,原来不过一大堆无用的废话,一个无效陈述与假设堆积出的泥潭。此项研究开展78年来,我们没有取得哪怕一英寸的进步。现在的情形与当初一样糟糕,多年的艰苦努力付诸东流,竟然没有得出哪怕一条无可辩驳的结论。
严格讲,已获取的关于索拉利斯海洋的全部知识都是无用的。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海洋有能力制造机器,但它并未使用过这种力量。在探测工作刚开始的两年间,它曾经复制我们放置在水下的设备元件,但那以后,它似乎对我们的设备和探测工作失去了兴趣,因为它对我们的工作完全置之不理,不再做出任何反应。一句话,它对“我们”不再感兴趣了。它没有神经系统,也没有神经细胞,其身体结构也并不轻易改变,哪怕对最强有力的刺激,它也未必做出反应。例如,在吉斯考察队第二次考察索拉利斯时,曾经发生过一起重大灾难。当时,一枚携带核燃料的辅助火箭从30万码的高空突然坠落,撞击行星表面,引发巨大的核爆炸,霎时间,2500码半径内的所有海洋原生质被摧毁,但海洋完全无动于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在科学界,“索拉利斯计划”逐渐被视为一项失败的事业,在宇宙学协会的管理层中,更有人提议停止对该计划的资金资助,中止研究,甚至有人提出解散索拉利斯基地。这些提议一旦获准通过,即意味着整个计划的彻底失败。后来,在许多科学家的坚持下,索拉利斯基地虽未完全解散,但人员却基本上都“光荣”撤离了。
然而,仍有许多科学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人,不自觉地把“索拉利斯计划”当作检验个人价值的标准和试金石。他们声称,无论如何,该计划不仅仅是为了探寻索拉利斯文明,更是为了考验人类自身,挑战人类的知识极限。有一段时间,由于新闻界的炒作,出现了这样一个广为大众接受的观念,大致是浣:索拉利斯的“思想海洋”是一个巨型大脑,它的智能因极度发育而遥遥领先人类数百万年,它是“宇宙的海洋思想者”,是大彻大悟的圣贤,是全知全能的化身。很久以前,它就已经看破红尘,洞穿意识作为的虚妄,为此,它选择了归隐,归隐于万古不破的沉默。不过,这个观念并不正确,事实上,海洋并非完全归隐无为,它仍有所活动。尽管它既没有建造城市、桥梁,也没有生产飞行器,既没有设法缩短空间距离,也没有想着去征服太空(那可是我们人类的最高目标),但是,它从未停止过变形,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自动变形”(这类描述索拉利斯活动的科学新名词真不少)。致力于索拉利斯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从已截获的一鳞半爪的信息来看,变形活动显然属于某种智能机制甚至超智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