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可透露 作者: 曾鹏宇-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窥视一切的权利。
不过我后来还是很认真地问了朱进中,这55个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他踯躅了半天才跟我点了点头说,有,有一个。我心头一震,我采访了55个孩子的每一个,也给他们每个人拍了照片,他们很多人的名字和容貌,我到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我没有继续下问是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让人不轻松,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答案。
如果答案就这么湮没了多好,可是几天以后我就知道了一切。
55个艾滋孤儿的新年心愿登出来后,无数的读者打来电话,想领养,想接他们来北京过年,等等。把捐款捐物送去河南时,我们找了三名读者代表一起去,阿梅是其中一位,30岁,已婚,还没有孩子。一路上她就在跟我打听星星的情况———星星是55个孩子之一,才5岁,父母双亡,爷爷奶奶无力抚养———阿梅说,在报上一见星星的照片就不由自主地心疼上了,“她那双眼睛大大地看着你,她才5岁啊,怎么就不知道笑呢?”阿梅这次去就是为了星星,她想把星星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爱。
车开了一天,终于到了柘城。第二天早上来到“关爱之家”时,阿梅几乎是第一眼就从孩子堆里认出了星星。星星不说话,这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但却一直沉默着。阿梅叫了星星几声她都没反应,却还是睁大眼睛看你。阿梅被她看得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在上车时阿梅一直愣愣地发呆,眼睛很红。我以为她还是为刚才那一幕难过,就劝她。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她还那么小,她怎么那么不幸……”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了朱进中说的那唯一的答案。阿梅眼泪婆娑地看着我:“刚刚我去找朱进中,说想在方便的时候带星星去北京,她还没见过天安门,没想到朱进中说,孩子身体不好,要治疗,出不了远门。我都傻了,再问,果然……”
再后来写关于“救助艾滋孤儿”的报道,我也没提这事。可能是我过敏,读者询问只是出于关心孩子健康的好意,但我还是宁愿他们不知道,比起其他有父母疼爱的孩子,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不幸到8岁的哥哥要学着给5岁的妹妹梳头,不幸到9岁的孩子就去煤矿做工……而我们能给他们的,也许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2004年2月春节过后,我就又去了河南,算是对“关爱之家”做回访。这次我又见到了星星,她还是那么小而柔弱。因为时常发烧,她那时已经回到爷爷家住。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能做的实在有限,所以在留下200块钱后告辞。如果不是这次去见星星,我就没机会认识单单。出门没走两步,我就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我走来。你是记者吗?我说是。老人的脸让我想起油画《父亲》。
老人没绕弯子,说你能帮助我家单单吗?我这才注意到那个小姑娘,很瘦,脸上手上长着冻疮,嘴唇青紫。她的父母跟星星父母一样,都死于艾滋,6岁的她自娘胎里就成了感染者。因为朱进中能力有限,外村的她没住进“关爱之家”,没钱读书,也没钱治疗。我说,我唯一能帮她的就是报道,可能就要公布孩子的照片以及她的真实身份。老人一脸暗淡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后来老人和孩子的叔叔分别写了一张“委托书”,大意是同意某某某使用单单的照片和姓名作为报道之用。我们报纸刚做完救助,短时间内不可能重复操作,我当时想的是,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其他同行,或者相关慈善机构,怎么都能帮上她。
2004年3月的一天,那天北京刮了很大的风,我给单单的叔叔打了个电话,想把联系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是2月见面后第一次跟他们通话。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孩子叔叔就说,曾记者你不用忙了,单单已经没了。
我整个人如坠冰窖———单单因为感冒高烧不退,家里没钱送医院,就在救助点拿了些药吃,拖了些时日,结果导致呼吸衰竭,殁于3月初。我连她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许连我这个陌生人的脸都没记住。
单单的死让我想起了星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甚至都不敢给阿梅电话,怕她会告诉我另外一个噩耗。最让人无言的是“关爱之家”,我们送去了17万捐款,央视《新闻调查》播出后送去100万,因为怕专款不专用,都没交给县里,结果县里很快提出接收这些孤儿。这真是一件好事,可县里同时要求“关爱之家”关闭,然后把钱物转交县里……
前些日子整理采访材料,发现了单单家人写的那两份“委托书”,安静地夹在采访本里。当时很平静地扫了一眼,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五分钟后坐下来却发现,心分明在通通地跳。
第一月嫂风波
她答得倒也有趣:在跟朱宏钧的交往中,我把她和白岩松看成是一个人。1春节长假后第一天上班,登陆新浪网,赫然看见“热点新闻”里《揭开“中国第一月嫂”全国诈骗的面纱》,点开一看,《中国青年报》的稿子。心里咯噔一下:这事到底还是被捅出来了!
说起来还是前一年冬天的事。一天,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夫人朱宏钧辗转和我取得联系,说有个“月嫂”在外地借白岩松的名义做商业宣传,外带赚钱,结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她想问我们报社可不可以曝光。我一听,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事情要是真报了出去,肯定又是一条轰动新闻!
朱宏钧在电话里告诉我,1997年她怀孕的时候,有朋友介绍了一个做“育婴咨询”的“月嫂”刘洁给她认识,还做过一次咨询。后来孩子半岁左右,刘洁又上门做过一次咨询。没想到这个刘洁从此就向外吹嘘“带大白岩松儿子”,不仅出了本书,还在温州开讲座并当场收钱。结果熟人打电话问白岩松,把白岩松气得够戗,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不知道刘洁是谁!
我当天就开始了采访,没想到第二天又接到朱宏钧的电话,说前晚她和白岩松又商量了一下,觉得《北京青年报》影响太大,这样报出去对他们的私人生活肯定会有影响,没准会把对方炒得更热,所以他们想就这么算了。
我尊重了他们的意见,不过我对朱宏钧说的“炒得更热”印象比较深,就跑到网上去查,发现原来刘洁就是那个媒体报了很多次“中国第一月嫂”,北京某晚报还专门发过宣传她的一个版呢。我一向对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看了这版对这人也没留什么印象。不过当时我隐隐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肯定完不了。
没想到真被我不幸而言中。2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起因是1月22日许多高价请刘洁“咨询”的家长联合到派出所报案,举报她诈骗。这篇文章除了说有家长付出几千上万却得不到相应服务也不能退钱外,还详细曝光了刘洁在温州那次讲座的情况,甚至涉及到白岩松。
文章说刘洁在借《赢在起点》一书宣传自己的时候不忘打“名人牌”,这本书的封面不仅有“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隆重推荐”的字样,还有白岩松的手写签名,并且还提到刘洁多次借白岩松的名义给自己宣传。如果不是之前对此事有所了解,我会以为白岩松真的给刘洁做了这样的宣传。
点开文章后的评论栏,已经有上百条帖子,很多都是骂白岩松的。
于是我就给朱宏钧打了个电话,她果然已经看到了那张《中国青年报》,她正在生气。朱宏钧很后悔:“当初还不如让你们报出来!”我说现在报也不晚,就把你和白岩松的态度说出来,读者自然就会去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在吹牛谁在辟谣。那天下午我就收到了白岩松发过来的有他亲笔签名的传真声明。
另外我还找到了写《赢在起点》那本书的作者周某,他是中央某报的记者。他开始一口回绝了我的采访请求,我说:“现在网上网下都把你形容成刘洁的‘帮凶’,与其拒绝我的采访,不如借这采访表明你的看法。”
他听了我的话,后来带着与他合写那本书的李某(他妻子)到报社接受了采访。
那天我主要的问题是:1·他和刘洁的经营活动究竟有没有关系?2·白岩松的隆重推荐这些内容都是谁提出来的,是他还是刘洁?3·那本书里的材料是他去实地采访过,还是刘洁提供的?有没有核实过?
他的回答是:1·他只是写了本介绍刘洁育婴理念的书,跟刘洁经营活动没有任何关系。2·跟白岩松有关的内容都是刘洁提供的,他为了万无一失,还专门和刘洁签了一个协议,关于这些内容的真实性都由刘洁负责。3·书里那些刘洁的“成功事例”也都是她本人提供的,他没有核实过。
他的原话是:“她说了那么多例子,要一件一件去核实,这哪儿可能呢?”
我说:“借名人宣传没有问题,但是要合法。现在人家说根本就不认识刘洁,你这些题词、签名都是怎么来的?”周某说都是刘洁搞来的。
在那天我和周某的谈话中,他的妻子李某经常会在周某回答不出问题的时候插进来,把事情绕开去。我从《赢在起点》里看到她的介绍,武大新闻学本科毕业,当年27岁。当时我并没有太留意她,因为那时我以为她不过是个次要人物而已,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比较天真。3那天我也拨过刘洁的手机,但是那个号码一直关机。
2003年2月9号我那篇稿子《白岩松:我从未推荐过“第一月嫂”》见报了。
2月10日,我听说刘洁在找我,原来她的手机早换了号码。我把电话打过去,她在电话里气势汹汹地说那篇稿子失实,坚持要到报社来,还要“和你们领导一起好好把这事说清楚”。我一听乐了,正愁找不到下家呢,她倒自己找上门来了。
然后我就在办公室里等她,可从下午1点一直等到4点,她都还没有来。正在纳闷,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她说你知道吗刘洁带了好几个人正在《中国青年报》报社闹呢。我吃了一惊,难怪她这么久不来,原来是准备挨家找麻烦啊。放下电话没几分钟,刘洁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人,还有一个扛着摄像机———拦住那人一问,原来是“河北卫视”的,说本想拍关于刘洁的纪录片,结果碰上这么一场风波,想全程记录。想想,也没有什么不能拍的,就同意了。
刚坐下来,刘洁就扣了一顶大帽子上来:报道失实。我本来是想听她有什么辩解的话,结果发现她绝对不是那种只守不攻的人,她的策略是以攻代守,哪怕是闭上眼睛一阵乱攻。见我年轻,她的气焰很盛,称呼白岩松那叫一个亲热:老白、岩松;说我跟老白那么熟,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你这文章就是失实!
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拿得出白岩松的授权吗?这女人说我跟朱宏钧说过。我说你认识白岩松的妻子跟认识白岩松是两回事。
她答得倒也有趣:在跟朱宏钧的交往中,我把她和白岩松看成是一个人。不过越接近事实的核心,比如签名和题词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得到白岩松夫妇的认可等等这些问题,她就一概糊弄过去,就算旁边有摄像机对着,她也毫不改色。
到了后来,我已经烦了,这人整个一空手道嘛!其间不断有报社同事进出办公室,见我跟一中年妇女对坐着“探讨”问题,旁边还有一摄像机伺候着,都觉得有点搞笑,有人居然还拿出相机来拍。真是,什么立场!
那天刘洁晚上六点多才走,最后大概她也意识到这次有些失策,脸色不算好,跟进门时的趾高气扬有了天壤之别。那天的场景我又详细记录下来,发在第二天的报纸上。4当时我以为,这件事已经差不多了。没想到那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读者马先生打来的,他说除了《赢在起点》这本书外,周某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叫《芝麻开门》,这两本书是一套丛书,里面都有吹捧刘洁的肉麻文字,但是马先生发现那本《芝麻开门》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卡尔·威特的教育》、《井深大早期教育法》、《斯特娜的自然教育》这三本译作中抄袭过来的,但是在书里却成了刘洁提供并“审校”的内容。
这个读者电话让我本来已经放松的神经又绷了起来。因为刘洁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一方面是因为早教市场毫无章法可言非常混乱,另外一方面也跟她周围像周某这样的写手卖力的吹捧不无关系。如果没有接二连三的在媒体上露面,谁知道刘洁是谁啊?
况且很多家长是因为看了报纸的报道才高价请刘洁去做咨询的。中国老百姓对媒体有种天然的、朴素的信任感,如果利用这种信任感牟取利益,是非常不齿的行为。
编辑本来也准备就此为止了,但是听到这个情况后也同意让我再做一次采访。
马先生是一位博士,孩子刚4个月大。他不仅拿出了《芝麻开门》和其他三本书,还把书中一模一样的地方都找了出来。其中《斯特娜的自然教育》一书几乎是被整个克隆到了《芝麻开门》中。另外我居然在《芝麻开门》的前、后分别找到两部分完全一样的文字,并不是印刷错误,也不是一段两段,而是好几页。想了半天,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抄重了,又忘了。
这次采访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我从马太太那里知道,她按照书上留的联系电话打过去想找刘洁,没想到接听的“育婴专家”竟然是李某,也就是周某27岁的妻子。她也在从事和刘洁一样的工作,而且收费也和刘洁一样,顾客上门一年4800,她上门一年10000。这让我很吃惊,因为8号这夫妻俩亲口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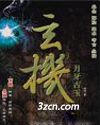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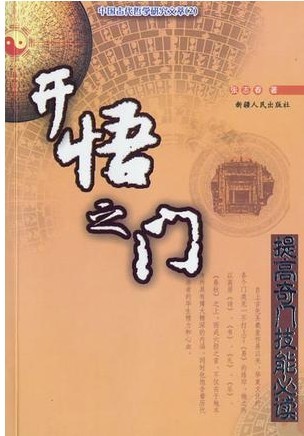
![[官场红人秘笈]玄机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