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
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
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
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
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
(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
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
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
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
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
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
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
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
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
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
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
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
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
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
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
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
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
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
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
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
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
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
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
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
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
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
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
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
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
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
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
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
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
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
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
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
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
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
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
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
“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
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
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
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
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
集团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
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
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
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
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
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
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
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
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
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
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
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
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
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
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
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
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
际增长数50~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
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
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
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
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
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
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 “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
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
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
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
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
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
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
《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
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
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
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
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
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
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
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
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
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
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
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
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
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
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
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
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
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
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
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
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
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
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
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
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
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
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
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
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
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
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
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
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
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
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
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
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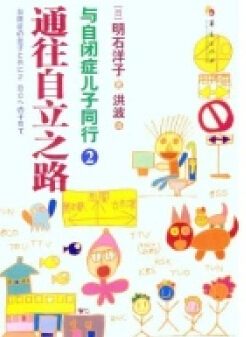
![(新神探联盟同人)[新神探联盟][展白-正泽]无法前进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10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