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72页。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时完成最后一
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
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
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
送给政治局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至今记忆犹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
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月4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
产党中央第一书记f.M.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记之后,让我发言。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
心:哪怕以“压缩” 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
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 (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
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
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
的弗洛连季耶夫对我耳语道:
“总的说来讲得很不错。不过不该不听我的,我可是建议有些话不要讲的。主
席团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么为什么到1978年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
科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这么说,还有另外
一边,它在哪儿,是什么样的,谁又站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国领导班子内部的争论。但我把这
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
作,才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在派系,
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解,以为这是“改革派” 与“保
守派” 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同一“信仰” 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
角逐不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量。首先是格列奇
科和基里连科,接下来是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再下来是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
还有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于勃列日涅夫也要依靠级
别较低的官员,自不必说。但现在我认为,政治局内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
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
复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
1978年7月库拉科夫淬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物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这样
的一个人,就是上任后不会破坏高层内部不稳定的平衡。这个我当时明白,但是对
许多情况并不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推测,当时把我作为候选人向全会推荐
的决定多么地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
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与各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系。
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
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板。
安德罗波夫“因素”
1978年8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话。
“你那儿情况如何?”
“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未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确认了我们之间的良
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
常多,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特别
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
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 对维护领导班子的
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见解。现在明白了,
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谈话” 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
好一阵数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谈话的继续,
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而出:
“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对我的“晴天霹雳” 习惯了的安德罗波夫大惑不解
地答道。
“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已经时日不多……”
应当说,当时在年龄方面政治局内的形势相当紧张:平均年龄接近70。人们感
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
规律的关系已不能履行职责。尽管如此,至今他们全都占着位子不下来。
安德罗波夫大笑:
“你把我们说得……”
“我不是指您,不过这个问题可是得考虑了。您看看吧,书记的情况也一样,
还有地方上……”
安德罗波夫开始讲他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如果提拔上岁数的人,这样的人
已有经历,也有经验,却没有野心。工作起来没有任何向上爬的派头。而所有的年
轻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 简言之,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老马不
毁垄。”
我开玩笑地反驳道:
“这可是列宁干部学说的新发展。我一直以为任何时候都必须搞新老干部结合。
这样就成了合成,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险主义,又可以防止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
“这都是理论,生活中不是这么回事。” 安德罗波夫不以为然。
“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列宁的意见。”我狂热地坚持。
“我也同意列宁的意见。” 安德罗波夫嘲讽地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宁……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
带小灌木丛。”
安德罗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我说的“小灌木丛”,忘不了这次谈话。而国家已经
无法接受并从心理上拒绝“老人当政”。有关社会情绪的信息肯定也传到了高层的
耳朵里。有的直言不讳,有的则采取“经典的”、即匿名信和笑话的方式。我记得
有这么一则笑话,不错,那是后来,苏共二十六大之后才出现的。俏皮之处全在对
问题的回答上:“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
都是抬着进去的。”
总而言之,“信号” 传到了政治局和总书记的耳朵里。他们也担心这个问题。
因此库拉科夫的接替者还一定得是比较年轻的。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
“插手” 了,不过他并未对我作任何暗示。
这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去巴库,参加
授予阿塞拜疆首府列宁勋章的庆典,由契尔年科陪同。每当火车在沿途停留时,当
地领导都出来迎接。勃列日涅夫在顿涅茨克会见了州委第一书记B.卡丘拉,在罗斯
托夫会见了邦达连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高加索车站会见了梅杜诺夫。
当天晚上,专车抵达矿水城车站。由安德罗波夫、我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执
委会主席T.塔拉诺夫迎接。
矿水城车站十分舒适可爱,但是不大,极易一晃而过…… 那是个温暖而漆黑的
夜晚。群山的轮廓依稀可辨。市区灯火点点。天上缀满大颗的星星。这样的星星只
有在南方方可得见。万籁俱寂。只有飞临矿泉水机场的飞机打破了宁静。列车平稳
地停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下火车,过了不一会儿,身着运动服的契尔年科也下了车。
塔拉诺夫向总书记问过好后走到一旁,于是我们四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契尔年科和我)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漫步……
人们就这次会见写了许多文章,围绕会见编造出的神话可说是无奇不有…… 那
还用说!四位相继替换登场的总书记。
我是从基斯洛沃茨克与安德罗波夫同乘一辆吉尔车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的。两人
之间的谈话与往常完全一样。他仿佛是顺便提了一句:
“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
然而谈话并不投机。在寒暄问好和不疼不痒的关于我和安德罗波夫的健康和休
假的话语之后,就开始冷场了。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
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
这次会见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见面、为解决边疆区的问题让他接见都不止一
次。他每次都表现出由衷的兴趣,并给以帮助。因此在一阵长时间的冷场之后他突
然提出问题,我就不感到奇怪了。他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们那个绵羊王国的情况如何啊?”
斯塔夫罗波尔提供了俄罗斯联邦27%的细羊毛。初夏,在产完春羔之后,草原
上放牧着成千上万个羊群:共有羊1000万只。那场面确实动人。名副其实的“绵羊
王国”。我简单讲了讲我们的情况。当年是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
个斯塔夫罗波尔居民两吨。
第二个问题是:
“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 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我设法解释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又是一阵沉默。安德罗波夫不时以期待的目
光看看我,契尔年科却完全哑巴了,这是个“边走路边默默作记录的装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休假怎么样了?还休不了吗?” 我尽量把谈话维持
下去。他摇了摇头。
“是的,应当,应当……”
安德罗波夫加入了谈话。他们就勃列日涅夫在巴库的活动日程交换了意见。又
开始冷场了。看得出来,总书记不是很愿意谈话。停留的时间结束了。我们走到车
厢面前。他已经站在车门口,抓着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
“讲话如何?”
“很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
到了车上我问他,总书记问的是什么讲话。原来是另一回事。安德罗波夫解释
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大概这多半就是他沉默寡言的原因吧,不过
论禀性他可是个好交往的人。
总之,这次会见让我感到奇怪。看来安德罗波夫倒是很满意。
后来还有第二次“相亲”。矿水城车站那次会见之后,基里连科突然访问斯塔
夫罗波尔。他正在索契休假,是乘直升机过来的。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同他一起前
往苏联科学院泽连丘克天文台和农业区。我向他讲了我们的问题。让我大为吃惊的
是他那动辄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的派头……路上看见农机修理场,就大动肝火
地训斥开了:
“那儿该有多少没用过的机器?捞的机器太多了……是不是打算卖废铁?你们
简直把嘴吃习了……”
他在政治局主管机械制造业,他认为农村的要求太过分。他那傲慢的教师爷口
吻刺激神经,拙口笨舌、不善言词又使得与他的谈话完全成了一种折磨,根本无法
弄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反正我们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极其紧张。我内心里感到他
不怀好意,于是以牙还牙,指桑骂槐地暗示我们这位客人对所谈的问题一窍不通……
我们显然是彼此都没有好感。以后也一直如此。后来已经在苏共中央工作了,
我发现基里连科不愿意我到莫斯科来。此外,他还是个擅权和爱记仇的人。我们的
关系发展为对立,后来更成了政治对抗。
不管怎么说,毕竟选中了我。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误,到最后一刻还
心存疑虑。因此同我的谈话早先没有进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进入领导班子的人选
时慎之又慎,需经过长时间的困难的选择。可一旦作出决定,就决不放弃。
整个夜晚我都是在饭店的窗户旁边度过的,逐一回顾了许多往事。不觉已是次
日早晨,到了准备参加全会的时候。考虑再三,决定如要发言,一定要讲农民的状
况,谈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必须改变。
我早早地离开了饭店,免得碰见人。不想多费口舌去作解释。
苏共中央全会于10时开始举行。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座位事先未
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稳坐了几十年。
一切都和契尔年科所说的完全一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
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
一致通过。平平静静,没有情感的流露。
然后,全会同样平静地将契尔年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
古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候补委员。“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马祖罗
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
反对意见。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国家计委主任HJ.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经济与
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 1979年苏联国家
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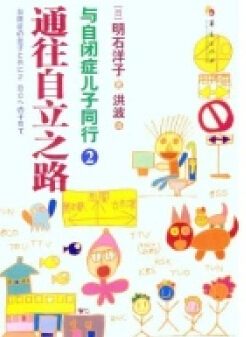
![(新神探联盟同人)[新神探联盟][展白-正泽]无法前进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10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