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长们包围起来,他们纷纷向我表示
祝贺。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应邀前往主席团的房间,里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员、候
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我走了进去。大家都在那里。安德罗波夫离我最近。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来:
“祝贺您,‘小灌木丛’
柯西金走过来,不知为什么十分信赖地说道:
“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对他讲话。他继续喝他的茶,只是点了点头。全会结
束后,我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
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
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
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我往家里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电话:“晚上听新闻。” 次日上午,我未经
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
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大
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
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示立即投入
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 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
能。我知道您对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
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我的话、对我
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句话是:
“库拉科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
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后,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倒霉
事。心里很不痛快。
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直奔老广场。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前
任库拉科夫在老楼的四层办公,与五层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近在咫尺。我的办公室
则安排得较远:在新楼(六号门)。
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说,中央书记“应有”:每月800卢布(“和列昂
尼德·伊里奇一样多”),伙食限额为每月可订购价值200卢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员
为400卢布),工作时间的伙食成本和札仪方面的开销均由办公厅承担。
“关于住宅、别墅以及服务人员的建议,赶在您从斯塔夫罗波尔回来的时候拿
出来,” 帕夫洛夫最后说。
决定对各位中央书记进行礼节性拜访:谈一谈,接触接触,毕竟大家要在一起
工作嘛。分别拜访了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和鲁萨科夫。我
去见波诺马廖夫时,听到了他对农业的建议。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
至他退休方告结束。波诺马廖夫属于“业余农学家”,他乘车从自家位于乌斯片斯
基的别墅出发,注意到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昨天我看见路边有一块地。庄稼熟了,该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动。这叫什么
事儿?”
要么是:
“昨天我在别墅附近散步,来到一片冲沟旁边,草有齐腰深……为什么不割?
在瞅什么呢?”
确实如此:堂堂国际问题的专家,却煞有介事地就农业提出“专家” 的建议。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则是拜访中央书记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助手和顾问的表现。
许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已不下数十次。我觉
得关系很正常。曾几何时……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些人了。出现
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
“官阶表” 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
为牢固的准则。
我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
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 昨天他们还在向
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
意见……” 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他们召集到一
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
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象原来一样地工作。” 这下大家都放心
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
游戏规则
接下来是拜访安德罗波夫…… 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不过我觉得他安排见面是
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首肯。谈话刚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而且整个谈话都与我们
以前的多次谈话大不一样。
“米哈伊尔,我想向你介绍一点情况。你知道吗,现在团结最重要。团结的核
心就是勃列日涅夫。这点要记住。领导班子中曾经有过……怎么给你说呢……我指
的是,比方谢列斯特或者谢列平,那个波德戈尔内。他们都自行其是。现在这号人
没有了,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不习惯像打哑谜一样与安德罗波夫讲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对我、对我的观点和立场最了解。我并不打算为
了取悦谁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安德罗波夫微微一笑。
“那太好了。因为我看见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
要顶住。”
原来如此!……全会休息时间在主席团房间里接受祝贺时,我发现安德罗波夫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来,他并未放过柯西金那句话和说话时信任的口气。
我问道: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
么变化吗?”
“没有,没有,”他回答说,“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 安德罗波夫此后
并未食言。
然后我给苏斯洛夫去电话,他请我过去。我早就认识他,他对斯塔夫罗波尔有
着深厚的感情。1939年他从罗斯托夫到我们边疆区来当第一书记。在斯塔夫罗波尔,
人们将走出残酷的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与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在同我谈话
时回忆道,当初形势极其严峻,他纠正错误的最初步骤受到部分干部的反抗。斯塔
夫罗波尔市卡阿诺维奇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委
常委为“人民的敌人”。不过挺过来了。
附带说说,同苏斯洛夫的谈话总是很简短。他讨厌饶舌的人,谈话时善于迅速
抓住问题的实质。不喜欢多愁善感,与对谈者保持距离,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一
本正经,一律以“您” 相称,只有极少数几个人例外。
这次他把我叫去,是为了讨论由谁来接替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桌上放了
两份个人档案:穆拉霍夫斯基,1926年生,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
卡兹纳切耶夫,1935年生,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你是什么意见?” 苏斯洛夫问道。
“我认为应当推荐穆拉霍夫斯基,”我回答说。“他经验很丰富。这个人已经
很成熟。至于卡兹纳切耶夫,要么还当第二书记,要么去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
当第一书记。”
“就这么说定了,”最后苏斯洛夫站起来说道。“你去搞个决议。所有的文件
这边随后寄去。”
不久,我乘机前往斯塔夫罗波尔。
第二章 往事在我心中
从斯塔夫罗波尔乘飞机去莫斯科,对我说来已是家常便饭。中央全会,苏联最
高苏维埃会议,会议和讨论会,去首都解决边疆区的问题……
起初是在矿水城上飞机,而当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和可供大型飞机起落的
跑道竣工(我也曾参与其事)之后,事情就变得更加简单,时间也更加节省了。生
活节奏变快了,老得节省时间,我当时认为那些坐火车的人都是在逃避工作,合法
地为自己另外安排一次休假。
飞行本身总是激起我积极的情感。我喜欢飞行。遇上阴云密布或者风雪交加的
天气,飞机升至云层之上,你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一种不可言状的无比开阔
和自由自在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若再步人驾驶舱,就会分外感觉到飞行之速度和
强度,仿佛整个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无边无际。宇航员说,从太空看我们的星球,
觉得它没有那么大。而从飞机里看出去,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只觉得地球真是其大
无比。
这次去斯塔夫罗波尔我是第一次乘坐专机,它由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的特别航空
分队提供。陪同的卫队坐在另一个机舱,这边就我一个人。我靠近舷窗,期待着这
次飞行也会给我带来自由自在和生活充实的感觉。心中却很不平静。我猛然醒悟到:
我要长期地以至永远地告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了。47年的生活中,我在这片土地
上度过了42年。上大学期间,我每次放暑假都回来(冬天不回来是因为经济上捉襟
见肘)。
对我说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里有我的根,我的故乡。我与这片土地生在一起了,她那生命的乳汁在我身
上流动。我热爱斯塔夫罗波尔。
根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莫斯科人的说法,尤其是在大学期间:“你们那个外省嘛,
愚昧落后…… 死气沉沉的王国。平平静静。” 说话者坚信,千百年来的整个人类
历史全是在首都创造出来的。但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我故乡的历史就是最好的
证明。并不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并不是外省,而是两个大陆的接合处,各种文
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处,许多民族、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接触点。
我不仅是从教科书和我仔细收集的地方志著作中了解到这些情况的。1975年在
皮亚季戈尔斯克附近的建筑施工中,马舒克国营农场内发掘出一个古墓。发现了墓
穴,那是一位领袖及其四名亲信的遗骨。学者确定墓葬已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1世纪,在斯塔夫罗波尔、西北高加索即有古希腊、罗马作者称之为
苗特人和辛德人的部落居住,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当时在北高加索土地上建立了奴
隶制国家。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西徐亚人从第聂伯河沿岸和克里米亚人侵此地。
后来这片土地属于希腊殖民的范围。公元初年阿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
国家,这个国家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他们被匈奴歼灭了。大约从9世纪开始,基督教
从拜占庭和格鲁吉亚传到这里。10世纪出现了第一批俄罗斯人,并出现了与基辅罗
斯联系紧密的特穆塔拉坎公国。13世纪开始了鞑靼蒙古人的入侵。
随着俄国的形成,高加索各民族开始从与它的联系中寻求摆脱形形色色的征服
者的保障。1555年8月伊凡雷帝的使者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公使从北高加索回
到莫斯科。伊凡雷帝宣布皮亚季戈尔斯克王国永远隶属俄国。开展了俄国防线的建
设,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建起了所谓的亚速一莫兹多克边界设防线,由七个城
堡组成。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批卫士为霍皮奥尔哥萨克(沃罗涅日省)
和弗拉基米尔团的近卫军士兵(弗拉基米尔省)。
俄国军队也来到这里。开始建设哥萨克村镇。为了逃出残酷地主的魔掌,农民
也往南方跑。后来则开始以强制方式将农民流放到此地。这种移民是极其惨烈的人
间悲剧,不少人成了牺牲品。其中既有我的曾祖父母戈尔巴乔夫一家,沃罗涅日省
的移民,也有来自切尔尼戈夫西纳的外曾祖父母戈普卡洛一家。
在这俄国的南部边疆,连人的性格也来得特别,甚至可以说那是反抗的性格。
难怪许多人民运动的首领正是在这些地方集合起自己的队伍并开始远征的,这里有:
孔德拉季·布拉温和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利扬·布加乔夫。
根据传说,就连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也是这些地方的人。
看来这已深入到此处居民的血液中,并且世代相传。
我的曾祖父莫伊谢伊·戈尔巴乔夫和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里戈里和安德烈)
在普里沃利诺耶村的最边上住了下来。他们起初都住在一起,一个大家庭,18口人。
旁边是近亲和远亲,都姓戈尔巴乔夫。家庭里的秩序严格而清楚:曾祖父是首脑,
他的话就是法律。儿子们成家后都另外盖房单过,我的祖父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
当时与外祖母斯捷潘尼达结婚,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1909年,我的父亲谢尔盖·
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生了。
家族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无条件地接受的。他
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 “我们的土
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
人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
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
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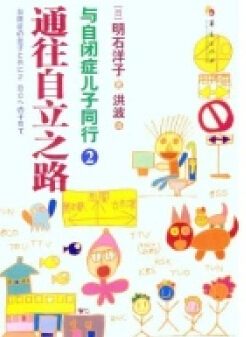
![(新神探联盟同人)[新神探联盟][展白-正泽]无法前进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10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