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
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
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
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
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
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
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初次
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
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
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
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西德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
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
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
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
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
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
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
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
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
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
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
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
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
逐渐建立了人际间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启动的德
国统一进程而“压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1988年10月那个时候,我们闯过了我们两国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道难关。在经
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文件。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战
后关系史上,两国国防部长首次坐在一张谈判桌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不久前的
“潜在敌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促进北约和华约建立接触方面,我们征得了德国
人的原则上同意。当时这是一个“突破”,而在三、四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联邦德国总理在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并拜谒柳布里诺的德国士兵公墓。慕尼
黑交响乐团这些日子里在圆柱大厅演出了贝多芬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获得了极大
的成功。我和科尔、我们的夫人、参加谈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听了这场音乐会
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两地游览,参观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
(圣丹尼洛人修道院),观看苏联艺术家之家举办的君特·霍克纳的画展。联邦总
理还会见了经济学家。科尔夫人参观了精神神经病医院,并向该院赠送了贵重的设
备,她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庄园。
在郊外住所的会晤,在这次访问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次会晤使访问在政治量度
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量度人性的量度。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这里没
有再谈一般性问题和种种忧虑,而是谈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思所想,了解了双方
的家史。我认为,我们是相互怀着好感而分手的。
在西方,人们对这次访问十分关注。联邦总理定期听取有关北约盟国反应的汇
报。《巴黎日报》和《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科尔的警觉,这两家报纸直言不
讳地说,这次访问的性质使人对联邦总理是否忠实于联盟的义务产生怀疑。在莫斯
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问科尔:您给了俄国人那么多,可您得到的回报
是什么,就是俄国人许诺释放的几名政治犯吗?要么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该如何
对待法德联盟、法德联军以及对法国人作出的其他许诺,科尔是否改变了航向
由法兰西的西方转向了苏联的东方呢?
美国报纸和外交界的指桑骂槐也未能逃过我们和科尔的注意。因此,联邦总理
将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定在1989年5月并非偶然。他估摸在这段时间内法国人将访问
苏联,而且我们还将和美国人进行接触。况且还不仅仅只和法美两国接触。这一切
都在1988年年底发生了!本以为这时变化很大,却原来变化很小!我们的对手们正
在步履维艰地走出“冷战”的丛林。当时我越来越频繁地说:不仅我们苏联应当转
变,你们西方国家也应当有个大的转变。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2年春天,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美国人说:我们需要自己
的美国式改革。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而一度陶醉于“冷战““胜
利”中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作好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准备。
回顾科尔第一次访苏,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
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在这方面采取的后续步骤具有深远的后果我们对1989
年底至1990年发生的事件原来是有所准备的。
对联邦德国的正式访问
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始于1989年6月12日。在这之前我刚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我以新的身份出访的第一站,在这个背景下看上去颇
有象征意义。
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十分紧凑。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联邦德国的几个州,许
多个城市和乡镇,会见了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党代表和社会运
动代表。
在联邦德国总统里哈德·冯·魏茨泽克官邪门前举行的欢迎仪式揭开了访问的
序幕。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同波恩的居民进行接触。同一群青年学生的会见格外令人
动情。我们当着总统的面热烈地交谈起来。年轻人希望向我表达他们对苏联改革的
声援。
接下来是总统在莱茵河畔的官邪设早宴。通过席间第一次交谈我已经明白了为
什么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德国公民中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识广博、风度儒
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我们的谈话一次更比一
次坦诚、充满信任。
在波恩市政厅广场的那次会见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还走在与广场毗连的街道
时,就已经置身于人的情感、友爱。亲善的洪流之中。欢呼,祝福……你无法记住
每句话。但其中有些话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戈尔比!要创造爱,不要修筑大墙”,
“请这样坚持下去,戈尔巴乔夫!”
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
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
束鲜花向我们走过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护栏上。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个场面曾出现在许多电视屏幕和无数报刊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中安排了去施图肯布罗克小镇拜谒苏军战俘纪念公
墓。战争初期这里建了一座集中营,关押战俘和从各个国家强行挟持来的人,这些
人被利用在矿山、军工企业、农场做工。他们只得到很少的口粮:每天只发给200克
面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么面包。他们的劳动却极其繁重。数十万苏联人以及波
兰、英国、法国的公民被关过这个集中营。我国同胞大约有65000人在这里遇难(被
处决、饿死、病死),埋葬在集中营的附近。
1945年4月2日美国人把这个集中营的囚犯解救出来。苏联战俘代表组成的倡议
发起小组坚持要求为死难的同伴整修坟墓。1945年5月,根据原集中营的囚犯、建筑
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莫尔丹(1984年去世)的设计,在公墓建立了一座
方尖碑,纪念在施图肯布罗克遇难的战俘。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月,这座公墓逐渐荒芜。然而有一个小组在牧师迪斯特
尔·麦奥尔的带领下主动地照看墓地和纪念碑。1963年这个小组改组为“献给施图
肯布罗克的鲜花”工作小组,它提出了“在死难者的陵墓上向俄国人伸出援助之手”
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纵容下,新法西斯歹徒
践踏陵墓,并试图毁掉纪念碑。于是出现了一些青年护卫队。到了70年代,“献给
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积极活动着的反战社会团
体,它拥有来自西德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会员。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们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团参加这项活动。但正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所说,这个
公墓却没有来过一个官方代表团,无论是西德的还是苏联的代表团。
这一次随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仅仅有代表团团员,并且还有陪同我
访问的文化界人士,东正教教会代表皮季里姆。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汉内洛雷·
科尔和劳女士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夫人。
那一天邻近城镇的居民在公墓举行了集会。他们向纪念碑献了一个饰着长长的
红色丝带的花圈,而科尔夫人和劳夫人献了鲜花。都主教皮季里姆发表了讲话。这
一次做了早就该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强加的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墓默哀,并向新德国
的公民说了友善的话语。德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而详尽的报道,认为这是一件值得
纪念的大事,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您在参拜公墓之后有何感想?”记者这样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
了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家庭不为在那个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亲人而悲痛。
我们知道,那个年月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向那些关心我国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谢。”
沉重的回忆,无以慰藉的哀伤。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更加理解,通向苏德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和解、亲近的路途是多么艰难。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厂冶金工人的会见令人激动。我们刚下汽车就受到了
几千人夹道欢迎。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大车间,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挤得满满的。除
了临时布置的“池座”之外,机床上,隔墙上都挤满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构件
上,吊车上,还有的人相互轮流着爬到肩膀上。我们代表团、工厂的领导人、工人
代表被安排在讲台上。听了别人对我们讲的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了,按照准备好的
讲稿去讲是行不通的,即使离开讲稿而另外加进几句也不行。由于我几乎每说一句
话都被喊叫声和欢呼声打断,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间应当采用的讲话方式,直截了当
地、而不用任何华丽词藻地谈了劳动者在一切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谈了德国人民
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
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
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
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
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
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
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
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
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
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
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柏林墙的倒塌
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部分”发生了使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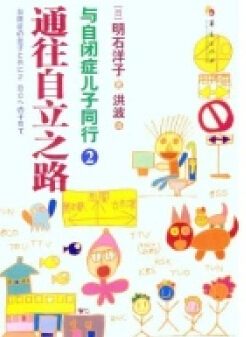
![(新神探联盟同人)[新神探联盟][展白-正泽]无法前进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10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