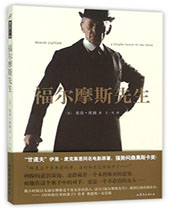福尔摩斯和萨默塞特狩猎-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法辛盖尔医生听见福尔摩斯提到打猎的事时,生气地对小休伊特摇了摇头。“千万不要对我讲你明天打算骑马,安德鲁。”
“这是秋天以前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不能错过它。可怜的德格伦纳迪尔会认为我完全抛弃了它。今天我觉得身体完全好了,早晨甚至会更好。”
法辛盖尔医生和我两个人尽力向我们的病人说明硬要加快养好脑部所受意外创伤的速度的危险性,但是休伊特坚定不移。有一个时刻我望望福尔摩斯,指望他支持我们的恳求。但是他抱起那只新发现的小猫。似乎全神贯注在和它玩耍上。我只能推测,如果我们的委托人明天要冒生命危险,不知怎地倒很合他的心意。一旦认识到所有的劝说都没用时,那个上了年纪的医生就起身告辞,临行前频频地祝安德鲁·休伊特和他的新娘健康幸福。
当那个医生在小路尽头转过身挥手示意时,安德鲁·休伊特对福尔摩斯说:“你从那位医生口中查明你想知道的情况了吗?”
福尔摩斯摇摇头。“你母亲的失踪显然导致了家里人和熟人们的分裂,不过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分裂了三年以后才试图谋害你,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
“我对你说过这毫无意义。我母亲和这事毫无关系。”
“我本来可能希望你们俩从一开始就对我非常坦率诚实。你们两个。当你的妻子对我讲家里人‘意见不一致’时,根据你朋友、那位医生叙述的一些事件判断,那简直是使人容易误解的、没有充分表达真情实况的陈述。我认为你的妻子了解实情。”
“哦,是的。好多好多星期以前,”安德鲁休伊特说,多情地朝着他的新娘微微一笑,“让她看看她的骑士的闪光盔甲上的凹痕和裂口是公平的。”
“很好,”听起来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些气愤,“不过现在,休伊特先生,彻底对我说说,我听到了这家人以及你母亲失踪和你自己最近坠马事故的全部真实情况吗?”
休伊特肯定地点点头。“当然啦。我把一切都向休医生吐露了;他了解我的一切秘密。”
“很好。”福尔摩斯点点头说。“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不再面对你家里另外一个成员讲的真实情况。休伊特夫人,希望你会原谅我,不过我想在你不在的情况下爱德华·休伊特会更易于无拘无束地讲话。”
“我去把小猫送给普拉特。”那位夫人愉快地说,稍稍吻了吻她丈夫,就朝马厩走去。福尔摩斯歪着脑袋望着她的渐渐远去的背影,突然问安德鲁·休伊特此时此刻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哥哥。听说在书房里,我们就都转身向那里走去。就像他弟弟所说的,我们在书房找到了爱德华·休伊特。他远远地坐在屋子尽头的一堆小火前面的安乐椅上,带着经过一段紧张或愤怒的时期以后力求恢复镇静的人的姿态抽着烟斗。我们进来时他转过身来,看见弟弟他的脸上立刻现出欢迎的笑容,这与他以前和我们打交道时总带着的严厉和有所戒备的神色形成了鲜明对照。“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他用拘泥于形式的声调说。
“福尔摩斯想和你谈谈话,内德。”他弟弟说。
福尔摩斯示意我关上我们后面那扇门。那位哥哥讥讽地对我们笑了笑。“这一定是很严肃的事喽,他说,“你们坐下吗?让我们都坐在窗口吧。”
我们在面朝一座正规的意大利风格花园的凸窗里的小半圈椅子上依次坐下。我想福尔摩斯会立刻开始他的谈话了,但是他却保持着沉默,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爱德华·休伊特,直到我们大家都感到完全不自在起来。
“好啦,福尔摩斯先生,”那位律师终于说,“你看够我了吗?你有什么话要说?”
“你可以先说呀,休伊特先生,”福尔摩斯平静地回答,“我倒想听听在这段皮带的问题上你有什么可说的。”
爱德华·休伊特极其冷静,就像从我们周围的书架上给他拿了一本稍微有趣的书一样,他没有流露出丝毫惊奇的种情,然后便从福尔摩斯手中接过那段有罪的皮带。
“这么看来,”他说,“你去过我的房间,是吧?这就是你给我们带来的有礼貌的客人们,安德鲁。”
安德鲁·休伊特看到丢失的那段马镫皮带大吃一惊。第二个打击是他听出言外之意是他哥哥把它藏了起来。在他拼命想从许多要说出来的话中说出一种明白易懂的想法时,福尔摩斯继续说了下去,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心慌意乱的神态似的。
“你承认你弟弟坠马时是你把它从地上捡了起来吗?”福尔摩斯问。
“既然毫无疑问你在我的东西中间找到了它,我当然不能否认。为什么,”爱德华·休伊特带着一点高傲的神情说。“你要搜查我的房间?”
“因为我相信我会在那儿找到那段马镫皮带,”福尔摩斯说,“现在告诉我——还有你弟弟——你为什么把它拿走藏起来?”
“我把它拿走为的是不让我父亲看见。看看给老鼠咬了的这个地方。我知道父亲会因马厩的一个小伙子没有照料好马鞍而非常恼怒,因此我把它放在口袋里希望他不会发现。不过显然我的单纯行动遭到了误解,有人,可能是你的简的叔叔。请来了侦探。多么荒唐啊!”
安德鲁·休伊特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我的马鞍是被老鼠破坏的,那就意味着没有人企图杀害我。”
“杀害你!”爱德华·休伊特惊呼道,“老天爷呀!当然没有!我只希望你没有使那个爱管闲事的老法辛盖尔也得到线索。”
“你自己干了那件事。”福尔摩斯说。
“哦,那个该死的爱管闲事的老家伙,我还能做什么呢?”爱德华·休伊特规劝说,“安德鲁,你告诉他这全是误会,好吗?我们不希望他再探听别人的事,是吧?”
“他只不过想帮助我,内德,”安德鲁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反对他。”
“噢,亲爱的弟弟。”爱德华·休伊特挥了挥手,“让我们别让这两位先生听到由于老法辛盖尔而使我们重复了五百次的争执吧。现在马镫的事你满意了吗?你会叫你的新亲属们把他们的侦探送回伦敦吗?”
歇洛克·福尔摩斯似乎觉得非常有趣。“我想,你弟弟能够摆脱掉我时,他就会是最幸福的人了。”
“我没有什么事反对你,福尔摩斯先生,”安德鲁诚挚地说,“只要你停止追问远远超出你的调查范围的所有那些令人痛苦的问题就行了。我希望,你对内德所讲的真实情况感到满意。”
“是的,”福尔摩斯同意说,“我想他的话彻底解决了你最近坠马的事。”
“那可太好了!”安德鲁大声呼叫着跳起来,“你要呆到明天打猎集合的时候,好吗?连我父亲都希望看见你骑马打猎。华生表亲,当然一定要留下。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结了婚的事告诉大家。这儿再也没有秘密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人身边冲到另一个人身边,拍拍我们的肩膀,握握我们的手。
“很好!”看到他弟弟突如其来的兴高采烈情绪,爱德华·休伊特露出了微笑,“除了一个场合:你一定不要对爸爸讲老鼠的事。另外没有人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是私人侦探可能也好,你同意吗?”
“对哪个问题都只字不提。”安德鲁答应,“我去告诉简我们的忧虑结束了。我不是也说过了,福尔摩斯先生?一旦我们对内德讲了,一切就会解决了。而且真的——果然如此!”
他向他的妻子那里冲去,但是我们却留恋不去,福尔摩斯依旧拿着那段马镫皮带——促使我们来到库比山的那件东西。爱德华·休伊特看了它一眼,摇摇头。
“先生们,你们从伦敦白跑了一趟,我真感到遗憾。我们的新姻亲们竟然认为我们能够伤害自己的家属,这对我们简直是强烈的谴责。”
“这么快就使怀疑烟消云散,也值得走这一趟,”福尔摩斯回答,“我非常惊奇你竟然这么费力劳神地来保护马厩的一个小伙子,休伊特先生。如果他不好好地照料马鞍,他应该失业。”
“确定哪个小伙子有过错可不那么容易,”休伊特平静地反对说,“而且正处于狩猎期我们可担负不起把他们全部解雇地损失。”
“还有你父亲的急躁脾气,呃?”福尔摩斯说,“梅尔罗斯小姐——就是休伊特夫人——认为她的公爹由于那桩意外事故和安德鲁的受伤而心烦意乱了。”
“是的。他可能极其冷酷地对安德鲁讲话,但是他深深地疼爱着他。我弟弟那天坠马时,我从未见过他那么悲痛。可怜地小老弟团成一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当拿不准我弟弟的伤情时我当然不希望我父亲看到那段毁坏了的皮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梅尔罗斯家的人会请来一个侦探调查一件普普通通的坠马事故。”
“有几件特殊的情况,”福尔摩斯温和地说,“臂如说,你弟弟半昏迷不醒地躺着时你父亲为什么咒骂他?”
“爸爸每逢心烦意乱就咒骂,这一向是他的作风。你永远不会看见他由于悲伤流一滴眼泪;他反而会大发脾气。”
福尔摩斯点点头。“我的朋友华生几乎一样。你喊叫‘爸爸,千万不要!’什么使你那样朝他呼喊?”
这一次爱德华·休伊特似乎吃了一惊。他的反应不太明显——仅仅是他的明慧的蓝眼睛微微眨了眨——但是他的确慌乱了。“我弟弟搞错了。那话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
“啊!”真不可思议,福尔摩斯话中意味深长的含意竟然传达到了一个单音节词上。即使他说了“多么有趣,我决不相信你”那句话,也不可能比他发出的那个简短的声音更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思。然而,由于没有说出那些字眼本身,他让听者得出了基于自己良心的自己的结论。
爱德华·休伊特西鬓微微红了。“我在对你讲的是绝对的真实情况。你的话好像暗示他做了什么有理由受到谴责的事,但是他没有做。我在那儿,而且我相信我弟弟会承认我比他当时更有理智。让我告诉你当时发生的情况吧。我父亲把安德鲁抱在怀里,轮流地骂他呼唤他。突然我弟弟睁开眼睛,像你说的一样大声呼喊道:‘爸爸,千万不要!’接着立刻又失去了知觉。”
福尔摩斯听着这番叙述时点点头,表面上似乎很满意。“安德鲁的记忆一定是捉弄了他。但是你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对于有人打算害他那种想法很敏感了吧?”
“当然,”爱德华·休伊特似乎平静了下来,“总有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医生供给他多疑的胡言乱语。”
“什么使你认为是法辛盖尔医生聘请我效劳的?”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似乎是那么和善的一个老头儿。实际上,直到我母亲失踪他都是我们家真正的好朋友,然后他似乎转而反对起我们。不知怎地他好像为此责怪我们。我相信是他往我弟弟头脑里灌满了那一切幻想。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弟弟认识了很久,久得足以看出他十分容易受各种各样荒谬暗示的影响。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也没有特别有逻辑、善于辨别是非的头脑,在像我母亲失踪那种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更没有那种头脑了。他和她那么亲,而她的失踪又那么神秘,以致他变成了那个卑鄙老头的牺牲品。因此形成了几个小集团:我父亲和大哥组成了认为她抛家出走的小集团,而安德鲁和法辛盖尔则组成了认为她可能被人谋杀的小集团。”
“你呢。休伊特先生?你支持哪个小集团?”
“我倾向于抛家出走小集团。”休伊特严肃地说,“但有一个限制条件。我父亲和哥哥认为安德鲁帮助我母亲逃跑了,或者至少,他知道她在哪儿。这我知道并非如此。我弟弟对事实和幻想有时可能很难作出正确区分,但他根本不是撒谎的人,而且在她离开我们以后他遭受的极度痛苦绝对不是假装的。他真的相信她死了,可怜的小伙子。”
“他的论据是,”福尔摩斯说,“她那种性格的人根本就不会离家出走。”
“我确信我们都这么认为,但是她时常去伦敦,表面上是去看她母亲和妹妹,但她很可能是在不引起起家里任何怀疑的情况下在那儿与什么人相会。我母亲是个很温柔的人,但是在好多事情上她都有自己的一定看法,而且她时常公然反抗我父亲。谁说得清一个女人真的在想什么?”
“不过你不知道有什么确定的爱慕者吧?”福尔摩斯说。
“我当然知道一个,”休伊特断言说,“不过她并没有和他私奔,那是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老法辛尔爱上了她。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你不是由于没有别的事占据你的注意力就打算调查我母亲这件事?”
“我发现那种情况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福尔摩斯承认说,“真遗憾三年前没有和我磋商。”
“我看结果也未必有什么不同。恐怕,她一去不复返了。从前我想如果孩们知道了真实情况就可以补救了,但是现在——哦,我们经从最痛苦的境况中摆脱了出来,假定你发现了她在哪儿,我父亲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每一个人会是什么感觉?唠唠叨叨地反复谈这个题目,折磨我们自己,并不会使事情有任何好转。你简直想象不出在她出走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安德鲁经受了多么剧烈的痛苦。他现在才从震惊中摆脱出来——这肯定要归功于简的亲戚,华生医生。我想她是你的亲戚,华生医生?”
我急忙回答:“哦,是的。”我本来想当场就讲了实话,但是给简·休伊特带来更多的耻辱我简直忍受不了。我看见福尔摩斯吃惊地挑起眉毛,但是他未做出任何纠正。
爱德华·休伊特似乎接受了我的话。“你知道我怀疑过,因为我不记得在婚礼上见过你。”
“没有,我不在那儿。”我掩饰说,“我有事离开论教。临时接到通知走不了。”
“进展的速度使我们的确始料未及。”福尔摩斯弄虚作假地补充说。
“不过,”我说,“毫无疑问他们非常恩爱,听到全家人中你是唯一不反对这门婚姻的我很高兴。”
“一旦我看见他们在一起的情景我怎么能反对呢?”爱德华·休伊特明显地带着感情说,“那时我看见我亲爱的弟弟在悲伤了那么久以后又轻松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