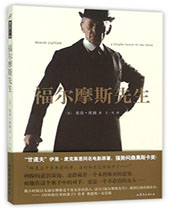福尔摩斯和萨默塞特狩猎-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担心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许上校的妻子终究是遗弃了他。也许她确实被那个老医生想象的过路陌生人杀害了。然而我不能接受这些解释,在听了休伊特的说法以后就不能接受了。就在他母亲的案子中采取行动而言,真希望我知道他隐瞒着什么,为什么隐瞒,在他母亲的案子中这似乎妨碍他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我们已经证实他隐瞒了他觉得会对他哥哥有危害的情报,不过那和他母亲能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相信爱德华·休伊特是谋害他母亲的凶手,我不相信他会保持沉默。”
“难道那么肯定罪犯是休伊特家的一个人?”
“不。”福尔摩斯回答,“不过如果不是我猜疑的那个人,对我们来说可就要丢脸地回到伦敦了。”
“你能告诉我你怀疑的是谁吗?”我问。
“不,华生。我一丢下你们单独两个人管保休伊特会问你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委托人以为他了解了案子的答案,我可不愿意想象那种后果。就了解这样的事情而言,他的性情未免太容易激动了,不管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否正确。”
“那么,你相信休伊特对你讲的一切喽?”
“我相信他确信他说的话是真实的。我意识到关于那张字条你不赞成我逼问他。我知道那使他心慌意乱。”福尔摩斯摊开双手,“不过他的反应在我看来是十分真诚的。要么是那样,要么是他妻子离开他们时他登上舞台了。而且,他的话听上去是真诚的。记得他多么清楚地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他遭到打击以前的事记得非常清楚。当夜晚的事件发展下去时他的记忆力受到了损害。那是既受到严重震惊,又因脑袋受了伤而经常发生的情况,你不同意吗?”
“我一时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休伊特的话,”我责备说,“既然你似乎愿意相信他的话,似乎又认为他的记忆一定有错误,那么你认为他什么地方搞错了?”
“我没有说他错了,”福尔摩斯说,“我说他观察得不够,而且当他声称他震惊得看不大清楚了时我相信他的话。我和他萍水相逢时,我以为他是一个傻瓜,但是我已改变了看法。我应该了解任何能创作出那种作品的人一定不是虚有其表。喂,华生,这儿有一个具体的情报,对你会有一些实际用处。昨天我和维克斯先生,那一群猎狐犬的主人,进行了一场很有价值的谈话。他对我讲今天的狩猎是为了庆祝杰拉尔德先生的生——因此,更稍微精心制做的早餐代替了日常的集合。这是这个季节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农村居民会倾巢出动跟随着那群猎狗,这将给一位顾问侦探构成完美无缺的掩护。维克斯先生对我说,在恩德山集合时,预料他将在小山北边取得第一个掩蔽处,假如风向有利,就象今天的情况似的。你观察过那个地方吗?华生,就在小河那边?”
“右边有一片树林吗?”我立刻回答。
“对啊,”福尔摩斯微笑,“亲爱的朋友,在户外活动显然是你适应的环境。很好。狩猎会朝那个方向出发,你和托你照管的人一定要在这儿等着,直到你看见所有的追随者们都渡过了小河;然后你和休伊特下山回村就安全了。理想的是,你们在路上不遇见一个人。万一你真的遇见什么人,就运用你的最明智的判断力,但是任何人也不要相信。”
我们听得见下面预料到的连续不断的声音:骑手们和坐着马车的人们相继到达,当所有人都进去吃他们的丰盛早餐时那种相对的寂静。我想象着咖啡香味一直飘送到我们的隐蔽处。终于,当他们准备动身狩猎时,我们听见了一群猎狗和一群马的集合声。当我们自己的坐骑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时,它们紧张不安地移动着。一接到这样的临时通知。我们就被迫骑上那两匹马,它们打猎的日子还要拖延很久,但是,即使如此,它们似乎仍然渴望参与。
一会儿以后我们听到一个单身骑手走近的声音,安德鲁·休伊特骑着他那匹红棕色骏马出现在眼前。他的脸就像福尔摩斯述说的那么憔悴,但是他的态度却异常愉快。一条长腿轻而易举地从马鞍前鞒上摆荡过去,他轻轻地落在了地上。
“没有人看见我,福尔摩斯先生。”他宣布说,“我能肯定。我就按照你说的办了。我把手套藏在帽子里,然后告诉内德我非得回去找手套。因为戴维和父亲不跟我讲话,我就不必欺骗别人了。我告诉内德不要等着我——那很对,不是吗?”
看到我们的委托人在实行他的小小骗术上那种明显的欢乐神情,连福尔摩斯都笑了起来。“干得好,休伊特。现在,你明白你必须和华生一起走,和他待在一起,直到我回来。”
休伊特点点头,于是他和那位侦探换了衣服。当他看到福尔摩斯小心地转移过去的手枪时他皱起了眉头,“我只希望了解其余的事。你甚至不告诉我你预料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不打算用那支枪对付我家里人吧,是吗?”
“我不打算用它对付任何人;它只是为了防御。”福尔摩斯断言,“华生也武装起来,如果我估计错了危险的来源。他会尽力保护你安全。”
“危险?”休伊特问,“出自谁啊?福尔摩斯先生,我有权利了解。我没有吗,华生?难道我没有权利了解吗?”
“照着我对你说的办。”福尔摩斯用不容胡闹的声调说,“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不等回答他就骑上格伦纳迪尔,策马驰下崎岖不平的斜坡。休伊特和我一直注视到骑手和马消失了踪影。“要想说服你我们应该跟随着他,而不是撤退。”休伊特随随便便地低声说,“有多大可能性?”
我不作回答,却紧紧地盯着休伊特。
他微微一笑,耸耸肩膀,“啊,好吧,骑着这几匹骨瘦如柴的老马,即使游戏,也没有希望。福尔摩斯先生一定是为了不让它们阻挠他的计划才挑选了这几匹马。看看这匹马;我敢打赌它比我的年纪还大。”
“不必为马担忧,”我责备说,“它们会妥当地把我们驮回村里。”
“对我来说这些马镫太短了,”休伊特抱怨说,“哦,我明白了,那么,这一定是你那匹马。我要骑福尔摩斯先生骑的那匹马;他和我身量几乎一样高。我待在这儿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简直令人恼火.我们至少可以到山顶上,观看一下骑手们吧?他们都会向前看着那群猎狗;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我怀着几分疑虑同意了,旋涡水池似的一样猎狗在一群长腿野马前面漂了出去,确实非常壮观。在灿烂的朝阳中,一匹匹红棕色马像一枚枚新硬币一样鲜明光亮,而一匹匹栗色马对照之下闪烁着自己的色彩,到处有一些灰色、黑色和黄色的马增加到优美与力量融合为一体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耀眼光彩中。穿着红上衣的主要人物们骑马走在前头,根据那匹栗色雄性骏马和骑马人的军人姿态,我辨别出是上校。后面是穿黑衣服的其他骑手们,接着来的是步行的、坐着各式各样运货马车和四轮马车的其余人物,他们希望看看打猎的情景,即使自己不能参与。
跟随着这支移动着的队伍的一个单个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福尔摩斯绕过小山,为的是他好像别人一样是从同一个方向来的。他那匹马的从容慢跑很快就使他到达了距离那一伙人五十码左右的范围之内,在那儿他把速度放慢成不静止的慢步。在我旁边的安德鲁轻声笑起来。“格伦纳迪尔不喜欢落在最后,看看福尔摩斯先生是怎样用力勒住它的。不过,就它来说它已经走得很好了。我喜欢看见那群猎狗吠叫着追猎。但是我们却坐在这儿,藏着。华生,我猜想福尔摩斯先生对我评价不高,是吗?”
“我认为他对你的尊敬一直在增长”我回答,“你来以前他刚刚对我这么说了。那有关系吗?”
“那对我有关系。”我的同伴承认说,“那是和一个人非常密切的接触,把你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告诉他。我对你们讲了我仅仅对简讲过的事情。我对你并不那么在乎,因为我知道你尽力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华生,但是福尔摩斯认为我是一个白痴。我想,在某些方面我是的。倘若我自己有一点头脑,几年前我就会理清这个谜团。现在福尔摩斯仅仅几天就做到了。”
“当我们自己与歇洛克·福尔摩斯比较时,我们大多数似乎都很迟钝我表示同情,“况且,你当时受了伤,痛苦不堪。福尔摩斯没有这些不利条件。”
眼睛依然凝视着下面的猎队,安德鲁·休伊特漫不经心地问:“福尔摩斯真的认为我需要一个保镖吗?”
“他不让一个代理人遭到意外。”我回答。
“你有一支手枪吧,那似乎可能造成损害。我从来没有放过枪,虽然我用鸟枪还是把好手。据说,是眼睛使人成为神枪手,而我有非常锐利的眼睛。你是个好射手吗?”
我谦虚地微微一笑,承认了我的技术。
“不过你不会开枪打我吧,是吗?”休伊特大笑着说。他的举止突然变了,凝视着下面的景象,“老天爷呀,他们在下面那儿干什么?”
我猛地转身俯视那种五光十色的景象,但是,就我辨别出来的,福尔摩斯仅仅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跟随着那一伙人。在我看到的下面那些东西中,分辨不出任何值得注意的事物。正好在我后面山坡上传来的践踏声是我获得的我给当傻瓜耍了的最初暗示。到我站起来的时候,休伊特已经跨上一匹马,而且,我还没有到达另一匹坐骑那儿,他就已在下面漫长斜坡的半路上了。更糟的事发生了:当我把脚尖放到马镫上时,整个马鞍滑到了我脚边的地上。原来休伊将以调整马镫皮带为借口,反而设法解开了马鞍肚带。我听见他从下面大声呼喊:“对不起喽,亲戚!”
要赶上他的唯一机会就是毫不拖延地跟着他,因此,我狠狠地咒骂了一声自己缺乏警惕,就爬到马的光背上,把脚后跟插到它的侧腹。那个牲口朝我扭过头,一只大眼睛向后转动,好像对我不要通常的装备骑马这一选择表示怀疑。我又轻轻踢了踢,抖抖缰绳,使它确信我是认真如此的,于是我们开步,跌跌绊绊地尽可能飞快地追赶上去。为了保住宝贵的生命,我紧紧地稳稳坐着,以免栽下斜坡。
安德鲁·休伊特已经到达平地,催马能走多快就走多快。除了他有马鞍骑马这一有利条件以外,他胯下还有一匹较好的马,他还是一个超级骑手,即使我们势均力敌地骑着马,他的速度也会使我的能力经受考验。以他在我前头加快奔驰的速度,要想完全逃避开我,仅仅是几分钟的问题。我掏出手枪,想把他的马打瘸,但是我担心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瞄不准,于是决定不扣扳机。
当休伊特消失在他右边长满树木的区域时我勒住我那匹动作迟缓的马,停下来思考,我为自己半个小时之内就把托我照管的人丢掉而羞愧得头脑发晕。要追回休伊特可决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即使休伊特实际上没有遭到任何伤害,在结案时我也要面对与福尔摩斯会见的凄惨景象。倘若最糟的事发生,我怎么能再期望我的朋友信任我?更令人忧郁的是想到和简·休伊特见面的情景。我想福尔摩斯说我几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了她的亲戚是对的。如果我给她带去会使她伤心的消息,我怎么忍受得了呢?既然我没有希望赶上休伊特,听听他去哪儿。我想我最好还是回到会使我纵览乡村风景的山顶。他想和福尔摩斯一起跟随着猎队似乎是最符合逻辑的;或许从那个有利地点能够看到他。如果那事失败,我至少可以追上福尔摩斯,警告他的计划化为泡影了因此我鞭策那匹行动迟缓的马登上了山顶。
正如福尔摩斯预告的,猎队前进到小河那边的掩蔽处。我可以看到那样猎狗在遍地岩石和荆豆残梗中间广阔地排开,而猎手们就在它们后面骑马缓行,等待着真正的狩猎开始。但是极目远眺我却分辨不出那匹鲜红骏马和它的瘦高骑手。福尔摩斯在哪儿呢?
这时我眼角看到了一场活动。在远离猎队的地方,四匹马穿过开阔的牧场,朝着相反方向在全速奔驰。一匹马——那匹红棕色马——在另外几匹前面奔跑。我不必仔细观看就了解到福尔摩斯遭到了休伊特上校和他的两个大儿子的追击。转瞬间,尽我那匹驮得动的装备不良的马匹奔驰的速度,我顺着小路冲了下去。
福尔摩斯迫在眉睫的危险代替了我寻找休伊特的心思。如果休伊特家其余的人是案子中的恶棍,安德鲁·休伊特跟随着猎队就很安全了,而福尔摩斯和我就在几里地远的地方对付他的敌人们。
追踪这四个人并不比跟踪那个难以捉摸的美术家容易。我开始意识到为了人类的舒适发明马鞍的重要性,但是,老实说,我倒没有被骑光背马吓倒,却被我显然不可能赶上前头的骑手们吓慌了。我在潮湿开阔的地面上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但是我看不见他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而且我担心我可能提供给福尔摩斯的任何帮助都为时已晚。但是我奋力前进,多半是因为我想不出更有效的事可做。
我一定是飞驰了一英里多地,这时我走的小道突然转向了密林中一条大路。我不得不缓缓行走,尽量低着头躲避悬垂着的奸滑树枝。这时,没有警告,我突然闯进了净是我追寻的人的一片空旷地。在我面前呈现出十分凶险的场面:都下了马,福尔摩斯在中央,戴维和爱德华·休伊特一人在他—边,紧紧地揪着他的胳臂预防他逃跑。老上校面对他们三个,他拿着的马鞭吓人地悬着但是我仍然感到一阵宽慰掠过我的心头;福尔摩斯活着,而且显然还未受伤。
留神倾听了一阵我的马蹄连续敲打声以后,当我勒马停住时,那一阵突然的沉寂是凶险可怕的。当我完全看得见他们勒马止步时,福尔摩斯对我怒目而视,我知道这与我未能把安德鲁·休伊特送回村里有关。这完全是这个卓越人物的特性,虽然他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除了恼怒没有毫不含糊地执行他的命令以外,他没有表现任何情绪。无论如何,我不想让他长久处在危险中;下一瞬间,我的手枪就瞄准了他的攻击者们。我本来更希望下马,瞄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