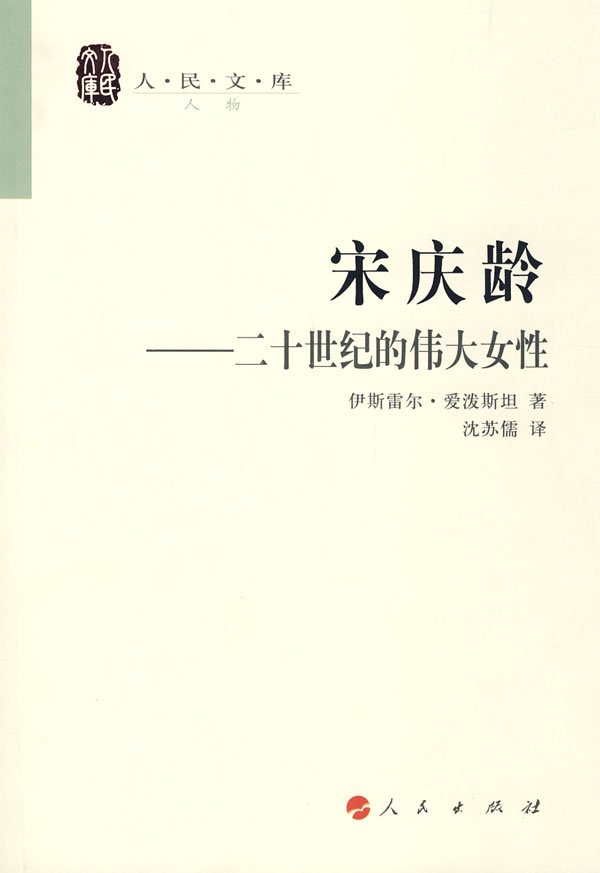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加恩惠或影响的工具。它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共同反对法西斯敌人的平等关系。
同时,在中国国内,它反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把持同外国救济团体的联系。它认为这个政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只是压迫人民、让人民挨饿;这个政权对侵略者的战斗不多,对那些正在战斗的人进行的干扰却不少;这个政权在分配资金和物资时对于那些抗日最积极的部队加以歧视,或者干脆排斥在外。更坏的是,国民党官员们经常盗窃救济物资(甚至分给他们自己部队的物资也不放过),并在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谋取私利。
因此,保盟——它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自救”——提出,由它自己来担任分配救济物资的受托人,保证由它经手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来进行分配;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一定严格地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
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卡尔逊写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①
①爱泼斯坦普《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141—142页。宋庆龄的引语见《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1943年9月18日于重庆),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0页。
在她的领导下,保盟对于一切要它放弃、减少或不公开支持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压力,不论明的暗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概加以抵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区域,保盟帮助建立和扩充国际和平医院,赞助儿童保育院(收养孤儿和父母在前线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建在延安窑洞中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美国洛杉矶华人捐款设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培养为抗战服务的文化工作者的,对它们的援助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也是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
宋庆龄和保盟以最直接的方式——并肩战斗来促进国际团结。这在保盟对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的支持上表现出来。几年前,也是由于宋庆龄的介绍,美国医生马海德参加了中国红军的医疗工作,成为保盟在延安的通讯员、同白求恩大夫(在华北前线)的联络员。
在印度柯棣华医生接替白求恩大夫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之前,曾经还有一位人选,即捷克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吉斯赫①。他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但国民党不许他去解放区。像他这种情况的——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医务工作者、愿意去中国解放区工作而未能成行——还有约20位医生,属各种国籍(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奥地利)。后来他们被分配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服务队,在国民党控制的抗日前线工作。作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以统一战线的精神,提供了优良的服务。
①见迈克尔·布兰克福着《高大的美国佬》(英文),第260页。
保盟每遇到一个障碍和挫折——正如整个统一战线所遭遇的那样——宋庆龄总是鼓励大家付出加倍的努力并加强宣传,以使海外对战时中国的复杂现实有较好的了解。
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保盟在促使全世界了解真相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如上述。在行动上,保盟继续给这支已被正式宣布“解散”的新四军提供医疗服务,新四军也加强了它的对日作战。当时所用的办法之一是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小心谨慎地采购医药供应品,然后通过巧妙的地下活动,偷过日本占领区。为此目的,有一个包括中外人士的保盟支持者小组在上海工作,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小组的据点是耿丽淑所住的公寓,耿是宋庆龄的朋友、保盟美籍会员、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大夫有时秘密地来往安排,沈还曾前后三次赴香港,向宋庆龄当面汇报。
在香港本地,由于宋庆龄的独特地位,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以保盟为中心的统一战线。作为孙逸仙夫人——即使小学生也都知道她是“国母”——她不可能轻易地受到哪怕是最恶劣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直接攻击。尽管常有一些见不得天日的间接的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但由于她为人所知的品格和个人的非凡魅力,结果受害的往往是制造这些流言的人自己。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五花八门,都认为能同宋庆龄交往是自己的殊荣。
但是,也还是由于她的罕见的政治技巧和策略,才可能使这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被用于她所选择的事业。
宋庆龄要求这一统一战线应该在保盟的实际救济工作中得到反映。保盟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为援助被封锁的解放区而奋斗,另一方面也毫不迟疑地帮助任何地方的项目,只要它们对民族抗战有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区域都开展工作。还有上面刚提到过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服务队也是在国民党区工作的。这同国民党对任何它所不能控制的东西一概排斥是明显的对照。
在香港,宋庆龄征集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捐赠。他们之中有中外籍的官员、银行家、工商业家。应孙夫人的邀请常在保盟活动场合出现的有港督罗富国爵士。上面已经提到捐赠新式救护车(带手术间)的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挪威船主埃里克·莫勒(他在远东有一支商船队)也捐赠了一笔巨款。
至于香港的中国富人,一位前保盟会员曾幽默地回忆起他在为“工合”筹款的一次聚会上所见的一幕:
“廖梦醒的母亲(直爽的何香凝)拉着何东爵士(香港的中国首富)女婿罗文锦的右手,硬是逼着他写下捐款的数额。其他名人排成队,挨个来,为工合筹到了一大笔钱。”①
①吉斯赫医生的弟兄伊刚·爱尔文·吉斯赫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左翼记者。
这可以作为当时流行的爱国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体现——廖老太太“有力”而她所“捕捉”的对象“有钱”。但实际上他们所以觉得难以拒绝是因为宋庆龄在场。
本地富裕人家的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国民党要员的夫人们都自愿为保盟义务工作——多半是因为能同孙夫人一起工作是件光彩的事。她们捐赠或帮助征集许多古董字画,由保盟委托美国和法国的友好团体拍卖,得款资助保盟的救济项目。不幸的是,美国不同意给这批东西免除进口税,虽经罗斯福总统夫人接到宋庆龄等呼吁后亲自出面说项,也未奏效。法国虽准许免税,但它自己不久也打仗了,这批东西没有卖掉,存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里,后经顾维钧大使夫人的努力,才又返回香港。
香港中国首富何东爵士的女儿伊娃医生(何娴姿),在保盟做基层工作,非常勤苦。国民党右派要人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帮助码放和分发供应品,劳动也十分辛苦。在这样的劳作中,宋庆龄自己总是带头。看到高个子、脸色白皙的胡木兰同小个子、黑皮肤的廖梦醒和宋庆龄在一起干活,真是有意思,因为胡汉民和廖仲恺(她们两位的父亲)曾经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敌。为了抗战中的民族而实现这样广泛的团结,全由于宋庆龄创造了必要的气氛。
坚定的原则性并没有使保盟陷于孤立。这一点在宋子文退盟造成的危机中可以看出来。她很快就筹建了一个由中外赞助人组成的新机构。中国方面有孙科、冯玉祥将军;国际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鲁、爱德华医生(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前队长),美国的保罗·罗伯逊(伟大的黑人艺术家和自由战士)和赛珍珠(中国出生的女小说家)、甚至还有克莱尔·布思——《时代》杂志大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想到后来他们所持极端的“冷战”立场,她的参加似乎不可思议),德国的托玛斯·曼(著名作家、这时因受希特勒迫害流亡)。
在这个“远东慕尼黑”看来临近难以捉摸的时期,宋庆龄拒绝了来自外国官方人士的、要她搬进蒋介石在港的一处房子的提议。认为这是无原则的。向她提议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一寇尔爵士,她同寇尔大使私交甚笃,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才要大使出来对她施加压力。她不客气地加以拒绝有可能使保盟在英属地香港的处境困难。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她和保盟没有缩手缩脚,而是继续利用每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避免同港英当局的关系出现不必要的紧张。随着英日矛盾的尖锐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双方的关系又趋改善。
尽管同香港高层进行合作,有了分歧还是需要指出。不过,宋庆龄不是用直接辩驳的办法,而是在自己发表公开谈话时有针对性地阐明观点。1941年中,英国已与德国交战但尚未与日本开仗,香港总督罗富国——他对保盟一般说来是友好的——为赞助保盟的一次募捐活动,说了这样一段话:
“遭受自然和人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难者,以及这些无助的人的要求,是值得大家支持的,这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
在同一个场合,宋庆龄在她的讲话中有意识地用了另一种调子——她不是把中国人民说成仅仅是“受难者”(当然更不是“无助的人”)而是战士,援助这些战士是对共同敌人法西斯主义的打击:
“这个月在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不顾敌人轰炸的威胁,却在为争取中国的医药救济经费而展开一个巨大的……运动……这个星期在菲律宾,也正在举行一个类似的、纪念中国抗战四周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正如我们在香港的一样,用募集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来帮助中国的斗争。”①
①许乃波致本书作者,1987年11月8日。他是一位工程师,为保盟委员会吸收为委员,任技术顾问。
在扩大保盟基础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宋庆龄善于交私人的朋友,并用她的关心和温暖使友谊长久保持下去。在美国志愿为保盟募款的热心人士中有一位安妮·马尔·斯利普,宋庆龄和她是从她们都还是女学生时起就相识的。她从没有因为遗忘、怠慢而失掉过一个朋友。同她通过信的人都可以证明,她不管怎么忙总是当天回信,最晚也不过晚两三天。
她从不要求或期望朋友或相识的人很快同意或接受她的观点,而是去顺应他们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那些较为迟缓或不愿改变看法的人,她也不会看不起他们。有人一变而敌视她所坚持的一切原则、也有人试图为自私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她所慷慨给予的友谊——她只同这样的人断绝交往。她对林语堂博士就是这样。在30年代,林曾是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事;40年代他成了美国畅销书的作者——后来又成了一个说话刺耳的发言人。他从美回国时大事宣传,说他要同“吾土与吾民”(这是他那本最出名的著作的书名)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正是为了这一点,宋庆龄在他途经香港前来访谒时接见了他。谈话开始时还很热烈,她向他介绍了保盟的工作。这位现已名利双收的人物对保盟没有表示任何鼓励,更不用说支援了。相反,他倒提出要请保盟帮他的忙,把他那部从美国带来的崭新的小汽车放在保盟的医药供应车队里运往重庆,这样可以免付关税。
宋庆龄马上问道,“我们可以把医疗设备装在你的车里吗?”
林回答说,最好不装,因为怕弄坏车里的坐垫等等。说话时脸色都变了。
谈话到此就谈不下去了,即使林语堂以他的礼仪和机智也没能挽回。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宋庆龄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看了令人难忘的、充满嘲讽的一眼。
但对保盟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她总是那样热心和民主,使大家感到同她是平等的、感到很自在。保盟每周开一次例会,开会的地点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总部十分拥挤的办公室里,桌上堆满各种文件材料,地板上还常常堆着小山似的供应品,准备分类处理。但会议的气氛非常亲切、随便。保盟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阶层,年龄也不同(1938年时本书作者才23岁,是最年轻的)。宋庆龄主持会议,但从不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而是让所有在场的人(不管是委员会成员、还是职工)都发表意见。会快结束时,她说说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后做结论的架势。谁有话还是可以说,即使说的同她相反或有什么新点子,她从不表示不高兴。谁都想不起什么时候听到过她提高嗓门说话。她的话总是很清晰、务实,常常提出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工作日程,而不是只说点意见或判断。
如果说她在保盟活动中作为嘉宾接待的都是一些显要人物,那末到保盟总部来并受到欢迎的则都是普通人。中国工会工作者来送个人或集体的捐款。还有外国工会工作者——美国或其他国家船上的海员每次送来的捐款少则几十美元、多则一两百美元,都是在来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们募集、或在出发港口的工会会所里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约翰·科米尔的美国海贝,每次他的船到香港,总要送捐款来。这样的客人总要坐下来聊一会儿。他们听到敌后游击队斗争的事迹,都很有兴趣,临走总要热心地带一些《保盟通讯》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给船上同事和朋友们看。
宋庆龄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是理论、也不是辞藻。这种感情是直觉的、强烈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与群众接触而产生的(特别是在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省港大罢工和农民运动中)。
本书作者就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件在香港发生的小事。她要本书作者陪她在九龙码头上迎接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本书作者迟到了——这是老毛病——发现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四周是码头工人们在忙着搬运和安装缆绳、滑轮等等碇泊和卸货的设备,就赶紧向她道歉:“真对不起,让您一个人在这儿等。”她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