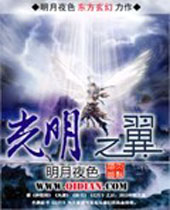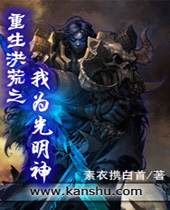光明王 作者:[美]罗杰·泽拉兹尼-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了上述作品之外,泽拉兹尼还有一部备受推崇的宗教题材科幻长篇,那就是出版于1967年并于1968年获得雨果奖的《光明王》(Lord of Light)。
三
“新浪潮”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刻意求新,抛弃传统科幻套路,向主流文学靠拢;作品以意象性、隐喻性和心理性为主,对人心理的重视超过了科技发展的重视;带有强烈的嘲弄或悲观主义倾向;发掘了科幻文学的新领域——这其中就包括了宗教题材。
“新浪潮”运动在提高科幻文学地位、拓展和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却很快陷于没落,不过风行了十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它丧失了传统科幻的特色,远离了广大的科幻读者;而且基于某些文学形式上的探索,使得其作品文风晦涩,叙述零乱,甚至不知所云。因此假装喜欢“新浪潮”风格是一回事,但真正读懂又是另外一回事。
说句老实话,对于《光明王》,一上来我就没看下去,甚至颇有些摸不着头脑。感觉像是一个离我很远的宗教故事,同时又像是一部架空历史小说;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它更像是一篇奇幻小说——恕我直言。
事实上我对于一些西方奇幻作品不感兴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中没有提到科幻读者所熟悉的钢铁与塑料之类技术,而是因为我对于那些文化背景和设定不甚了解;而对于不了解的东西,我宁可不去看它的热闹。
从大的角度来说,《光明王》也应该是一个用技术来诠释宗教的故事,而类似的故事科幻读者也应该有所了解。比如特德〃蒋的《巴比伦塔》——作者描述了一个在现实中建造一座不断上升的高塔的故事;比如A。C。克拉克的《星》——作者用一种极为伤感的笔调描述了一个文明被大自然无情击毁的时间与人类神话传说的时间相巧合的故事。而在《光明王》当中,作者除了用渲染和铺张的手法展现出一种宏大和眩丽之外,也使用了一些技术性的叙述诠释了类似轮回之流的概念。
面对《光明王》,我无力进行“解词”一般的工作。这首先是因为我对于这部作品也有很多直观的不解之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它赖以存在的宗教文化基础过于深涩,距我甚远。
印度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了解和把握的神秘国度,到处笼罩着浓郁的宗教气氛。基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印度人所信奉的宗教极多,而且同一宗教还有诸多教派。这一局面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印度的历史也被笼罩在一层厚厚的迷雾当中。古代印度人不注意记述自己的历史,而是喜欢讲述神话故事,这样一来,后世历史学家就只有从神话中发掘和考证印度的古代历史。因而读懂这部《光明王》,也需要先跨越印度神话、印度宗教史以及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诸多深奥繁杂的门槛。
在印度,婆罗门教即印度教最为流行,而它的那位王子后来创建的佛教却墙里开花墙外香地覆盖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因而各种概念的相互借用使得《光明王》一文中的叙述更为混乱。比如《光明王》在一开始所提到的阎摩(Yama),就应该是印度神话中的那位死神,据说他是第一个死去之人,首开死亡之路,从此万众追随。而从第二部分开始,故事似乎稍微明晰了一些,因为那位创建了佛教的佛祖释迦牟尼以悉达多王子的身份正式出场了。随即他们回到了现实世界,并开始干涉它的进程。再往后,众多的人物角色开始铺展林立开来,慢慢地各种神灵也都出全了,诸多其他的教义更是纷至沓来,不但容纳了印度教和佛教,还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甚至还附带涉及了很多其他毫不相干的信仰或理论(诸如马克思主义!)。不了解这些宗教文化的背景,就很难用世俗的语言重新言说这部作品。
全文共分为七大部分,每一部分的开篇都列有简述并引经据典——这可是真正的引经据典!而在这些理性的阐述之外,作品的故事情节似乎只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叼陪末座式的,因而我不清楚是否有人真能看得明白。总之我在阅读了至少三遍之后,也只是大约理解了其中一些历史进程的片段,感觉似乎是在文化领域发生了某种革命,并为最终催生“光明王”做好了理论铺垫。
由此可见,光有原文的注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诸如“莎丽”之类的词汇很多读者都知道,但文中还有更多的东西很多读者不知道。
四
如前所述,问津“宗教题材”是“新浪潮”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颇具革命性的一步(另外一步“性题材”当之无愧)。而这一时期科幻文学对于宗教文化的描述,一种是相当激烈的反叛,一种则是稍许和缓的诠释。前者以迈克尔〃莫考克的《瞧这个人》为代表(中译《走进灵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之所以喜欢《瞧这个人》(Behold the Man,1966)这个名字,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直译,还因为这本是尼采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的名字,莫考克如此选择自己的小说名自然有其深意。
《瞧这个人》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宗教。主人公犹太人卡尔〃格洛高尔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患有神经衰弱,因此期望从圣经中寻找慰藉,以解决自己时时存在的困扰。为此他乘时间机器前往公元28年,以目睹耶稣之死,没想到却早到了一年。
格洛高尔首先找到预言家约翰,但结果却他令他大吃一惊,因为约翰居然不知道耶稣其人!接着格洛高尔又找到了玛丽亚等人,而结果更令他吃惊:因为圣母玛丽亚与圣经的记载相距甚远,而耶稣看起来显然不像是一个能够承担拯救人类命运的人物。
格洛高尔为此感到极度失望,但还是决定暂时住下。因其通晓医术,拥有问诊治病的能力,于是悬壶济世,开业行医,治好了很多人的疾病,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圣人。而作为一个熟读圣经的信徒,格洛高尔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断。因而接下来,他开始率领着人民向耶路撒冷方向前进——事实上,这时格洛高尔已经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耶稣的使命。
当然格洛高尔也知道,自己这些行为的结局是什么——被出卖,被逮捕,并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莫考克就是以这样激烈的方式,阐述了一个“反宗教”的故事。
而泽拉兹尼的《光明王》,显然属于后者,即所谓“稍许和缓的诠释”。
在这个由所有的神灵构成的遥远世界里,众多的出场角色看起来都与凡人无异。但是他们灵魂不朽,法力无边,集体演绎着一出出看似平凡实则惊心动魄的故事。作者试图在平淡的叙述中向读者传递这些一些信息:掌控着这一奇异世界规则和命运的神灵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究竟是用怎样的方式改造了一个世界并使那古老的东方宗教和神话在其中得以重现?
从部分叙述的手法上来说,泽拉兹尼在《光明王》中成功地取得了一种类似讲经的效果。但在整体叙述上,则有一种信马游缰的流畅,有时候我们也习惯把这称为“玩弄感觉”——我不知道国内作者要是如此这般地写上一篇,会不会被读者质疑甚至谩骂。
也许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只是在于——阐述了无名的重要,阐述了梦境的真实。
其实宗教也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只不过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并不接受这种解释而已。但也有很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这完全取决于你是从哪种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
有人在网上发文询问:有什么样的图书专门讲述因果律、能量守恒或者物质不灭之类的普适定律;有人回答他说:大学物理;但马上就有人发文声称:大学物理最讲不清楚的就是这些事情了。
所以我宁愿选择另外一个人的回答:般若波若密多。
我想,假如那个人用其他一些宗教教材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起到的效果也应该是差不多的。
五
勿庸置疑,从作品上来看,罗杰〃泽拉兹尼应该算是一位更偏奇幻的作家。
近些年来,科幻文学和奇幻文学有一种明显的融合趋势。有人为此担心,有人为此不悦。事实上这些年来奇幻文学对科幻文学的冲击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一些“正统”的科幻迷对此甚至痛心疾首。
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科幻文学与奇幻文学融合的起点都比这要更早,而不是自“哈利〃波特”获得雨果奖才开始的。事实上很多科幻作家同时也兼写奇幻作品,并且名气极大。而科幻界一直推崇的星云奖,根本就是“美国科幻与幻想作家协会”颁发的奖项,并不排斥奇幻作品,因而发给奇幻作品也属天经地义。
很难说这种融合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在童年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
文明的前进,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强度的加大,都给人一种试图逃避责任返归童年的渴望。而这一特征的表现之一,就是使得人们在阅读和观赏文艺作品时,更注重的是其娱乐功能而非审美功能。人们不喜欢在阅读和观赏的同时不愿过多地思考,因为对简单快感的享受比对深邃哲理的思考来得更为直接。
当然,这并不是说奇幻阅读比科幻阅读的趣味更趋近于童年。奇幻作品也有其独特的背景设定,也有其独特的审美取向,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没有设置现代科技这一门槛。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道门槛,阻隔了不少人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对科幻作品望而生厌,敬而远之,在科幻作品面前畏缩不前,知难而返。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科学研究本身也不再处于那样一个浪漫的英雄年代,已经更为职业化和专门化,不再那么直观,不再那么神秘。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已经从一种神圣的向往,沦为实现其幸福生活的一种社会基础。
但从一个更为博大的角度来说,这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幻想文学至少还实现了愉悦读者的功能,尽管它远离先进的科技。这就好比文学本身:战争与灾难也许能成就更好的文学,而假如在和平和安全的环境中文学丧失了某种品质,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去发动战争或制造灾难,以此来迁就文学的发展。
事实上任何领域的发展,都不仅仅是理论者的功劳,都离不开具体的实践者。有什么样的成就和效果,就有什么样的潮流和标准。对于幻想文学而言,究竟是科幻文学还是奇幻文学更领风骚,同样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无论如何,只要幻想文学有所发展,就是为构造人类精神遗产做出的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