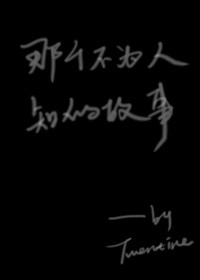坦德莱奥的故事 作者:[英] 伊恩·麦克唐纳-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
《坦德莱奥的故事》 作者:'英' 伊恩·麦克唐纳
导读
这是个充满同情和力量的抒情故事,讲述了在未来,被外星入侵者逐渐吞噬的非洲大陆上一个年轻女孩的成长经历,并描述了入侵者把占领的土地改变成了富饶、陌生、难以想像的世界。这个巨大的改变还延伸到了人们的生活,他们在入侵者引导下发现了自我……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唐纳1960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爱尔兰,现在贝尔法斯特生活、工作。
伊恩·麦克唐纳是个雄心勃勃、大胆的作家,他涉猎广泛,具备丰富卓越的才华。他的第一个故事在1982年发表,之后他的作品屡次出现在《交叉地带》、《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新世界》、《巅峰》、《其他伊甸园》、《惊奇》等杂志上。1985年他获得了约翰·W·坎贝尔奖的提名。1989年他的小说《荒凉之路》获得了轨迹“最佳小说”奖。1992年他的小说《清晨之王,白日之后》获得了菲利普·K·迪克奖。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小说《蓝色六号》、《心、手和声音》、《最后的咖啡》、《愚人的祭品》以及广受好评的《进化的海岸》,另外还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帝国梦》和《用舌头说话》。他新近出版的小说《基里尼亚》和短篇小说《坦德莱奥的故事》都是《进化的海岸》的续篇。
第一章
我的故事还得先从我的名字讲起。我叫作坦德莱奥。我出生在这——基奇奇。这让你很惊讶吧?这个村子已经变了很多,现在就算是土生土长的人也认不出它了,但名字还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事物的名字都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们能保存下来。
我出生在l 995年,是在傍晚前的晚餐后不久生下的。坦德莱奥在我们卡伦金语中的意思就是:傍晚前刚吃过晚餐的时候。我是圣约翰教堂牧师的大女儿。妈妈后来的两次怀孕都流产了,最后在父亲的祈祷和教区居民的祝福下,妈妈在1998年生下了我的小妹妹。我们都叫她小蛋。那时候政府正提倡减少人口,父亲觉得作为牧师应该成为教民的榜样,所以妈妈就生了小蛋和我两个孩子。
父亲平时管理着五所教堂。他经常骑辆红色山地摩托——那是纳库鲁的主教送给他的——去那些教堂。那是辆很棒的摩托车——日本人生产的雅马哈。父亲很喜欢骑它。他总是在后面的小路上偷偷练习刹车跳跃,因为他觉得不该让别人看见一个神职人员在玩特技。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没人向他提起过。圣约翰教堂是父亲一手建起的,在这之前人们只能坐在树下的长凳上。教堂用坚固的白色水泥砌成,屋顶是红色的锡皮。喇叭花的藤爬满了屋顶,到了开花季节,花朵会一直垂到窗外,让人觉得恍若置身于一个花园中。当我听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后,我想像中的伊甸园就是这样的:一座隐匿在花丛中的宫殿。教堂里有为人们准备的长凳、一个布道用的诵经台、一把高脚椅——给主教为孩子们行按手礼时用。同绕祭坛的栏杆后面是盖着白布的圣台,墙上还有个放圣餐杯盘的壁龛。我们没有洗礼盘,所以我们总是把人们带到河边,让他们浸到水中算作洗礼。这时候我和妈妈就在旁边唱圣歌。洗礼仪式很冗长,现在想想当时大家都很不耐烦,不过音乐很好听。女人们合唱,男人们演奏乐器。其中高个子鲁奥弹得最出色,他是乡村学校的一名教师,我们不太礼貌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莫斯特·亥——意思是最高。演奏乐器很简单——用一个报废的法国标致牌汽车的引擎活塞环做的,莫斯特·亥用一根厚铁条在上面敲打,会产生一种美妙清脆的旋律。
教堂后面就是牧师住宅。房子有水泥地板和一些天窗,一个独立的厨房,还有个很好用的木炭炉子,那是一位教区居民用一个柴油桶焊成的。我们有电灯,两个电插座,一台收录机,但没有电视。爸爸告诉我们电视会在晚饭时引来魔鬼。厨房、起居室、我们的卧室、妈妈的卧室、爸爸的书房,一共五间。用卡伦金人的说法:我们是基奇奇颇有声望的人物。
基奇奇是座狭长的,布局分散的村子:商店、学校、邮局、马他图①车站、加油站、油炸圈饼店坐落在主干道的两边,大多数房子盖在山谷梯田周围的小道边。梯田中有一块我们家的耕地,就在山谷南边半公里的地方。通往那块地的小路正好经过乌凯雷韦家的前门。他们有七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讨厌我们。他们朝我们扔粪球或石头,骂我们是自以为是的卡伦金人,可恶的圣公会教徒。他们属于非洲内陆的基库尤②教派,这些人对基督教的清规戒律一点都不尊重。
【①马他图:非洲较普遍的小型公共汽车,也就是小巴士,随叫随停,票价便宜,但非常拥挤。】 【 ②基库尤人:生活在肯尼亚中部和南部的民族。】
如果说教堂是我爸爸的伊甸园,那么耕地就是我妈妈的天堂。山谷里空气凉爽,你能听到流水冲刷河床发出的潺潺声。我们在田里种了玉米、葫芦和一些甘蔗。地方上的酒商向父亲买甘蔗来酿朗姆酒,出于基督教义的考虑,父亲装作对他们买甘蔗的目的毫不知情。此外我们还种了大豆、红辣椒、洋葱、土豆和两株拇指香蕉树——虽然梅兹·吉普乔布认为它们会汲取土壤外的生命。玉米已经长得高过我的头了,我时常会从玉米地跑进甘蔗地,似乎两步路就把我从一个世界带进了另一个世界。田里总是有音乐,有时是太阳能收音机里的声音,有时是女人们在翻土锄草时一起唱歌。我会和她们一起唱,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很擅长和声。耕地里有块地方专门用来摆放贡品以祈求神灵的保佑。一棵被蔓生的无花果树死缠着的老树伸展着浓密的卷须,上面挂着妇女们做的木制小神像,还献上了钱、印第安珠宝和啤酒,这就是耕地里最神圣的地方。
你也许想知道这时的恰卡怎么样了?大概你已经算出了日子,第一个包裹是在我九岁的时候落在了乞力马扎罗山上。那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呀——另一个世界要接管我们的世界,可是它怎么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如此少的印象?这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它比原来的世界离我更近。
在基奇奇我们并不孤陋寡闻,在电视上我们看到过乞力马扎罗的画面,在民族日报上读到过有关文章,讲述从天上掉下的东西长出类似珊瑚礁和雨林的故事。我们听到过收音机里的讨论说它增长得有多快——每天50米。在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样的疑惑——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从哪儿来。
每天清晨,好几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从空中呼啸而过,在天上留下几道蒸气云迹,它们运来更多的人和机器来研究恰卡。但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它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教堂、房屋、耕地、学校;星期天的礼拜和星期一的圣经学习;音乐课、家庭作业学习小组;缝纫、锄草、搅拌粗玉米粉;赶跑玉米田里的山羊;和小蛋蛋,还有邻居家的格蕾丝、露斯一块玩——我们玩耍时不能太吵,因为爸爸在工作。流动银行一星期来一次,流动图书馆两星期来一次。疯狂的马他图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压倒任何它们看见的东西,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每扇车门和车窗上都吊满了人。风尘仆仆的大型乡村客车像公牛似的在陡峭的山路上奔驰。基库比,镇上的傻子——但愿我们能受得了他,穿着粪色的衣服坐在乡村客车前头阻止它们行驶。雨季、热季、凉季①,人们出生、结婚、离婚、生病,或在事故中突然死去。乞力马扎罗也好,恰卡也好,那都是从同样遥远的地方带来的另一个世界的画面。】
【①非洲许多国家一年分为雨季、凉季、热季三个季节。
第二章
我十三岁了,在我们这已经算是个女人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恰卡来到了我的世界,毁掉了它。那晚我在格蕾丝·穆西卡家,我和她一起做家庭作业——这是个听收音机的借口。联合国占领你的国家所能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有了很棒的电台节目。我会跟着电台哼唱,它常会播放些我们家不允许听的音乐。
当时我们正在听迷幻舞曲音乐。突然收音机一片嘈杂,仿佛电台在自己调频道。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唱片跳针了或是别的什么,格蕾丝站起来拨弄收音机旋钮。结果只是更糟了。格蕾丝的妈妈从隔壁房间进来说她的电视机没有图像了,尽是些曲线。然后我们听到了第一声轰隆声。声音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沉闽空洞,像是滚动的雷声。在高地的许多夜晚经常会打雷。我们很清楚雷声听起来该是什么样的。那不是雷声,一定是别的什么。轰!又是一声。现在声音靠近了。
外面人声鼎沸,灯影晃动。我们也举着火把循着声音跑出去。马路上都是人:男人、女人、孩子。无数火炬摇曳的光线交织在一起。轰!声音更近了,响声震得窗户嘎吱作响。所有的人都把火把高举向天空,看着就像一支支闪光的矛。孩子们都吓哭了,我也有些害怕。
莫斯特·亥好像找到了答案:“音爆!上面有东西!”
他的话音未落,我们也都看到了——它运动得如此缓慢。模样很奇特,就像是一个孩子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道线。它从东南方向过来,穿过乞力阿尼东面的山脉,犹如一支箭般笔直朝向我们偏南一点的方向飞去。
这是五月末一个平常的夜晚,大雨过后天空明朗,满天繁星。
我们看见线的顶端有个发亮的圆点划过星空。它仿佛是在飘浮、跳舞,就好像如果盯着太阳太久眼睛会出现幻觉一样。在它后面拖着的那条尾线就像联合国的大型喷气飞机留下的云迹,只是更纯净,发着蓝光,在夜空移动。
现在又有两声声响接连发出,声音离我们是那么近,直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这时一个老婆婆开始哀号。恐惧攫住了我们,很快所有的人望着天空中闪光的细线泪流满面,男人也和女人一样哭了。
许多人坐在地上把熄灭的火把靠在膝盖上,茫然不知所措。一些年纪大的人用夹克、围巾、报纸把头蒙住。其他人看见他们这么做了,很快所有人都坐在地上把头蒙住了。
莫斯特·亥却没那么做。他站在那抬头凝望着发光的线,它似乎在把夜空劈成两半。“多美呀!”他说,“我竟然能亲眼看到这样惊人的景象!”
他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直到那东西逐渐消失在西面黑蒙蒙的山脉后面。我看见天空中细线的闪光映射在莫斯特·亥的眼眸中,久久才消褪。
那东西消失后好一会儿,没人知道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吓坏了,同时大家也都松了口气,它就像是黑暗天使从天而降,却放过了基奇奇。人们还在哭,但现在是解脱的泪水,哭声也就不同了。
有人从屋里拿来一台收音机,其他人也拿来了自己家的收音机,很快我们所有人坐在路中央的黑暗中,周围围了一圈收音机。
一个播音员打断了晚上的音乐节目发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在20点20分8秒,一个新的生物包落在了中央省内。
听到这些,人群中传出低低的交头接耳声。
“安静!”有人叫道。大家都不再说话了。虽然消息很可怕,但它总比黑暗中的怪声要好多了。
播音员说生物包落在靠近图沙的尼安达鲁瓦东面沼泽中,一个基库尤小村子上。
图沙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有些人的亲戚就住在图沙。有乡村客车从涅里开往图沙,从基奇奇到图沙也就二十公里。有人在抽泣。有人在祈祷。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但我们都知道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四年里恰卡已经吞噬了乞力马扎罗、安波塞里和纳芒加的边缘,现在正在靠近卡及亚都的A104高速公路和内罗毕。我们忽视它的存在,继续自己的生活,相信等它真的到来时我们会知道该怎么做。现在它从天上落到离我们二十公里的地方,按每天50米的速度,也就是说,四百天后它将到达基奇奇:你只有这么多时间来决定该做些什么。
这时,负责标致汽车站的杰克逊站了起来。他把头歪向一边,举起一根手指。大家都安静下来。他看着天空,“听!”
可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指向南面,这回我们听到了:飞机的引擎声。
闪烁的飞机探照灯照出了山谷远处树林的剪影。从树林后面先是出现了一架,然后十架、二十架、三十架、更多。直升机像蝗虫一样笼罩了基奇奇。它们引擎的轰鸣声铺天盖地。
我用校服的领巾裹住脑袋,用手捂住耳朵,尖叫着想盖过声响,但那刺耳的巨响仍穿透耳膜,我的脑壳似乎要像瓦罐一样四分五裂了。
一共是35架直升机:它们飞得非常低,机翼产生的强大气流震得我们的锡皮屋顶咔啷啷直响,搅动起来的漫天灰尘扑面而来。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欢呼着,向飞行员挥动他们的火把和学校的白衬衫。他们欢呼着,看着直升机越过山脊、田垄。他们欢呼着,直到飞机的引擎声逐渐消失在夜虫的呜叫声中。恰卡到哪里,联合国就会紧随其后,就像追着母狗不放的公狗。
几小时后卡车也开进来了。当它们在崎岖的公路上跋涉时,转动的引擎声吵醒了整个基奇奇。
“现在是凌晨三点!”库里雅太太朝着灰白色卡车叫喊道,它们的车门上有蓝色的UNECTA①标志。
【① UNECTA:联合国在非洲的国际警察组织,专门负责研究恰卡和处理居民撤退事宜。】
大家再也没法入睡了,我们站在大路边看着他们穿过村子。我倒很想知道当那些司机转弯时,突然看到这么多面孔和眼睛出现在车灯前会怎么想。有些司机向我们挥手致意,一些孩子也向他们挥手回敬。等到了黎明我们下地干活挤羊奶时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进来。在我看来他们就像一条望不到头的白蛇在山谷的公路上蜿蜒盘旋。在他们到达山谷隘口处时,东面升起的第一缕阳光为车队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