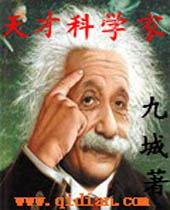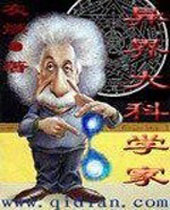历史学家 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的,是的。好像是中间那条龙吞噬了它周围的一切。”我轻率地开了口,但最后语速慢了下来。
罗西好像无法将眼神从他眼前的那条龙身上挪开。后来,他终于有力地合上书本,搅动咖啡,但没有喝。
“你从哪里弄到这本书的?”
“就像我刚才和您说的,两天前,有人不小心把它放在我图书馆的座位上。我知道我应该马上把它送到珍本室,但我真的觉得这是私人藏书,所以没有送去。”
“噢,的确。”罗西盯着我说。“它的确是某人的私有财产。”
“您知道是谁的?”
“知道,是你的。”
“不,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发现了这本书,在我的——”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住了口。外面的光线从灰蒙蒙的窗子照进来,他看上去老了十岁。“您说它是我的,是什么意思?”
罗西缓缓起身,走向他书桌后的书房一角,爬了两级图书馆取书用的梯凳,拿下一本黑色的小书。他站在那里凝视了一会儿,似乎不情愿把它交到了我手里。然后他还是递了过来,说:“你看看这个如何?”
一本小书,封皮是古旧的棕色天鹅绒,像古老的弥撒书或《日经》,书脊和正面什么也没写,不知这是本什么书。上面有一个铜色扣子,稍一用力就解开了。书自己一下子敞开到中间。横亘在那里的就是我的——我说了是我的——那条龙。这一回,它的形象覆盖到了书页的边缘,爪子突出,龇牙咧嘴,页眉依然是同样的哥特字体,写在同样的小旗上。
“当然,”罗西的话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时间,我找到了资料证实这幅图的出处。它是中欧的设计风格,大约一五一二年出版——所以你看它完全可以按内容的不同而随便移动,如果有内容的话。”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那些精致的书页。前面的书页上没有标题——是的,这我已经知道了。
“多么奇怪的巧合!书的背面有海水浸渍过的痕迹,也许是在黑海旅行后留下来的。即使是史密森学会也没法告诉我旅途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瞧,我还不辞劳苦地找人做了化学分析。花了整整三百美金,我才得知这玩意儿曾在某个多岩尘的环境里待过,很可能是在一千七百年以前。我甚至不远万里,去伊斯坦布尔了解它的来源。但最奇怪的还是,我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
他伸出手,我欣然将这本又旧又脆弱的书还给他。
“您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吗?”
“我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桌上发现的。”
我一阵惊颤。“在您的桌上?”
“确切地说,是我图书馆里单间的桌子上。”
“您是在哪里——它是从哪里来的?是送您的礼物吗?”
“也许吧。”罗西怪怪地笑了笑。他看上去像是在努力控制某种情感。“再来一杯咖啡吗?”
“嗯。那现在我给您的书找到伴儿了,您更知道它该待在哪里,它们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
“它们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即使空气中飘着现磨咖啡的香醇,那声音听上去也是如此的空洞。
“那您的研究呢?仅有化学分析不够埃您说过您曾试图多了解——?”
“我是试图了解更多。”他坐下来,张开他不大但看起来很实在的手捧着咖啡杯。
“我想我欠你的还不只是一个故事,”他平静地说。“你听说过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吗?”
“是的,德拉库拉。喀尔巴阡山脉一片领地的统治者,也叫做贝拉·路格斯。”
“是的——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在他们当中最令人讨厌的那个家庭成员上台前,他们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你去图书馆时是否查了他的资料?查了吧?不祥的预兆。那天下午我看到那本怪书时,就去查了那个单词——那个名字,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还有喀尔巴阡山。马上就被迷住了。我们来谈谈喀尔巴阡山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它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地区。当然,关于德拉库拉的基本故事已经被推敲过多次,没有多少可挖掘的了。他是瓦拉几亚的国王,十五世纪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和他自己的人民都痛恨他。他应该算是中世纪所有暴君中最恶劣的一个。德拉库拉的意思是德拉库尔的儿子——也可以说是龙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任命其父为‘龙之号令”的首领——这个组织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保卫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德拉库拉的父亲在一次政治谈判中将幼小的德拉库拉交给了土耳其人做人质,德拉库拉目睹了奥斯曼的酷刑,从而也变得残暴起来,这是部分原因。”
罗西摇了摇头。“不管怎样,弗拉德在一次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被杀了,或许是被自己的部下误杀的,被埋在斯纳戈夫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关于他的回忆成为一种传奇,迷信的农民将它代代相传。到了十九世纪末,有位爱夸张的作家——亚伯拉罕·斯托克——受其影响,拿着德拉库拉这个名字套在了一个完全是自己想象的人物,一个吸血鬼的头上。弗拉德·特彼斯的残酷令人心惊胆战,但他当然不是吸血鬼。斯托克的书根本没提到弗拉德,尽管他笔下的德拉库拉讲到他的家族反击土耳其人这段光荣的历史。”罗西叹了口气。“斯托克在书中收集了一些关于吸血鬼的传说——也有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尽管他根本没去过那里——事实上,弗拉德·德拉库拉是瓦拉几亚的统治者,而瓦拉几亚就和特兰西瓦尼亚接壤。到了二十世纪,好莱坞继续复活、传承吸血鬼的神话。顺便告诉你,我了解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我目瞪口呆,他叹了口气,好像不愿意往下说。“你瞧,弗拉德·德拉库拉在中欧、东欧,也许还有他家乡的大档案馆一直被人们在研究着。但他是以杀戮土耳其人起家的。我发现,还没有人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去调查德拉库拉的传说。于是我才决定去伊斯坦布尔,算是我对早期希腊经济研究的一次偷偷的散心。噢,我出版了所有关于希腊研究的成果,多少带点报复性。”
有一阵子他没有说话,凝望着窗外。
“我想我还是坦白告诉你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发现吧,以后我就不去想它了。说起来,这些漂亮的书你也得到了一本。”他庄重地把手放在那叠在一起的两本书上。“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可能会重蹈我的覆辙,也许还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他对着书桌的上方阴沉地笑了笑,说:“我还帮你省了写资金申请的许多麻烦呢。”
我笑不出来。他究竟意图何在呢?我突然想到自己低估了自己导师独特的幽默感。也许这是一个精心制造的恶作剧——这种危险的古书他有两本,就放了一本在我桌上,知道我会拿来给他的,而我像个傻瓜似的,真的照做了。但是我看到灯光下他突然变得灰沉的脸,他的胡子一天都没刮,眼神空洞,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和幽默。
我向他倾身过去,问:“您想告诉我什么呢?”
“德拉库拉——”他停了一下。“德拉库拉——弗拉德·特彼斯——还活着。”
“老天,”我父亲突然看了看表说。“你怎么没提醒我?都快七点了。”
我把凉凉的手插进我的海军蓝外衣口袋里。“我不知道啊,”我说。
“您还是继续讲吧,别在这节骨眼上停下来。”我觉得,父亲的脸有一阵儿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我从来没料到父亲还有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说,心智失常?因为讲那个故事,有几分钟里他是乱了方寸了吗?
“太晚了,故事长着呢。”父亲端起茶杯,又放下。我看到他的手在发抖。
“再给我讲讲嘛。”我说。
“要是我们还不走,他们就要来赶我们了。”
夜早已降临——寒冷,多雾,潮湿的东欧之夜。街上很荒凉,几乎没有行人。
“戴上帽子,”父亲提醒我,他自己总是戴帽子的。
我们正要走到被雨水清洗过的小无花果树下,他突然停住了,张开手,把我护在身后,好像有车刚刚疾驶过我们身边。但并没有车,黄色的街灯下,街道也安静,如在乡下。我父亲谨慎地左右观望。我觉得前面根本就没有人,不过我的长帽檐挡住了些视线。他站住,转头仔细听着,身体纹丝未动。
然后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我们继续朝前走,讨论我们到了云游旅馆该吃什么晚饭。
在那次旅行中,我再也没有听到德拉库拉的故事。我很快掌握了父亲害怕的规律:他每次只简单而急促地讲一点点故事,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戏剧性效果,而是为了保护什么——他的力量?他的理智?
第三章
回到阿姆斯特丹家里,父亲特别沉默寡言,同时也总在忙碌。我不安地等待着有机会能再问问他关于罗西教授的事。但他似乎总是在躲避我,除非有时我就挨着他坐下,等待一个可以提问的间隙。这时,他会伸出手来,心不在焉但有略为伤感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每当此时,我实在不忍心再问起罗西教授的故事。
父亲再去南方时,带了我一同前往。他只要去那里开一个会,而且不是很正式的会,不值得特意跑那么一趟。但他说,他想带我去看看那里的风景。
在公共汽车里,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拉古萨的主干道都是大理石铺成的,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多少鞋底的打磨,再加上周围商店和宫殿灯光的反射,显得格外光亮。以至于它看起来犹如一条大运河的河面。
在城市靠海的一端,我们瘫坐在一张咖啡桌前,过去这是城中心。
“南方就是舒服啊,”父亲满意地说,拿起了一瓶威士忌和一碟烤沙丁鱼。
“你以前什么时候来过这里?”我才开始相信父亲有过从前的生活,就是我出生以前他的生活。
“我来过好几次,四次或者五次吧。第一次是很多年前了,我那时还是学生。我导师建议我从意大利到拉古萨来,就是看看这里的奇观。当时我在学习———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个夏天在弗罗伦萨学意大利文。”
“你是说罗西教授了。”
“是的。”父亲敏锐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去看他的威士忌,“我应该多给你说一说他。”
“我想听,”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好吧,我明天给你多讲讲罗西,白天讲,那时我不会太累,我们还可以有点时间去看看城墙。”
他用酒杯示意了宾馆上面那些灰白而明亮的城墙,“白天讲故事更好,尤其讲那种故事。”
第四章
“您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儿结巴地问他。
“我再说一遍,”罗西以强调的口吻说。“我在伊斯坦布尔发现德拉库拉还活在我们中间。或者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疯了,”他慈爱地说。“我跟你说每一个在历史中折腾久了的人都可能会疯掉。”他叹气说。“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料库,是苏丹迈米德二世创建的。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地图,上面标有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人的墓地,我想那可能就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地图总共有三张,都是关于同一地区的,只是比例尺一张比一张小,标得也更详细。”他边说边用手指敲打着自己那本怪书。“第三张地图中央的文字是一种原始的斯拉夫方言。只有懂得多国语言的学者才可以看个道道来。我尽力过,但不能确定。”
这时,罗西摇了摇头,好像仍在遗憾自己知识有限。“一天下午,我在仔细研究第三张,也是最让人费解的一张地图上邪恶之墓的位置。你还记得弗拉德·特彼斯是被埋在罗马尼亚斯纳戈夫湖中一座岛上的修道院里吧。这幅地图和其他两幅一样,并没有显示有什么湖中小岛——尽管它的确显示有一条河穿过,到了中部,河床逐渐变宽。在地图中心,邪恶之墓的上方,不论它该在哪里,有一条线条粗略的龙,头上戴着王冠,那是一座城堡。那龙和我——我们——书上的一点儿不同,但我推测它肯定是随着德拉库拉传说到土耳其人那里的。在龙的下面,有人写了很细的字。起初我以为是阿拉伯文,用放大镜仔细看过后,我突然发现这些文字竟然都是希腊语,我完全不顾规矩地开始大声翻译——尽管图书馆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位无聊的管理员进出,很明显是要来看我有没有偷什么东西。这时,我完全是一个人。那些极小的文字在我眼皮下跳动,我大声念了出来:‘它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就在此刻,我听见楼下大厅有门被砰地关上。楼梯间传来很重的脚步声。我的脑海里还转着这个念头:放大镜告诉我这幅地图不像其他两幅,它被三个不同的人,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做了标记。笔迹和语言都不相同。那些老而又老的墨水的颜色都不一样。我突然有了个想法——你知道,就是那种一个学者经过长时间认真研究后有的那种灵感。
“我觉得那幅地图最初是由中间的素描和周围的山构成,希腊文的咒语位居正中。可能是后来才用斯拉夫方言标记它提到的那些地方———至少是用代码。后来它不知怎地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周围添上了来自《可兰经》的谚语,它们把中间那个邪恶的预言包围或者囚禁起来,或者就是用辟邪物将它包围起来,以抵抗黑暗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哪个懂得希腊文的人先标识了这幅地图,甚至画了这幅地图?我知道在德拉库拉那个时代,拜占庭的学者用希腊文,而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则大多不用。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我从来没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