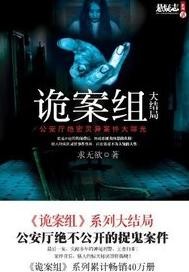弓区大谜案-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我该说是不快的吗?”
“不,不,堪特考特。别误解我。孩子他妈最近对此事特别恼火。你瞧她有个越来越大的家庭。每天都在变大。但别管她。你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再付。”
丹泽尔摇着头:“不行。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租了你上面的房间住下。接下来我认识了你。我们一起聊天,聊美或是实用。我发现你没有灵魂。但是你很诚实,而我喜欢你。我甚至愿意跟你们家一起用餐。我让自己把你的起居室当作自己家一样。但现在瓶子碎了(我不是说壁炉台上的那个),尽管玫瑰花香还留在上面,它不能重新被拼起来了——永远不能。”他悲伤地甩着头发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店。克劳想追着他出去,但克劳太太还在叫他,而在所有守礼节的社会里,女士总是优先的。
堪特考特径直——在他松松垮垮的步态下尽可能的直——走向格罗弗街46号,敲了敲门。格罗德曼的女杂工开了门。她是个脸上坑坑洼洼的人,有砖灰色的皮肤和轻浮的举止。
“哦!我们又在一起了!”她快活地说。
“别像个小丑一样说话,” 堪特考特骂道,“格罗德曼先生在吗?”
“不,你打扰到他了,” 格罗德曼自己咆哮道,他突然穿着拖鞋出现了,“进来。在审讯结束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又在喝酒?”
“我发过誓了。再也不喝一滴酒,从——”
“凶案以后?”
“呃?”丹泽尔·堪特考特惊恐地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从12月4号。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根据那起案子为基准,就像他们用格林威治为基准来算经度一样。”
“哦,”丹泽尔·堪特考特说。
“让我看看。差不多两周了。离开酒——还有我己经这么久了。”
“我不知道哪一样更糟,” 丹泽尔愤愤地说,“你们两者都偷走我的脑子。”
“是吗?”格罗德曼微笑着说,“那也不过是小偷小摸罢了。什么事在你的伤口上撒了盐?”
“我的书的第24版。”
“谁的书?”
“好吧,你的书。你肯定从《我抓住的罪犯》中赚到了一大堆钱。”
“《我抓住的罪犯》,” 格罗德曼纠正道,“我亲爱的丹泽尔,我已经多少次指出组成我的书的骨干是我的经历,而不是你的?每个案子里是我破坏了罪犯的计划。任何一个记者都可以添上佐料。”
“正相反,新闻界的记者们善于揭露事实。而你自己已经做到了——没有人比你善于冷静,清晰,科学地陈述。但是我把裸露的事实理想化,把它们提升到诗歌和文学的殿堂里。这本书的第24版证明了我的成功。”
“胡说!第24版的成功是由于里面的凶案。那都是你干的吗?”
“你还真突然地指控人啊,格罗德曼先生,” 丹泽尔转变了腔调说。
“不——我已经退休了,” 格罗德曼笑道。
丹泽尔并没有非难退休侦探的草率。他甚至也笑了一下:“好了,给我五英镑,我就说‘了结了。’我还欠人钱。”
“一便士也没有。为什么你在凶案之后一直不来找我。我还得自己写信给《混乱报》。你可能赚到一克朗(译注:25便士)。”
“我受到手指痉挛困扰,不能干你最后的工作啦。我正要去告诉你,在那个早晨发生了——”
“凶案。你在审讯时说过了。”
“那是真的。”
“当然。你不是宣了誓吗?你这么早起来告诉还真是热心。你是哪只手上痉挛?”
“什么,当然是右手。”
“那么你不能用左手写?”
“我连笔也握不住。”
“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许。你是怎么会弄成那样的?”
“写得太多了。那是唯一可能的原因。”
“哦!我不知道。写什么?”
丹泽尔犹豫了一下:“一篇史诗。”
“怪不得你欠债了。一英镑够让你解脱吗?”
“不,那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那么,给你。”
丹泽尔拿起了硬币和他的帽子。
“难道你不去挣它吗,你这个乞丐?坐下来写点东西给我。”
丹泽尔拿起了纸和笔,坐下来:“你想让我写什么?”
“你的史诗。”
丹泽尔吓了一跳,满脸通红。但是他开始干了。格罗德曼在躺在他的扶手椅里,看着诗人严肃的表情笑了起来。
丹泽尔写了三行,停了下来。
“记不起更多的了?好吧,给我读开头。”
丹泽尔读道:——
“人类的第一次违抗,
禁忌之树上的禁果致命的味道,
把死亡带到人间——” (译注:诗文断句并不一样,大意如此)
“停下!”格罗德曼叫道。“你选的是多么令人讨厌的主题啊。”
“令人讨厌!为什么,弥尔顿选了同样的主题!”(译注:弥尔顿,《失乐园》的作者。)
“该死的弥尔顿。走开,你还有你的史诗。”
丹泽尔走了。脸上坑坑洼洼的人为他打开大门。
“我什么时候该得到条新裙子,亲爱的?”她挑逗地低声说。
“我没钱,简,”他简短地说。
“你有一英镑。”
丹泽尔把一英镑给她,用力关上了门。格罗德曼听到了他们的低语,默默地笑起来。他的听觉很敏锐。大约两年前简把丹泽尔介绍过来。当时他想要个文书助理,这个诗人就从那时起开始给他干杂事。格罗德曼辩称简也有她的理由。不用了解他们,他就能掌控他们俩。他觉得没有人他掌控不了的。所有男人——还有女人——都有要隐藏的事情,你只需要装着知道它是什么。格罗德曼就是这样科学。
丹泽尔·堪特考特摇摇摆摆,满怀心事地回家,心不在焉地回到克劳家的餐桌上。
第六章
克劳太太如此冷酷地盯着丹泽尔·堪特考特,并如此粗鲁地给他切牛肉,使得他在晚饭结束的时候大呼慈悲。彼得吃西红柿来滋养其哲学的天赋。他足够宽容地让他的家庭拥有他们的不良嗜好;但没有香味能诱惑他放弃他偏爱的素食。而且,肉食可能会令他联想起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和皮革很像,但弓区的牛排有时跟它很接近。
丹泽尔晚餐后通常沉浸于诗意盎然的白日梦中。但今天他没有去打盹。他立刻出去找点工作。但到处是一片寂静。他到他曾为之写过关于教区委员的尖刻社论的《迈尔恩镜报》的办公室想要一笔预付款但徒劳无功。他跋涉到城里提出要为《火腿和蛋公报》写一篇关于熏咸肉的现代方法的文章也被拒绝了。丹泽尔知道很多关于养猪和屠宰,熏制和干燥过程的知识,因为他有好几年时间为《新猪肉先驱报》听写关于这些单调事情的政策。丹泽尔也知道很多其他隐秘的事情,包括织布机,卷心菜叶以及烛花的生产,下水道的内部结构。他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为商业报纸写作了。但那里有激烈的竞争。太多的拥有文学天赋的人知道复杂的关于生产和市场的学术词汇,并急着接活儿。格罗德曼可能没怎么使丹泽尔的这种能力退步,但有几个月他把时间都花在《我抓住的罪犯》上,这就像荒废那样有害。因为当你的对手在进步的时候,原地踏步就是一种倒退。
绝望中,丹泽尔费力地走到贝斯纳格林。他在一家小烟草店的窗前停了下来。那里贴着一张公告写着“出售情节”
公告接下去声明从这里可以得到大量的情节——包括轰动性情节,幽默情节,爱情情节,宗教情节,以及诗歌情节;也有完整的手稿,原创小说,诗歌和故事。里面有售。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脏的店,砖头被玷污,木头发黑。橱窗里有一些发霉的旧书,各式各样的烟斗和烟草,以及很多没有挂起来,也没有装框,用油彩在画板上画着最肮脏的涂鸦。从标题中你能知道这些是想画风景。最贵的是“清福德教堂”,别的一些主要是一些苏格兰风光——以山为背景的湖,水中有完整的倒影,前景中还有一棵树。有时候树也会在背景中。这样湖就会在前景中。天空和水都特别蓝。这个系列的名称是“原创手制油画”。灰尘积在所有东西上面,就好像是被仔细铲上去的。业主就像晚上不脱衣服睡在橱窗里一样。他是一个枯瘦的人,红鼻子,帽子下面盖着长而少的黑发,胡子又黑又密。他抽一根长粘土烟斗,就像戏剧中衰弱的反角一样。
“啊,下午好,堪特考特先生,”他搓着手说,一半出于冷,一半出于习惯,“你带来了什么给我?”
“什么都没有,” 丹泽尔说,“但如果你能借我一英镑,我会给你一个绝妙的东西。”
戏剧里的反角甩着他的头发,眼里充满狡诈:“如果你拿到了钱还会去干,那它还真会是绝妙啊。”
戏剧里的反角拿那些情节去干了什么,是谁带来的,这些堪特考特从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头脑现在很廉价了,丹泽尔能找到一个顾客就很开心了。
“当然你认识我已经够久,该信任我了,”他叫道。
“信任已经死了,” 戏剧里的反角喷着烟说。
“安妮女王也死了。”气愤的诗人喊道。他的眼睛里是一种危险的被逼急了的神态。他需要钱。但戏剧里的反角容不得变通。没有情节,没有晚饭。
可怜的丹泽尔愤怒地离开。他不知道该去哪儿。临时地他又转过身绝望地盯着橱窗看。再一次他读着上面的字——“出售情节”
他盯着这看了那么久以致它的含义都消失了。当这些词的意思突然再次闪现在他的脑海里,它们有个新的意义。他温和地走进去,从戏剧里的反角那里借了4便士。接着上了去苏格兰场的公共汽车。车上有个长得不算难看的女服务员。车子的节奏在他的脑海里形成旋律。他忘却了他的情况和他的目的。他从没有真写过史诗——除了“失乐园”(译注:指在格罗德曼家写的东西)——但他为酒和女性写歌词,还经常啜泣着想自己是多么不幸。但除了熏咸肉或者攻击教区委员的文章外,没人向他买过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奇怪而狂野的人。那荡妇在他热情地注视下都觉得自己挺漂亮。这几乎把她催眠了,尽管,她低头看她的新法国羊皮鞋以逃避它。
在苏格兰场丹泽尔要求见爱德华·温普。爱德华·温普并不是马上能见到的。就像国王和编辑那样,侦探们是很难接近的——除非你是一个罪犯,你一点也发现不了他们。丹泽尔知道爱德华·温普主要是因为格罗德曼对他继任者的蔑视。温普是一个有品味,有文化的人。格罗德曼的兴趣完全集中在逻辑和证据问题上。他只读关于这些的书,对于那些美文完全不屑一顾。温普有着灵活的智慧,他轻视格罗德曼那种缓慢,费力,沉闷,几乎日耳曼式的方法。更有甚者,他威胁要通过一些天才的手段,让格罗德曼的光辉传统黯然失色。温普最善于收集间接证据,把2和2加起来得到5。他能收集起许多黯淡的毫不相关的数据,让一些统一猜想的电光以一种为达尔文或者法拉第增光的方法闪过它们。一个可能去揭示自然秘密的知识分子被转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守护者。
诗人让一个警察以为这事事关生死,在这友好警察的帮助下,丹泽尔得到了大侦探的私人地址。那在国王十字车站附近。奇迹般地,温普下午在家。当丹泽尔被领到楼上见他时,他正在写字,但他站起来,用他公牛般的眼睛望着来访者。
“我想这是丹泽尔·堪特考特先生,” 温普说。
丹泽尔吓了一跳。他并没有报上姓名,只是把自己形容为一位绅士。
“是我。”他咕哝道。
“你是亚瑟·康斯坦特之死审讯会上的证人之一。我这儿还有你的证词。”他指向一份文档,“为什么你又来提供新的证据?”
丹泽尔又吓了一跳,这回脸也涨红了:“我需要钱,”他不由自主地说。
“坐下。”丹泽尔坐下了。温普还站着。
温普年轻而面色红润。他有一个罗马人的鼻子,穿着整齐漂亮。在找到了上天赐予他的妻子这一点上他战胜了格罗德曼。他有一个活泼的男孩,没有人能比他更聪明地从食品室里偷果酱。温普在房子顶层孤立的书房里干所有他能带回家的工作。在他恐怖的密室外面他是一个普通的丈夫。他爱他的妻子,而她并不看好他的才智但欣赏他的脾气。温普对家庭琐事毫无办法。他甚至无法分辨出佣人的“身份”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可能他无法把自己降到处理这种琐事的水平上。就像一个顶尖教授忘了怎么解二次方程,而只能用微积分来解决问题一样。
“你想要多少钱?”他问。
“我不讨价还价,” 丹泽尔回答,他终于冷静了下来,“我来这儿给你一个提示。我觉得你会为此给我5英镑。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不会拒绝。”
“你不会拒绝的——如果你应得的话。”
“好。我就单刀直入了。我的提示是关于——汤姆·莫特莱克。”丹泽尔就像射出鱼雷那样吐出这个名字。温普并没有什么反应,“汤姆·莫特莱克,” 丹泽尔有些失望地继续说,“有一个恋人。”他刻意停了一下。
温普说:“怎么样?”
“那个恋人现在在哪儿?”
“到底在哪儿呢?”
“你知道她失踪了?”
“你刚刚告诉我了。”
“是的,她离开了——没留下一点线索。她在康斯坦特先生的谋杀案两周前离开的。”
“谋杀?你怎么知道那是谋杀?”
“格罗德曼先生是这么说的。” 丹泽尔再次被吓了一跳。
“哼!难道那不正好是那是自杀的证明吗?好,接着讲。”
“在自杀案两周前,杰茜·戴蒙德失踪了。在斯特尼格林,她租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做裁缝的。她手艺高超。比较时尚的女士都知道。她做的一件女装曾被拿到法庭上。我想是那位女士忘了付钱;杰茜的女房东是这么说的。”
“她一个人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