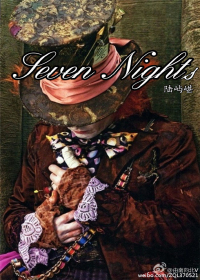"爱丽丝·镜城"杀人事件-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的意思是说,把带不走的机器都扔下了?”
“大概是吧。就算把坏掉的机器带走,也换不了几毛钱啊!但他们为何突然放弃了江利岛呢?”
“按常理而论,莫非是破产了?”
“倘若真是那样,报纸该有消息的吧。虽没有明确记载,但他在其他地方的生意持续经营了数年,想必不是资金方面的问题。”
“那会不会是要建城堡,所以才中止了砍伐?”
“那样子的话,未免急躁了些。倘若从一开始就是要建造‘爱丽丝·镜城’才买下这座岛的话,这转变未免太快……嗯,益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果然还是和过去的战争有关吧。”
“也有可能……”古加持的嘴角泛起一抹微笑,望着鹫羽,“白角当时是要砍伐杉树才踏上这座岛,却发现了跟战争有关的某个重要东西,譬如未使用的燃料库、大量的导弹头,又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他觉得这不是砍伐的时候,于是就建立了城堡,隐居在这座岛上,目的是为了隐藏什么东西。”
“听起来就像是一部冒险小说啊。”
“谁让我是个喜欢冒险小说的侦探呢!”古加持耸耸肩膀,开了个玩笑,“你呢?知道这座岛的秘密了吗?”
“完全没有。”
“诀窍就是要纵观全局,整体性的失败就是寻求真理的失败。若要知道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将世界粉碎,而要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整体来看待,这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要将世界上所有界限都清除掉。”
“那就是侦探的任务?”
“没错,但还有一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命运’这东西。”古加持皱起了眉头,“若侦探只以‘外人’之姿置身局外的话,那他很可能是一位名侦探。但他若被牵扯到这个整体里面,或者从一开始就被牵扯进去的话,那其下场只有两个——成为被害者;或者,成为犯人。”
“有理。”
“而眼下,我可以断言,”古加持略一停顿,须臾说道,“我们现在就是从一开始就被牵扯进去了。”
“这话真不吉利。”鹫羽苦笑道,“你是不是想起了那个英国有名的孤岛杀人事件?”'此处是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
“我没办法不想起来啊!或许,我们也会像那十个人一样,迎来完全相同的结局。”古加持远眺着道路尽头,说道,“前方就是那座有问题的城堡吧?”
“对,马上就要到了哦。”
“招待我们的路迪,是假名吗?还是外国人?”
“她好像是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混血儿呢!虽然国籍是英国,但表面看来明显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她自称日语很差,其实用语方面比我都要恭敬。似乎几年前,她就和朋友住在日本了,这座江利岛目前的所有者据说就是她的伯父,三年前从白角手中购得了这座岛的所有权。”
“那个伯父来了吗?”
“好像没来,但上午见过路迪小姐本人了,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人。”
“哦?那还真是值得期待!”
最终,视野豁然开朗。
他们面前所出现的,正是“爱丽丝·镜城”。
城堡的外观纵以“混乱”称之,恐怕亦不过分。各种风格交相混杂,予人一种凌乱无序的感觉。哥特大教堂式的山墙顶封檐板奇妙地歪在一边,玄关门廊处突出来的四角形柱子底部细小,上端反而异样地膨胀着。入口处的右边是一个巨大的柱基,上面并排着三位仿佛是圣者的雕像,却一律背对来客。尖塔的前端不知为何从墙壁里横横穿出,上面设有无数个不知能否打开的百叶窗。然而,这些全都是故意建造的,其初衷绝对是要确保城堡的整体混沌。砌墙用的石头本该是白色的——当然达不到新天鹅城堡'Neuschwanstein Castle,一座白墙蓝顶城堡,德国的象征。'的水平——而眼下,那些石头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黑色,就像永远无法剥落的影子般四处浮现着。从远处眺望城堡,类似圆形的塔以及看起来很牢固的胸墙,让人一眼就知道这模仿的是西欧古堡;但再看看细节的话,又会发现其中独具匠心地混杂着哥特教堂风格。总而言之,这是一座把古堡和教堂塞进一个模子里、强行融合而成的建筑物。
鹫羽曾见过“爱丽丝·镜城”,所以受到的冲击不像古加持他们那般巨大。但就算是这样,他只要一停下脚步,便觉得内心的震惊无法平静,甚至踌躇得不想靠近城堡。城堡周围堆积的落雪有些发黑,寒风如刀刃般迎面扑来。鹫羽艰难地继续前行,古加持沉默无语,无多和入濑亦是闭口不言。正面那宽阔的门廊湿漉漉的,未积一片飘雪。门旁扔了团塑料管子,看来有人曾用管子将水引来,融化了积雪。这也算是没有铲雪锹时的应急措施了,只不过,若继续这样冷下去的话,到夜里就会变成一个天然的滑冰场吧?又或者,门廊会屈从大暴雪的淫威,再次被白雪覆盖。
“搞不好的话,连门都会被埋掉吧?雪为何会下这么大?以前,我在山形县工作的时候,可吃够了大雪的苦头!”
“因为风是从陆地刮过来的缘故吧!”
一直沉默着的无多突然像自言自语一样说道。他旁边的入濑用双手捂住了脸,似乎很冷的样子。
“怪不得有股西伯利亚的感觉。”古加持笑道,“倘若只是暴风雪的话,尚能容忍,但愿别积雪才好!”
“一般会积多厚呢?”
鹫羽满脸不安地问道。
“厚得让你头大。虽不知这岛上的情况如何,但这建筑物估计是没有应对积雪的设施。其实,没必要太担心吧?怕就怕到时候雪太大,船出不了海,那就麻烦了。唉,反正先祈祷大伙平安无事好了!”
鹫羽一行人聚集在玄关的门廊处,门从里面上了锁。鹫羽抓着门环,“笃笃笃”敲了三下,里面全无动静,又敲了三次,这才从里面传来一道话音:
“欢迎光临‘爱丽丝·镜城’!
“And wele queen's guests;(向王后陛下的客人们,)With thirty…times…three!(献上三乘以三十遍的欢迎!)'这句话是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And wele Queen Alice with thirty…times…three!”(三乘三十遍敬献给爱丽丝王后)变化而来。'
“去接船的鹫羽君差不多该回来了吧?那么就可以说‘大家都到齐了’!通常,在封闭的情况下杀人,每杀一个人,总人数就会减一,而老夫正酝酿着这种题材的小说,就是从无人生还的情况下往前倒叙,遇害人物相继登场,当大家齐齐露面之际,就写上‘闭幕’这种字眼。这种推理很有抒情诗的美感吧?你觉得如何?”
“一点也不如何!若要我去看那种无趣透顶的东西,不如直接跳海算了!”
“那你会冻死的哦!”
“这个时期,比起气温,水温更加暖和!本大爷才不会傻到去冻死。”
海上哧哧冷笑着,仿佛有满腹坏水。他从夹克衫里随手拿出根烟,用桌上放着的打火机点燃了。
窗端望了一眼他的动作,从凳子上起身走近窗户。大雪纷纷落下,且有继续变大的倾向。雪花像被污染的羽毛一般,在这阴沉沉的天空中四下飘舞。窗户有两层结构,以防止室内的暖气向外泄漏,但窗玻璃表面却冷得吓人。这里是“爱丽丝·镜城”的一个房间。窗端他们很随意地称这间屋子是游戏室。室内摆放了很多游戏道具,角落的玻璃柜内则有多种美国制纸牌,抽屉里还放了很多桌面棋牌游戏,地产大亨、苏格兰场、象棋、麻将等应有尽有。墙壁上自然挂着飞镖的标靶。室内更摆着高级的台球桌和上等的台球杆。海上邀窗端玩一局台球,但长时间的旅途奔波使后者相当疲倦,更何况他一大把年纪了,要和海上进行对等的比赛,委实有点困难。要知道,他最后一次摸台球,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海上被窗端拒绝,兴致索然地走向柜台,从里面挑出几瓶威士忌,返回桌边向窗端劝酒。两人遂你来我往地喝起了加冰的威士忌,打发掉了近一个小时。
窗端坐在桌前的沙发上,海上则坐在他对面。这男人原是刑警,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严厉的面孔,身上的肌肉紧绷绷的,套着件宽松的深灰色夹克衫,多少缓和了一点他那过度结实的身材。
“那你喜欢哪种推理呢?”窗端问道。
海上从口中轻吐出一个烟圈,漫不经心地将视线投向窗户那边:“要我说啊,首先犯人必须很强,而且要强得不像话!不是被侦探一逼问就哭哭啼啼、坦白从宽的那种软蛋,而且不会因这样那样的小事就挂掉,就像电影《虎胆龙威》那种。然后,那家伙把和平生活着的家伙们一个个全都干掉!”
“你这……哪有推理性可谈?”
“犯人的残暴性就是推理本身,用那无法想象的残暴将人挨个杀死。”
“简直就是小成本制作的恐怖电影嘛!说是推理,更像是恐怖……不,该说是血腥才对。”
“本大爷说的不是推理这个类型,而是犯人何等冷酷,”海上斜斜摇晃着手上的玻璃酒杯,“唉……算了,现在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合适,我辞掉刑警工作的理由,就是因为不管哪个犯人都只会犯一些可怜又无趣的案子!因为隔壁太吵了,就用球棒殴打邻居;因为妻子外遇,就用刀杀了她!妈的!开什么玩笑!身穿黑衣、手拿斧子的面具男人在哪里?哪里都没有!既然没有那种人,那么要抓捕他的本大爷就不必存在了,这是存在性的危机啊!你能理解吗?老爷子,用你喜欢的那种正统推理来说的话,就是永远找不到会按照若山牧水的诗歌来杀人的家伙呀!”'若山牧水(1885-1928),原名若山繁,对短歌、俳句、新体诗颇有造诣,一生出版歌集十四本,极度嗜酒,无酒便无法创作,亦不能挥毫,后因酒精中毒而死。'
“先不提若山牧水。你的心情,老夫并非不能体会。”
“老爷子你也喝嘛!”
“酒对肝不好,你也少喝点。”
“是吗?那好,老爷子对这棋盘有何看法?”
“嗯……”
窗端俯视着桌上的棋盘。
木质的棋盘,表面光滑,镀有一层树脂薄膜。正方形的框子里面,画着八乘八的小方格,颜色不是普通的黑白两色,而是白色和褐色。盘面上分布着棋子,一眼望去,好像是随意摆放,但每个棋子的位置又显然带有各自的含义——在普通的对弈里,棋子是绝不会这样摆放的。
“有十个白色的棋子。”
窗端摘下老花镜,把眼镜腿叠回又打开,缓缓开口。
“主教(相)、城堡(车)、骑士(马)各有两个,士兵(卒)有四个,没有国王(王)——通常来说,若没有国王的话,就无法开局,但仔细看看棋子的摆放,又会发现这不是随意摆的,而是完完全全放在格内。更何况‘十’这数字,就算老夫不愿意,亦不得不有所想法。你听好了,老夫是如此想的,这白色的棋子,会不会是代表印第安人的小瓷人呢?”
“西洋棋的棋子岂会变成印第安小瓷人?真要说的话,和主教相比,印第安人更适合当祈祷师呢!”海上说罢,似乎突然想到了某事,“你是说,范·达因的……”
“不是《主教杀人事件》,而是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这部小说里,杀人是按照英国古老的童谣进行的,这首童谣的内容就是讲述十个印第安人挨个死去,故事中的行馆位于一座叫印第安的小岛上,馆内的桌上放了十个印第安小瓷人,每少一个,就代表有一人遇害。到访该岛的十个人,最后一个不剩,全被杀死了!”
“啊,那个我很早很早以前好像看过呢。”
“尔后,这种被害者遇害未久便告消失的东西,譬如人偶,侦探小说迷们通称之曰‘印第安小瓷人’。”窗端扬扬得意,问道,“如何?是不是跟咱们眼下所处的环境很像?”
“是吗?”
“你仔细看看棋盘。若鹫羽君他们安全到达城堡的话,包括他在内,就增加了五个人,加上咱们这些先到者,正好和棋盘上的棋子数目相同。说到底,咱们只是盘面上摆放的白色棋子罢了。”
“等等,莫非你没算路迪这女的?”
“算了,招待者当然不能例外。只有大家都站在棋盘上,游戏才能开始。包括女佣堂户小姐都算上了。现在,她估计正铲着雪呢。招待我们的路迪小姐,自我们到了城堡,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更不知道在做什么。”
窗端刻意将话音压低。虽未看到窃听器或隐蔽摄像头之类东西,但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棋子的怪异摆放足够挑起他的戒心了。
“克里斯蒂那小说中的犯人,就在十个人当中吧?虽然我忘了是谁。你是说,我们当中有犯人?”海上把还剩短短一截的香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或许正如老爷子所说,若真有谁最初就怀有杀意的话,和小说的共同点就是把准备杀掉的人都喊到这岛上来。但为何人们都会像笨蛋一样被杀掉?人又不是玩偶,不会像玩偶那样悄然消失,好歹总要抵抗一下的吧?”
“正好相反,对天真无邪唱着童谣慢慢靠近你的死神,咱们人类正如玩偶一样,毫无还手之力。或许,玩偶正好象征了无能为力的死亡。倘若是那种意思的话,棋盘上的棋子就很合适。”
“别开玩笑了!本大爷才不会被干掉,绝对不会被干掉!虽然不知道是谁,但他若把这座岛比作棋盘的话,本大爷肯定是最后一个留在棋盘上的!”
“气势真不错呀。”窗端放下酒杯,微微一笑,“怪异的城堡,受邀而来的侦探们,充当印第安小瓷人的棋子,你不觉得其实挺有趣的?刚才,你说这世上不可能存在正统推理式的犯人,说不定接下来咱们就能碰到呢?”
“能不能有指望,难说。”
“嗯,眼下确实还没人被杀,也有可能这一周都平安度过。大概是老夫的杞人忧天吧,如果能离开这座岛的话,送你一辆自行车当礼物好了!”
“我才不要!”
“不过,凡事都有个万一。老夫脑袋里的灰色脑细胞正发射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