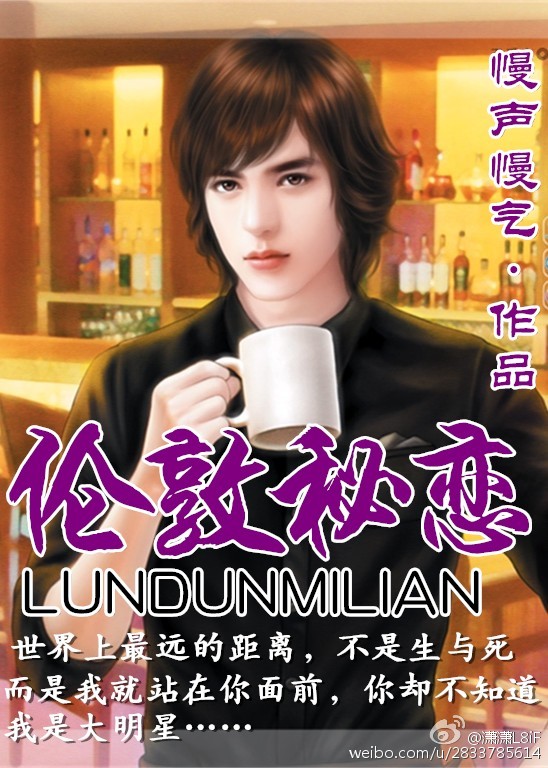伦敦桥-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是因为他们更了解巴黎,而且会在这里呆更长的时间,”毛德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俄国佬混蛋打过几年的交道。顺便说一句,他们并不信仰你的‘野狼’。相信我,我打听过。”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就从“野狼”一直谈到布拉赫所知道的那些俄国佬混蛋。撇去别的不说,早上那明亮的蓝天真是太漂亮了,但这却让我更加郁闷。我他妈在这儿干什么呢?
中午一点半,毛德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去吃午饭吧。当然了,是跟俄罗斯人。我知道个地方。”
她带我走进了一家她所谓的“巴黎最古老的俄式餐馆”——达鲁餐厅。餐厅的前厅里摆放着暖松,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莫斯科富翁的别墅。
我很生气,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时间坐下来吃午饭。
然而,我还是陪着毛德吃了下去。我真想掐死她和那个谄媚的服务生,还有所有我能够得着的人。她肯定是一点都不知道我有多么生气。她也能当侦探!
吃完午饭,我注意到邻桌的两个男子在看我们,也许他们是在看毛德,在看她那头性感的红头发。
我告诉她有人在看她,可她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巴黎的男人都这样。猪。”
“看看他们会不会跟踪我们,”我们站起身离开餐馆的时候,我对她说。
“我想他们不会。我不认识他们。我认识这儿的每个人。不过,不包括你的‘野狼’。”
“他们跟着我们出来了,”我告诉她。
“这没什么。毕竟这里是出口。”
距离不长的达鲁街在福布格?圣欧诺雷街口就走到了尽头。毛德告诉我,这里是橱窗街,一直通到万多姆广场。我们才走了一个街区,一辆白色的林肯房车就停到了我们的身边。
一个黑胡子男人打开后车门,探出头来。“请上车。别吵吵,”他的英语里夹带着俄语的口音。“上车,快。我不想跟你们废话。”
“不,”毛德说。“我们不会上车的。你出来跟我们谈。你他妈是谁?你以为你是谁?”
胡子男人掏出枪来开了两枪。我真不敢相信当街发生的这件事。
毛德?布拉赫倒在了人行道上,我敢肯定她已经死了。鲜血从她前额中间那个可怕的锯齿形伤口里流了出来。她的红头发四处散开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上方的蓝天。在她倒下的时候,脚上的一只鞋松开掉到了街当中。
“上车,克罗斯博士。我不想再说一遍。我已经够礼貌的了,”俄罗斯人说着,把枪对准了我的脸。“上车,不然,我也一枪打暴你的头。我会很高兴这么做的。”
《伦敦桥》第79章
“现在是展示与讲述时间,” 我一上车,黑胡子俄罗斯人就对我说。“美国学校里面不都是这么教的吗?你有两个孩子在上学,对吗?所以,我会向你展示一些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会向你讲述它们的意义。我让那个女侦探上车,可她不愿听。她叫毛德?布拉赫,没错吧?她想像其他那些臭警察一样强硬。可她现在却成了死警察,还强硬什么?”
汽车离开了杀人现场,把那个被打死的法国女侦探留在了街上。我们在距杀人现场几个街区的地方换了车,这是一辆不那么扎眼的灰色“标致”。为了留下有价值的线索,我记住了两辆车的车牌。
“现在我们去乡下兜兜风,”那个俄罗斯人说,看来他还很会享受生活。
“你是谁?你们想要我干什么?”我问他。他个子很高,大概有六英尺五英寸,身体非常结实。很像我听说过的“野狼”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支“贝瑞塔”对着我的头。他的手结实而有力,看得出来,他很熟悉枪械,知道怎么使用枪支。
“我是谁,这一点也不重要。你在找‘野狼’,不是吗?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他阴森森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递给我一个布袋。“套在头上。从现在起,照我说的做。记住,展示与讲述。”
“我知道。”我戴上头套。我永远也忘不了布拉赫惨死在他枪下时的情景。“野狼”和他的手下都这么嗜血吗?这对四个目标城市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吗?这是他们展示实力和控制的计划吗?还是为了过去的某个秘密罪行进行的报复?
我不知道“标致”车开了多久,但肯定是远不止一个小时:先是在市区内缓慢行驶,然后又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小时左右。
后来,车速又慢了下来,可能是开上了尘土飞扬的土路。因为车身晃得比较厉害,我的脊椎都快折断了。
“现在可以把头套摘下来了,”黑胡子对我说,“我们快到了,克罗斯博士。反正这儿也没什么可看的。”
我摘下头套,发现车已经开到了法国乡下的某个地方,正沿着一条两边长满蒿草的乡间小路向前行驶。路边根本没有任何指示牌或标志。
“他住在这儿?”我问。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带我去见“野狼”。为了什么原因呢?
“目前他住在这儿,克罗斯博士。不过他马上就会离开。你应该知道,他居无定所。就像幽灵和鬼魂一样,到处游荡。很快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标致”车在一个石砌的农庄前停了下来。两名武装分子立刻从前门走出来接我们。两人都用自动步枪瞄准了我的上半身和脑袋。
“进去,”其中一人对我说。这个人长着白胡子,不过,跟那个把我一路押来的黑胡子一样高大结实。
很明显,这个白胡子比黑胡子的级别高,那个黑胡子到现在才收敛了一点。“进去!”他对我重复道。“快点!你没听见吗,克罗斯博士?”
“他是个野兽,”白胡子对我说,“他不该杀那个女人。我就是‘野狼’,克罗斯博士。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伦敦桥》第80章
“顺便说一句,千万别逞英雄。不然的话我就不得不杀了你,然后再重新找一个送信的,”我们走进农庄的时候,他告诉我。
“我现在是送信的?送什么信?”我问。
那个俄罗斯人不耐烦地挥挥手,就好像我的问题是一只在他的那张毛脸前不停地嗡嗡乱叫的苍蝇。
“时光飞逝。你跟那个法国侦探呆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他们正在碍你的事,那些法国人。你不这么想吗?”
“我是这么想过,”我说。与此同时,我真不敢相信他就是“野狼”。我不相信。但他是谁呢?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你当然想过。你是个聪明人,”他说。
我们走进一间黑暗的小屋,里面有一个石砌的壁炉,但里面没有火。屋里零乱地摆放着一些实木家具、旧杂志和发黄的报纸。窗户关得很紧,密不透风。屋里唯一的光亮来自一盏落地灯。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现在在我面前露面?”我开口问道。
“坐下,”俄罗斯人说。
“好吧。我是个送信的,”说着,我坐到了椅子上。
他点点头,“对。送信的。让所有人都清楚地了解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们明白,”我说。
我的语音未落,他就突然冲过来,在我的下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的椅子向后翻了过去,我也一下子栽倒在地,脑袋撞到了石地板上。我可能昏迷了有几秒钟。
但我马上就被屋里的其他人给拽了起来。我只觉得头晕目眩,嘴里也有一股血腥味。
“我要跟你说清楚,”俄罗斯白胡子继续说。看来,揍我只是他这段演讲中一个必要的停顿。“你是个送信的。你们这些笨蛋还没有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没人明白,没人真正明白,他们都会死掉,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今天死在巴黎的那个蠢女人就是这样!你觉得在那颗子弹飞进她的脑袋之前,她明白吗?这一次,你们必须支付赎金,克罗斯博士。全部赎金。四个城市的赎金。还有,必须释放囚犯。”
“为什么要释放他们?”我问。
他又打了我一拳,但这次,我没有倒下。然后,他转身离开了房间。“因为我说了!”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很沉的黑色手提箱又回来了。他把手提箱放到我面前的地板上。
“这是月亮的背面,”他说。然后,他打开箱盖,让我看里面的东西。
“这东西叫战术核爆炸装置。说得简单点,就是‘便携式核弹’。爆炸威力非常可怕。不像常规弹头,它可以在地面爆炸。易隐藏,易携带。别这么大惊小怪。我保证你肯定看过广岛被炸后的照片。当然,每个人都看过。”
“这跟广岛有什么关系?”
“这枚核弹的当量跟那枚相当。威力巨大。我们,也就是前苏联,生产过这种可由卡车运载的核弹。
“想知道其他的在哪儿吗?好吧,华盛顿、特拉维夫、巴黎和伦敦都有,而且还不只一枚。所以,正如你看到的,我们拥有‘核武库’里独特的新成员。我们就是核俱乐部的新会员。”
我开始觉得全身发冷。这里面真的是枚核弹吗?
“这就是你要我送的信?”
“其他核弹已经就位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你可以带着这枚核弹回去。让那些家伙们看看。不过,记得提醒他们看得快点。
“现在,也许,也许,你明白了。滚吧。对我来说,你就是只臭虫,不过,至少你还算是只臭虫。带上核弹。把它当成一份礼物吧。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会发生什么事。现在,滚吧。快滚,克罗斯博士。”
《伦敦桥》第81章
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不清。黑色头套只是做做样子,我想,因为在回巴黎的路上,他们什么都没给我戴,而且路途显得比来时也短了许多。
我不停地问他们要把我和这枚核弹送到什么地方去,可车里没人给我回答。一句话也没有。他们一路上只说着俄语。
对我来说,你就是只臭虫……带上核弹……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巴黎市区,那辆“标致”在一个购物中心拥挤的停车场里停了下来。一支枪对着我的头,然后,他们把我铐到了那个手提箱上。“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们,但同样没人回答。
随后,“标致”车又在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街停了下来。这里曾经是巴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不过现在却几乎空无一人。
“下车!”他们命令我——这是一个小时以来我听到的第一句英语。
慢慢地,小心地,我带着核弹下了车。我觉得有点头晕目眩。可“标致”却呼啸着开走了。
我注意到了空气中的湿度、尘埃,这就是真正的原子的感觉。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前宽敞的广场上,手上铐着那只黑色的手提箱,它至少有50磅重,可能还不止。
这可能是一枚核弹,跟哈利?杜鲁门下令投放到小日本头上的那枚威力完全一样。我已经冒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一切就会这样结束吗?当然会。我们已经全盘皆输,尤其是我的生命也会结束。我会被炸死吗?如果没死,我会不会受到核辐射?
我看到一家维京唱片店附近站着两个警察,就朝他们走了过去。我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身份,并请他们尽快给公共安全局的局长打个电话。
我没告诉他们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但当局长的电话接通后,我立即向他通报了这个情况。“这是真的吗,克罗斯博士?”他问道,“这枚炸弹是不是已经启动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就当它已经启动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快派你的拆弹专家来。快点!”我放下电话!
几分钟内,整个波布区就被撤空了,只剩下了几名巡警、宪兵和几个拆弹专家。至少,我希望他们是专家,是法国能派出的最好的专家。
他们叫我坐到地上,我照做了。当然,是坐在那个黑色的手提箱旁边。无论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会照做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觉得胃里很恶心,不过,坐下以后我觉得舒服了一点,虽然作用并不大。至少,我先前的头晕目眩已经过去了。
首先,他们牵来一只搜弹犬来嗅我和那个手提箱。这是一只漂亮的德国小牧羊犬,“搜弹犬”。它非常小心地接近我,看着手提箱的样子就好像在看着一个对手,一个敌人。
当它走到离我5码远的地方时,它停住了,然后从胸膛里发出一阵低吼声。它脖子上的毛全都竖了起来。哦,妈的。哦,天啊,我心里想。
它一直低声地咆哮着,直到它确认了里面的辐射物质,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到训犬师的身旁。真是只聪明的牧羊犬。我又是孤单一人了。我这辈子从没这么害怕过,从来没有。被炸得支离破碎,甚至有可能是彻底蒸发,这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想要忘掉这个想法实在是太难了。
如坐针砧的几分钟过去后,两名拆弹专家穿着宇航服似的防护服小心地朝我走过来。我看到他们中有一个人手里还握着剪线钳。上帝保佑他!这一刻简直是太离奇了!
拿着钳子的那个专家跪到我身旁。“没事的,不会有事的,”他小声说着,然后小心地拆下了我手上的手铐。
“你可以走了。慢点起来,”他说。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揉着手腕,赶快朝后退去。
几个穿得跟外星人似的警察护送我出了所谓的“热区”,来到了两辆拆弹车的停放地。当然,这里仍然属于“热区”。如果核弹爆炸,巴黎市区方圆至少一英里的范围内都会立即被蒸发掉。
我坐在其中一辆车里看着拆弹专家们拆解那枚炸弹。如果他们能拆掉的话。我从没想过要离开这个现场,随后的几分钟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漫长的几分钟。车里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屏息以待。就这样死去,这么突然地死去,这简直无法想象。
法国拆弹专家传来话:手提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