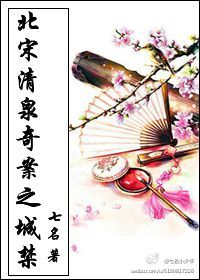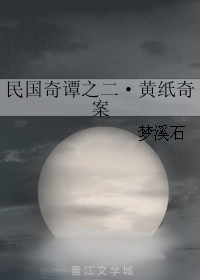黑麦奇案-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尼尔摇头表示同情。
柏西瓦尔·佛特斯库准备要走了——他拿起帽子说:
“若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找我。不过我想——”
他停顿片刻——“你会到紫杉小筑来吧?”
“是的,佛特斯库先生——此刻我已经派一个人在那边
负责。”
柏西打了个冷颤。
“真不愉快。想一想这种事竟发生在我们身上——”
他叹口气,走向门口。
“白天我大抵在办公室。那边有很多事要料理。但是我
傍晚会到紫杉小筑。”
“是的,先生。”
柏西瓦尔·佛特斯库走出去。
尼尔咕哝道:“一本正经的柏西。”
谦谦虚虚坐在墙边的海依巡佐抬头用疑问口气说:“长
官?”
尼尔不答腔。他问道:“长官,你有什么心得?”
尼尔说:“我不知道。”接着小心引述名言说:“他们
都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人物。”
海依巡佐似乎有点困惑。
尼尔说:“爱丽丝漫游奇境。海依,你不认识你的爱丽
丝吗?”
海依说:“那是一本名作,对不对,长官?第三广播节
目,我不听第三广播节目的。”
。10。
飞机刚离开巴黎机场五分钟左右,兰斯·佛特斯库打开
他手上的大陆版“每日邮报”。过了一两分钟,他惊叫一声,
邻座的派蒂好奇地转过头来。
兰斯说:“是老头。他死了。”
“死了!你爹?”
“是的,他似乎在办公室突然发病,送往圣尤德医院,
刚送去不久就死了。”
“亲爱的,真遗憾。什么毛病,中风吗?”
“我猜是吧。看来好像是。”
“他以前有没有中风过?”
“没有,就我所知没有。”
“我想人不会第一次中风就死掉。”
兰斯说:“可怜的老头,我以为自己不怎么喜欢他,不
过现在他死了……”
“你当然是喜欢他的。”
“派蒂,我们的本性不像你这么好。噢,算了,我的好
运似乎过去了,对吧。”
“是的。现在发生这种事,真奇怪。就在你要回家的节
骨眼上。”
他猛回头看她。
“奇怪?派蒂,你说‘奇怪’是什么意思?”
她略带惊讶看着他。
“噢,一种巧合。”
“你是说我打算做的事情都会出问题?”
“不,亲亲,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世上真有霉运存在。”
“是的,我想是有的。”
派蒂又说:“真抱歉。”
他们抵达哈德罗机场,正等着下飞机,一位航空公司的
官员以清晰的嗓门叫道:
“兰斯·佛特斯库先生是不是在飞机上?”
“在,”兰斯说。
“麻烦你走这边,佛特斯库先生。”
兰斯和派蒂跟着那人下了飞机,比其它旅客先走。他们
经过后座的一对夫妇身旁,听见男士对他太太说:
“我想是著名的走私客。当场被捕。”
兰斯说:“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他望着桌子对面
的警探督察尼尔。
尼尔点头表示同情。
“塔西因——紫杉果——这件事活像一出刺激的通俗剧。
督察,我敢说你一定觉得这种事很普通。全是日常工作。不
过下毒事件在我们家族似乎很牵强。”
尼尔督察问道:“那你根本想不出谁会毒死令尊罗?”
“老天,想不出来。我猜老头在生意上结了不少冤仇,
很多人恨不得活生生剥他的皮,在财务方面打垮他之类的。
至于下毒?反正我不可能知道。我出国多年,对于家里的事
情所知不多。”
“佛特斯库先生,我就是想问你这一点。我听你哥哥说
你和令尊已多年未来往。你肯说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家
呢?”
“好的,督察。我曾收到家父的信件,我看看那是多久以
前的事了——噢,六个月以前,就在我婚后不久。家父写信
暗示说:他希望往事成为过去。他建议我回家,进公司做事。
他说话含含糊糊,我不确定要不要照他的意思去做。结果我
八月到英国来——也就是三个月以前。我到紫杉小筑去看他,
他提出的条件相当有利。我说我要考虑,而且要跟内人商量。
他十分谅解。我飞回东非,跟派蒂商量,最后决定接受老头
的建议。我得将那边的事务作一了结,但我说好在上个月底
弄完。我跟家父说我会打电报通知我返英的日期。”
尼尔督察咳嗽一声。
“你回来,你哥哥似乎很惊讶。”
兰斯突然咧嘴一笑。他那张迷人的面孔泛出淘气的喜色。
他说:“别以为柏西知道这回事。他当时正好到挪威度假。
告诉你,老头故意选那个时间。他背着柏西办事。事实上我
怀疑家父是跟柏西——叫他瓦尔也可以——吵架才给我机会
的。我想瓦尔多多少少想要管老头,咦,老头绝对受不了这
种事。他们吵些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他气愤极了。他大概觉
得安插我进去,挫挫瓦尔的锐气也好。他一向不喜欢瓦尔的
老婆,说来有点势利,他对于我的婚姻非常满意。他大概想
叫我回家,让柏西面对既成的事实,开个大玩笑。”
“上回你在紫杉小筑逗留多久?”
“噢,至多一两个钟头。他没留我过夜,我相信他就是要
背着柏西秘密进行。他甚至不希望仆人知道这件事。我说过
啦,最后讲好我回去考虑,跟派蒂谈谈,再写信把我的决定
告诉他,我都照办了。信上提到返英的大概日期,昨天再从
巴黎拍电报给他。”
尼尔督察点点头。
“这封电报害你哥哥非常吃惊。”
“我打赌会的。不过,柏西照例又赢了。我来迟一步。”
尼尔督察若有所思地说:“是的,你来迟了一步。”又
精神勃勃地说:“八月回来,你有没有碰到家里其它的人?”
“我继母在那边喝茶。”
“你以前没见过她?”
他突然咧嘴一笑。“没有。老头真会选女人。她至少比
他年轻三十岁。”
“请恕我发问,令尊再娶你是不是愤慨?你哥哥呢?”
兰斯显得很惊讶。
“我当然不会,我想柏西也不会吧。我们的母亲在我们
——噢,十岁或十二岁左右那年就死了。我惊讶的是老头怎
么没早一点再娶。”
尼尔督察咕哝道:
“娶一个比自己年轻这么多的女人真冒险。”
“这话是不是我哥哥对你说的?他就是这样。柏西最擅
长暗示艺术。督察,案情是否如此?我的继母是否有毒害家
父的嫌疑?”
尼尔督察面无表情。
他欣然说:“佛特斯库先生,现在还不能确定什么。喏,
我能请问你有什么计划?”
兰斯思忖道:“计划?我想我得改订新计划了。家属在
什么地方?都在紫杉小筑?”
“是的。”
“我还是马上赶去好了。”他转向他太太:“派蒂,你
最好找家旅馆住下来。”
她连忙抗议:“不,不,兰斯,我要跟你走。”
“不,亲亲。”
“我要去嘛。”
“真的,我想你还是不要去比较好。不妨下榻——噢,
我已经好久没在伦敦逗留了——巴尼斯旅社。以前巴尼斯旅
社是很优美很安静的地方。我想还营业吧?”
“噢,是的,佛特斯库先生。”
“对,派蒂,那边若有房间,我把你安顿在那儿,然后
我再去紫杉小筑。”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呢,兰斯?”
兰斯的面孔突然显得阴森森的。
“坦白说,派蒂,我不敢确定大家欢不欢迎我。是爹请我
回来的,可是爹死了。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地方属于谁。我想
是柏西,不然就是阿黛儿。总之,我要先看看人家怎么接待
我,再带你去。何况——”
“何况什么?”
“我不想带你到一处有下毒者逍遥法外的住宅去。”
“噢,胡扯。”
兰斯坚决地说:
“派蒂,事关你的安危,我不愿冒险。”
。11。
杜博斯先生恼火了。他气冲冲地把阿黛儿·佛特斯库的
信笺拦腰撕掉,丢进废纸篓。接着他忽然慎重起来,又找出
纸片,点根火柴烧成灰。他低声咕哝道:
“女人为什么天生的这么笨?最起码的智虑……”这时候
杜博斯先生郁郁沉思道,女人从来就不懂得小心。虽然他因
此而获利多回,可是现在他却恼火了。他自己采取每一种预
防措施。如果佛特斯库太太打电话来,他吩咐人家说他不在。
阿黛儿·佛特斯库已经打给他三次了,现在她居然写信来。大
体上写信更糟糕。他沉思一会儿,走到电话边。
“请问,我能不能跟佛特斯库太太讲话?是的,是杜博斯
先生。”一两分钟后,他听到她的声音。
“维维安,终于找到你了!”
“是的,是的,阿黛儿,要小心。你在哪儿接电话?”
“图书室。”
“门厅里没有人偷听吧?”
“他们为什么要偷听?”
“咦,这谁知道呢。屋里屋外是不是还有警察?”
“不,他们暂时走了。噢,维维安亲亲,真可怕。”
“是的,是的,我相信一定会的。不过阿黛儿,我们必须
小心。”
“噢,当然,亲爱的。”
“电话里别叫我‘亲爱的’。这样不安全。”
“维维安,你未免太惊慌了吧?现在人人都叫‘亲爱的’。”
“是,是,这话不假。不过你听着。别打电话给我,也别
写信——”
“不过维维安——”
“只是暂时如此,你明白。我们必须小心。”
“噢,好吧。”听她的口音好像生气了。
“阿黛儿,听着。我给你的信,你烧掉了吧?”
阿黛儿·佛特斯库迟疑片刻才说:
“当然。我跟你说过我会烧的。”
“那就好。现在我要挂断了。别打电话,也别写信,我会
在恰当的时机给你消息。”
他把听筒放回挂钩上,若有所思地摸摸脸颊。他觉得对
方那片刻的迟疑很不对劲。阿黛儿烧了他的信没有?女人都
一样。她们答应要烧东西,却舍不得烧。
杜博斯先生暗想:信件——女人老是要你写信给她们。他
自己尽量小心,可是人有时候就是逃不掉。他给阿黛儿·佛
特斯库的寥寥几封信写些什么?他闷沉沉想道:“都是寻常的
闲话。”不过万一有特殊的字眼——特殊的措辞让警方歪曲解
释成他们所要的意思呢?他忆起艾迪斯·汤普森案。他暗想
自己的信纯洁得很,却又不敢确定。他愈来愈不安。就算阿
黛儿还没烧掉他的信,她现在有没有脑筋把它烧掉?也许警
方已经拿去了?他不知道她放在哪儿,也许放在楼上她特用
的起居室——可能在花哨的小写字台里。那是仿路易十四年
代的假古物。以前她曾告诉他那儿有个秘密抽屉。秘密抽屉!
这骗不了警察。不过现在屋里屋外没有警察,她说的。早上
他们在那边,现在都走了。
先前他们大概忙着查食物中的毒素来源。但愿他们还没
有逐室搜查房屋。也许他们得申请或取得搜索状才能这么做。
如果他现在立即行动,可能——
他脑中清晰浮出房子的画面。天快黑了,茶点将端入图
书室或客厅。人人都聚集在楼下,仆佣则在仆人厅喝茶。二
楼一定没有人。穿过花园,沿着遮蔽效果甚佳的紫杉树篱走
过去很简单。有一扇小侧门通到大露台,不到就寝时刻从来
不上锁,可以从那边溜进去,选择恰当的时机溜上楼。
玛丽·窦夫慢慢走下大楼梯,在半路梯台的窗口停顿片
刻,昨天她曾由此看见尼尔督察抵达。现在她眺望窗外渐暗
的日光,发现有个男人的身影绕过紫杉树篱消失了。她怀疑
是浪子兰斯·佛特斯库。说不定他在大门口遣走汽车,自己
绕着花园漫步,先回忆旧时光,再应付可能有敌意的家人。玛
丽·窦夫很同情兰斯。她唇边挂着微笑走下楼。到了大厅,她
碰见葛莱蒂,小丫头看到她,紧张兮兮跳起来。
玛丽问道:“我刚才听到的电话就是这一通?谁呀?”
葛莱蒂说话透不过气来,显得很仓促。“噢,是拨错号码
的——以为我们是洗衣店。前面那通是杜博斯先生。他要跟
女主人说话。”
“我明白了。”
玛丽横越门厅,回头说:“我想喝茶的时间到了。你还没
端来吗?”
葛莱蒂说:“小姐,我想四点半还没到吧?”
“差二十分就五点了。现在端进来吧。”
玛丽·窦夫走进图书室,阿黛儿·佛特斯库坐在沙发上,
眼睛瞪着炉火,小手指拎着一条花边小手帕。阿黛儿烦闷地
说:
“茶呢?”
玛丽·窦夫说:“正要送进来。”
一根木头掉出壁炉外,玛丽·窦夫跪在炉格边,以火钳
将它放好,又加了一块木头和少许煤炭。
葛莱蒂走进厨房,克伦普太太正在烹饪桌上调一大钵发
面点心,她抬起愤怒的红脸。
“图书室的电铃响了又响。丫头,你该端茶点进去了。”
“好吧,好吧,克伦普太太。”
克伦普太太咕哝道:“我今天晚上会跟克伦普说,我要告
他的状。”
葛莱蒂走入餐具室。她没有切三明治。噢,她偏不切三
明治。没有三明治,他们可吃的东西仍旧多得很,对不对?两
个蛋糕,加上饼干、圆面包和蜂蜜,还有新鲜的黑市奶油。用
不着她费心切蕃茄或肥肝三明治,已经够丰盛了。她有别的
事情要想。克伦普先生今天下午外出,所以克伦普太太的脾
气很大。咦,今天是他的休假日对不对?葛莱蒂暗想他没有
错嘛。克伦普太太由厨房叫道:
“水开了半天,壶盖都掀掉了。你到底泡不泡茶?”
“来罗。”
她抓了一把茶叶,量都不量就放进大银壶,提到厨房,
把滚水倒进去,又在银质大托盘上摆好茶壶和水壶,整个端
进图书室,放在沙发附近的小茶几上。她匆匆回来端另一个
放点心的托盘。她端点心盘走到门厅,老爷钟突然轧轧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