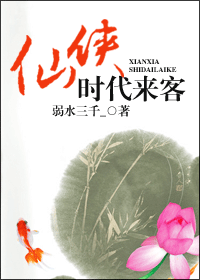巴巴罗萨来客-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用胶布小心翼翼地将那把没用的P6 型自动手枪贴在她的腹部并将备用弹匣牢牢地固定在她的乳房下面。她显得有些畏缩,但她用手和眼睛无声地向他保证她仍然可以行动自如并且能将武器很好地掩藏在厚厚的毛衣下面。
她回卧室去以后,邦德把自己的自动手枪在下腹部处贴好,枪的角度正好可以让他用手从腰带或衣襟部位迅速地把枪抽出来。揭开胶布时难免会有点痛,可一想到不会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一名手持武器的人时,那种疼痛就显得不那么厉害了。
他把一个弹匣贴在了腰背部的下方。然后穿上了那件长保温内衣,这是为了一旦需要他离开比较温暖舒适的饭店时所做的准备。
他穿上了厚牛仔裤和一件厚圆领毛衣以及他所喜欢的那件在某些部位带有皮块以防止磨损的斜纹粗棉布夹克。今天早晨他之所以要选择这件衣服穿,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感觉到了有某种非常严重的威胁正在逼近。那些皮块下面暗藏有一些能够在逃命或求生时给他以帮助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都很难被察觉出来,即使在身体接触或是在对衣服进行搜查时也是一样。
在摄影棚内的强光下他会有些热,但他至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动身前,邦德重新检查了他的毛皮大衣并把磁带倒好放入了笔记本计算机内,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紧急发送。他把发射机和笔记本计算机重新放在原先隐藏的地方,做好了迎接新的一天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他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尼娜既没有看到计算机,也没有看到发射机。
在他们做准备工作的时候,邦德和尼娜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对话——谈了谈天气、录像片,以及为“正义天平”组织工作被证明比他们原先想像的更要有趣和有收获之类的话题。他们的这些谈话大多都很空洞无物,有几次在谈到他们所能够制作出的这部平庸的审判录像片时两人还爆发了大笑,几乎把事情搞糟。邦德想,这只不过是盖伊和海伦在演戏罢了,可当他想到他的海伦极有可能已经出卖了他时,禁不住胃里一阵翻腾。
当娜塔莎领着他们通过走廊时,她压低嗓音告诉众人说今天可能要工作到很晚。“他们要求在今天完成拍摄工作。”她说。“好像是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
纳特科维茨孩子气地插话说可能是炖肉出了问题,娜塔莎听后咯咯地笑了起来。邦德皱起了眉头,他明白这是一种局势更加紧张的迹象。通常情况下彼特·纳特科维茨说话时总是会引起谴责声和不屑的表示。
吃完饭后,他们向摄影棚走去。那扇像一堵墙似的高大金属拉门大敞着,人们正在为拍摄做着准备。克莱夫站在摄影机附近同尤斯科维奇说话,尤斯科维奇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表演他的生平。
“盖伊,”克莱夫大声喊道,“行行好,动作快一点,求你了。我们最好还是赶紧开始拍戏,不然的话这一天又要过去了。我们可是在一个已经被时间遗忘了的地方。”
在邦德的示意下,纳特科维茨道了一声对不起后便向洗手间走去,邦德跟在他的后面。他们都向昨天晚上两人被人领着去过的三层瞥了一眼。现在看来那就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
男洗手间内空无一人,但没准儿隔墙有耳。邦德抓起一条放在洗手池上的坚硬肥皂,他从上面掰下一块并很快地在镜子上面写了几个字,“娜塔莎?
多大把握?”
纳特科维茨拧开一个水龙头把那几个字从镜子上擦掉。然后他用断断续续、颠三倒四的句子说了几句话,“是一架飞机?还是一只鸟?我不知道。”
然后又说道“从未见过像她那样的,太迷人了,她知道所有的把戏,但我不相信她是为了钱。”
这对邦德已经足够了。他冲彼特·纳特科维茨做了半分钟的怪脸,让他知道他的P6 型自动手枪可能已经成了一块废铁。
“一点不错,”纳特科维茨一边洗手一边不合调地哼唱着,接着他又以同样不和谐的音调唱道,“没有什么东西像女人,没有任何东西像女人。”
邦德语无伦次地对他唱的内容评论了一番,然后两人便走出了男洗手间。当他们穿过大厅向摄影棚走过去时,纳特科维茨露出他那乡绅般的笑容漫不经心地说,“我想和你谈谈那位女士,她是我从未见过的要不得的人,至少要六个小时才能拿下来。”
他们两个人心里都明白,由于他们之间的谈话一直很隐晦,估计不会有别人能搞懂。“你要是早点儿说会更让人开心,我的乔治老伙计。”邦德回答说。
“我以为你不会关心这种事。”
他们进到了摄影棚内,那扇拉门被关上了,接下来的长时间工作几乎使他们忘却了昨天晚上的辛劳和担心。
他们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拍摄倒叙镜头,表现人们所做出的反应——吃惊、悲伤、愤怒——集中拍摄构成三人法官小组的三名军官;然后是担任起诉和辩护的军官,再接下来便是尤斯科维奇,由于笼罩在他周围的真实的邪恶气氛,使他的过火表演得到了弥补。最后,他们拍摄彭德雷克的镜头,可以说他是唯命是从。
邦德通过大取景器看着彭德雷克的特写镜头,他敢说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毒品的威力,但那个人的表情只有中毒至深的人才能做出,要不就是人们想方设法引导他表现为一个无意的毒品受害者的形像。
午饭休息过后,他们又继续这场戏的拍摄。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控方和辩方军官的总结性发言。5 点钟他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工作,拍摄一大段经过精心准备的尤斯科维奇的发言,尤斯科维奇的表演就像任何初出茅庐的新星一样时好时坏。他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拍部分发言片段,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表现也不满意。包括身在控制室里的克莱夫在内,所有人都变得很急躁。“你简直可以用绳子把空气切成块了,”纳特科维茨耳语道,不过他的声音还是通过他的话筒传进了控制室,克莱夫闻听此话顿时火冒三丈,他命令所有的人都不许再作声,除非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
“如果再有谁饶舌我就亲自下去把他剔出去。”
“开始训人了,”在邦德身边为他担任跟焦员的尼娜小声说。
尤斯科维奇的发言是一段很精彩的政治性议论和有关人道主义的答辩。
他说俄罗斯领导集团“没有胆量将这桩可怕的事件公之于众。他们允诺实行一种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秩序,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自由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在内。”他们害怕行动。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并不打算把祖国引向一个新的时代。现在的统治集团一心想奉行另一种独裁统治。他不停地说着,他的声音很平静,很少有起伏,所以也更显得充满恶意。
终于,他们似乎达到了要求,但克莱夫通过耳机告诉邦德说被告还要再回来。他必须准备好拍摄尤斯科维奇和那个所谓的沃龙佐夫之间的一次简短问答。
邦德后来想他本不应该感到有什么意外,可当他拍完那段简短的对话后,那种欺骗行为的确使他吃了一惊。
尤斯科维奇站在被告席的正前方,他的眼睛直盯着犯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他问道。
“我只知道你是叶夫根尼·尤斯科维奇将军。这是别人跟我介绍的。”
“你能想到你早就该认识我吗?也许,从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
“我不知道怎么会应该认识你。”彭德雷克的俄语好的让人起疑,他甚至还带有乌克兰口音。“你的父母,他们是叫亚历山大·沃龙佐夫和列娜·沃龙佐娃吗?”
“是的。”
“你是在哈尔科夫城出生和长大的吗?你的父亲是不是在那里当医生?
你的家庭是不是很美满?”“我父亲在医学院行医并教授麻醉学,不错。我母亲是一名护士,他们都是好人。”
“你母亲的闺名叫什么——也就是他和你父亲结婚前使用的名字?”
“穆济金。列娜·伊莲娜·穆济金。”“是这样。你记得她的任何家人吗?你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有你母亲的姐妹们?”“是的,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我的外祖父穆济金以及我的三个姨妈。”
“你的几个姨妈是否结过婚?”
“是的,其中的两个结过婚。”
“你能回忆起她们婚后的名字吗?”
“她们中的一个同一位名叫罗斯托夫斯基的医生结了婚。另一个的丈夫名叫西达克。他是个军人,一名军官。”
“很好。她们有孩子吗?你有表兄弟吗?”
“是的,我的表兄弟名叫瓦迪克和康斯坦丁。他们是我瓦伦蒂娜·罗斯托夫斯卡娅姨妈的孩子。我另一位姨妈的丈夫早死了,他们说是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他当时只有三十多岁,我一直怀疑……”
“你不记得有一个叫叶夫根尼的表兄弟吗?”
“不,我只有两个表兄弟。”
“你没有任何名叫尤斯科维奇的亲戚?”
“那是你的姓名。”
“所以我才会问你。我要再问一次。你知道有个名叫尤斯科维奇的亲戚吗?”
“从未有过。没有。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亲戚。”
“很好。”他转向法官席。“我向被告提这些问题是因为某些对我们可爱的俄罗斯祖国的未来心存不轨的无耻之徒竟说我和被告有着某种关系。我希望将被告的以上回答记录在案,从而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再宣称我与这个卑鄙的家伙有丝毫的血缘关系。”
拍摄到此嘎然而止。摄影棚的大门被拉开,克莱夫来到了拍摄场地。他告诉他们只剩了最后一个长镜头需要拍摄,主要内容是被告的认罪和祈求宽恕。“我真的认为我们今天晚上应该尽可能结束全部拍摄工作,亲爱的。去喝点咖啡或是做点别的什么你们所愿意做的事。不要浪费时间或是耍什么花招。我们在45 分钟后开始。就45 分钟,我要求证人到时候准时到位。明白吗?一个也不准缺席。”
“我可不可以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邦德问。
“你可以去乘热气球,去滑雪,干什么都行,亲爱的,只要你在45 分钟后能赶回来。”
导演转过身去。“我不允许有任何托辞。”他转过头丢下一句话。
“我想回斯特拉特福去了,”纳特科维茨打了个呵欠说。“应该砍下他的脑袋,让克莱夫见鬼去吧。”
“你不出去吗?”邦德说着话已经在往电梯方向走去。
“太他妈的冷了,盖伊,什么傻话也不要讲,就像‘我也许会很久’之类的话,对不对?”
“我过45 分钟就回来。”
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抓起他的毛皮大衣,在他乘电梯下楼的时候把毛皮大衣穿在了身上。他觉得头很重,眼睛也很疼,这是半夜起床的结果。外面的寒冷天气很快就能让他恢复精神。
10 分钟后,特种部队十月营赶到了,他们伴着滚滚的轰鸣声从天而降,房顶几乎都要被震塌了。
17 007之死
似乎所有的人都站在通向摄影棚的宽阔大厅里。那扇金属大门打开了,克莱夫的几名助手正在对布景进行细加工。所有在剧中担任证人角色的人都已经被细心地化过妆。他们一边谈笑着,一边在喝着咖啡,还有的在吸烟。
邦德看到娜塔莎正和迈克尔和埃梅拉尔德站在一起,他们的装束乍看起来非常像老派的犹太人。纳特科维茨正在调试录音设备,尼娜却好像是消失了一般。
邦德刚才想出去散散步借以清理自己的思绪,他在去大厅出口的路上去了一趟洗手间。当事情开始的时候,他正要从里面出来。
如果他们已经在拍摄之中,就什么也不会听到,因为只要大门一关,整个摄影棚就会与世隔绝。但情况并非那样,只听得一阵阵巨大的引擎声从空中传来,那震动声使整个建筑物都随之颤抖起来。
一时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加入到了孩子们玩的“塑像游戏”中。一阵令人心悸的寂静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刚刚还在谈笑风生的人们转瞬间便呆若木鸡,仿佛木雕石刻的一般。香烟、咖啡、软饮料都在手里不动了,各种液体在一刹那都好像凝固了似的。
邦德一退身回到了空无一人的男洗手间内,顺手将外衣的拉链拉开并把自己的P6 型自动手枪掏了出来。他用拇指把手枪的保险打开,然后又将外衣的拉链重新拉好。他靠在门上想听听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外面的寂静已经被慌乱所取代。喊声、尖叫声、惊恐不安的人们失去控制后乱跑乱撞发出的各种乱哄哄的声音不绝于耳。邦德戴上自己的保温手套,把手枪更紧地抓在手里。
从大楼外面突然传来了很清晰的手雷爆炸声,接着又响起了枪声;自动武器的“哒哒”声和点射的“砰砰”声响成一片。接着又传来了跑步的声音,沉重的脚步声向大厅这边疾速而来。
邦德把洗手间的门又推开了几英寸,他看到了穿着一身伞兵迷彩服的鲍里斯·斯捷帕科夫,他的身后跟着一名表情严厉的高个子军官和一群士兵,邦德估计大约有六、七个。他们全副武装,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斯捷帕科夫的手贴近胯部握着一把最新式的PRI 自动手枪。其他人都带着AKS…74 步枪、手雷,以及挎在右肩上刀鞘内的长刀。邦德甚至还看到了一台R…350 型无线电话,就是具有编码和迅速发射能力的那种。只有斯捷帕科夫和那名高个子军官没有戴上跳伞服的兜帽,其他人全都蒙得严严实实的,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
看到他们跑了过来,那群证人和技术人员都开始往后退,闪出了一条通道。邦德在他的右侧看到了迈克尔·布鲁克斯正在向通往密室和地道的那扇门移动。只见他把后背靠在门上,把手伸在后面用钥匙开门,他一边开门一边向左侧瞟了一眼,正好与邦德的目光相遇,他摆了摆头,示意邦德跟他走,就在这时那扇门无声地打开了。
邦德只是看了他一眼,但他并没有跟过去。不一会儿,那个变节间谍的身影在密室中消失了。接着他便听到了斯捷帕科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