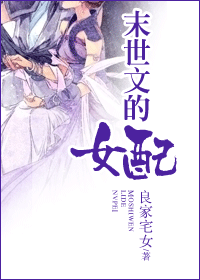71达尔文的阴谋 (全本)作者:[美] 约翰·丹顿-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加拉帕戈斯那可怕的几个月。内维尔是对的,他的天才——他的创造力——要胜过他的不屈不挠。就是那种异乎寻常的能力,让他能够追溯过去,用开阔的眼界,找到很多联系——这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一个模式出现了。他对事情做出推断;山脉是怎样形成的,世界是怎样在万古前形成的。他能够站在时间之外。这些想法突然从他的脑海中蹦出来,好像他眼前的真实景象,万物之间突然有了联系——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种创造力也许来自其他地方,也许来自工作本身,来自对它的迷恋。他是怎样一直8年都沉迷于对黑雁的研究,而逐渐形成了震动世界的学说的?工作赋予他这些。罗兰的话没错:达尔文所刻苦钻研的黑雁原本是雌雄同体的,最初的一代有两个橘黄色的生殖器官。达尔文如此入迷地——也许如此惊骇地——发现性别之分缓慢地进化了,而不像教堂要让我们确信的那样。上帝是那么计划的吗?微观和宏观。模式就是那么定的。不仅是把点连起来,像老话说的那样,而是能够先看见那些点。
休打开抽屉,拿出几张从网上复制的小猎犬号上的画像。有船员的画像,他已经开始知道这些人:菲茨洛伊船长,勇敢又有点疯狂;惠格姆上尉,戴着海军帽,洋洋自得;菲利普·吉德利·金,如拜伦般浪漫;杰米·巴顿,圆脸但高深莫测;十来岁的传教士马修斯,面如银盆,长发披肩。
他看着康拉德·马顿斯画的一些航船的水彩画。有一幅画的是停靠在塔希提岛上帕度提的小猎犬号。那个所在是一个平静的海港,四周棕榈树环绕。另一幅画是停泊在悉尼的道斯的一批船只,有些正准备扬帆远航。
然后,他想起了达尔文和麦考密克站在树边的那幅素描像。就在一瞬间他明白了它的意义所在。当然,它里面藏着个秘密。那是莉齐已经破解了的。多么愚蠢,以前怎么没想到。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幅画。关键不在画画的地点,而在于画画的人。那个画家是康拉德·马顿斯,而不是奥古斯塔斯·依阿尔。而马顿斯只是随航行走了一半的路在蒙得维的亚上的船。
就是这样!——这证明麦考密克在里约并没有弃船而去。他一直在船上,直到最后都在与达尔文唱对台戏——嫉妒,野心勃勃,毫无道德。而达尔文,对此撒了慌。莉齐是对的——她的父亲——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做出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欺骗行为。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达尔文的阴谋》作者:'美' 约翰·丹顿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二十二章
对于查理和菲茨洛伊来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后一天,正好向他们证明了小猎犬号整个航行的悲剧色彩。但是船员中没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没人能猜出这一天对于将来那些相关的人来说是多么地至关重要。
那灭早上,查理、菲茨洛伊和麦考密克乘一艘小船去了埃尔伯马尔——那座最大的岛屿,去考察火山。他们曾在远处观察过那些火山,为那直入云端的烟雾和断断续续的火焰而着迷。
埃尔伯马尔有5座火山,最大的沃尔夫是一座活火山。几天来它一直在震动,在隆隆作响。那天早晨,它喷出一股白色的烟云,足有l万米那么高,在空中散播开来,像一顶巨大的张开丁的帐篷。他们看着这一景象,被它的宏大所折服。一阵风吹起一片火山灰落在船上,将船变成了白色。
查理心急火燎地想尽可能靠近那个火山口,想从那儿收集些熔岩标本。那比散乱在火山锥体周围的那些普通的凝灰岩更具诱惑力。菲茨洛伊虽然因刚刚摔了一跤而仍心有余悸,也迫不及待地要开展开采汁划以证明他的勇气和决心。而麦考密克也不愿让在理独享荣耀,不愿自己被落下。
4个船员把他们送到了岛上,把船停在岸边。他们依令等在那儿,直到3人归来,不过显然他们都巴望着尽早离开。海湾表面掀起层层惊涛骇浪,仿佛就要沸腾起来一样。但这一切都没有减少他们探险的热情与勇气。
踏上海滩的那一刻,杏珲就感到有些不对头。直到他走到树带生长界线。回头再看时,他终于明白了不对劲的地方:沙滩上没有海狮——实际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踪迹,连鸟也没有。除了火山口深处断断续续在喷射之外,到处一片死寂。
他们想找一条上去的路,最后决定沿着 条干涸的河床前进。四处杂乱的岩石让他们无处落脚,不过还好没有树枝和藤蔓阻路。大约一小时以后,他们看到了路上铺满了蕨类和一丛丛的马樱丹,上面白色的小花已被焦热烤枯了。
菲茨洛伊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在前面开路,查理紧随其后——带着他的各类工具:一个小显微镜,一个指南针,一把地质锤,还有别在腰带上的手杖。麦考密克跟在最后,带着午餐,呼吸沉重。
最后他们来到了斜坡上的一片空地。他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个礁湖,末端被灰色的火山岩流围了起来。再远处是大海,远远望着,还能看到小猎犬号小小的身影。查理说那个礁湖曾经是一座火山的山口。
“喂!”他说道,“看这个。”他掏出指南针,把它放到一块岩石上。
了他们看到指针迅速转了起来。但它没有指向真正的北方,而是没头没脑地四面八方乱转。
“火山破坏了磁场。”他说。
“你感觉到震动了吗?”麦考密克问。他正坐着,手掌铺在地上。他听起来很紧张。
查理坐在那儿,也感到不停的震荡。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震荡不仅来自地层深处,而且好像也存在于他们周围的空气中。他知道,大气的这种骚动,是火山喷发的前兆。
菲茨洛伊从麦考密克的包里拿出一大块腌牛肉,用猎刀切成小片,分给每一个人,接着是撕下一片片的面包片。
“我们现在需要借酒壮胆。”他笑着说,一面在酒杯里斟满了红酒。
他们都已疲惫不堪,实在不愿意立刻就开始艰苦的跋涉。菲茨洛伊不停地倒酒,直到两瓶酒都被他们喝光,然后他们仰面躺倒,头枕着一块木头,把帽子盖到脸上。
过了些时候,查理睁开了眼睛。菲茨洛伊和麦考密克一动不动地躺着,还在睡觉。他觉得震动越来越强烈了,甚至闻到了空气中硫磺的味道。在后面的斜坡上,他看到一片凝固了的熔岩流。他爬起来,用锤子敲打着熔岩,撬出了一块光滑的黑镯石,他从上面切下一小块,放进了口袋里。
重新爬回来,他看到麦考密克已经醒了。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查理点点头,指向山顶。麦考密克站起来,没说话,也点了点头。他们一起开始跋涉,留下还在梦中的菲茨洛伊。他们周围震动又加剧了。
一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火山口顶。热浪扑面而来,将他们的脸映得通红,也使他们呼吸急促起来。透过带着硫磺味的烟尘,他们惊愕地向那深不见底的盘状盆谷内望去。周围一圈发亮的硬壳起伏不定,中央部位液状的红红黄黄的熔浆汩汩地冒泡,放射出一股高大的烟柱,伴着隆隆的响声。
下面20英尺的壁层处有些查理从未见过的火山岩,是深黑色的——一种古人在威苏维尔火山找到的熔岩。他看到有可能够到它们,火山口内的岩壁并不陡峭,人可以下至中部,往下有充足的立足之地,可以做到的。
有哪个探索者曾敢冒那样的险呢?
一段时间后,海滩上的船员已经消除了恐惧的情绪,取而代之的是厌倦和乏味。他们在沙滩上来回走动,很小心地不敢远离小船。后来,他们发明r些游戏来消磨时间,包括用标枪投掷水中的浮木。最后,他们都躺到了树荫里等待。
第一阵爆裂声来势凶猛,听起来像加农炮,只不过更迫近更响亮。他们紧张地转向海平线搜寻小猎犬号的身影。它还在原处。停泊在海湾的外围。
接着他们感到了震动,脚下的大地开始不再牢固。这种感觉令人不安。另一阵爆裂声伴随着一阵烟雾接踵而来。火山喷射出一片浮石,像冰雹一样砸在沙滩r,雪块一般的烟云紧随其后。
几个船员开始争辩该怎么办,他们不愿丢下船长,但却开始着手准备离开了。他们把船推向水中。3个人跳进船里,另一个还站在地上,手里抓着绳子。他们就那样等了好大一会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最后,他们看到山坡上两个倾斜的身影。他们跑到海滩上,跑着穿过沙地——是船长和阿哲。船员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没有第三个人。
就在预示着再一次喷发的爆裂声响起时,两人跑到了海边。他们激动不安而又气喘吁吁地上了船。
船长立刻下令:“离开,马上离开!”
回小猎犬号的半途中,一个船员大着胆子问道,“麦考密克先生呢?”其他几个都侧着身子倾听查理的回答。他一向温文尔雅,在这火山怒吼之际,话语尤显柔和。
“死了。”
那天晚上,查理和菲茨洛伊在船长室单独进餐,两人几乎一言不发。最后,仍紧张得吃不下饭的查理把餐巾丢到桌子上,尽量平静地说道:
“我不知道是否愿意把今天发生的事记述下来。他死得太恐怖了,他的家人得知细节后一定会悲痛欲绝——就是说,如果我们详细记录在航海志上的话。您不觉得吗?”
菲茨洛伊看着他,仔细打量他的脸色。
“在整个考察计划中,这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在理继续蜕道。“当然,海军部会问起的。您当然一定要通知他们,不过可以选择一种比较策略的说法。”
菲茨洛伊默不作声。他又在他这同餐之友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威势。
“我猜想您已告诉过他们,他告病回里约了。”
“是的。”
“订购也遭到了反对。”
“是的。”
“那样地结束生命实在是太恐怖了.我想恐怕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不要责怪自己”,船长回道,“我知道你已经竭尽所能丁。”
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就起航了,以每天150英里的速度飞速向西行进。在它剩下的周游世界的旅程中,一路平静无事。
最后,在一个阴雨的礼拜天,轮船从英吉利海峡起航向法尔茅斯驶去。菲茨洛伊在船上布置了最后一次礼拜仪式,以感谢上帝让他们平安归来。凼为外面的狂风暴雨,他们不得不在甲板下进行。船长读了《创世记》中的一些段落,其中包括亚当和夏娃的部分以及上帝发现他们的原罪时愤怒的话: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那天是1836年lO月2日。
《达尔文的阴谋》作者:'美' 约翰·丹顿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二十三章
1878年5月30日
亲爱的玛丽·安:
很久投给你写信了,为此我感到很抱歉。我没有任何借口可找——当然不是因为我太忙了。恰恰相反,我有时真不知该拿什么来填补我空虚无聊的生活。我已经不再给海格特的女囚犯念东西了,现在,我更多的是呆在唐豪斯。妈妈、爸爸和我,我们三个人的生活陷入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怪圈。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它有时让人觉得时光飞逝,有时又令人度日如年。我们通常会在早上7点半起床,中午就吃正餐。晚上,爸爸还是先下两盘双陆棋,大约10点半的时候,他先用力抽两下鼻子,接着开始擤鼻涕——非常准时,你都町以拿这个来对表了——跟着他就会七楼去,而我们也可以休息了。我现在总能在细微的事物中找到乐趣,有时还会连续几个小时沉醉在自己的冥想中。下面我给你举个例子。
今天正午时分,我陪爸爸一起去沙道散步。我们一起去散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像往常一样,我们穿过花园来到后院,左拐走过一道镶嵌在高高的栅栏中的木门,就踏上了那条小径。出于某种原因。我当时正处丁一种极为怀旧的情绪中,在回忆着那些遥远的过去。或许是在阳光下闪耀的某些东西刺激了我也说不定。
那条小径依旧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模样。开始的一段在阳光下沿着树林蜿蜒,仿佛在俯瞰着下面的山谷。一丛一丛的蓝铃花和牛眼菊点缀着草地,显示着大地已从季节的沉睡中醒来。在最远处是一座孤零零的夏日小屋。那可是一个梦幻王国,我们过去常常在里面扮成勇敢的王子和美丽的少女,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甚至还记得当时我们用粉笔画的那些模糊的龙骑兵。从这儿,爸爸和我开始往回返,只有这接下来的一段路我们是走在浓密的树冠下。小径像一条隧道,漆黑一片。这儿以前经常吓到我们,我记得小时候走在这段路上的情景:即将落下的夜幕把那监熟悉的树枝变成了各种鬼怪——树干中空的岑树,像一个食人恶魔;树干上长满瘤子的大橡树像一个奇形怪状的巨人。那时我通常跑过这一段去,远远避开那些可能刮到我头发的树枝,心在胸膛里直打鼓。
爸爸和我走了一圈后决定再走一圈。我心中的回忆也继续自发地排着队在脑海中一一掠过。我想起了春天刚生下的小羊羔的呜咽声,还有8月里准备收获时磨镰刀的嚯嚯声。五朔节时,我们挥舞着樱桃枝挨家挨户地索要硬币,然后在收获时节把它们藏到装草的大车里。我耳边仿佛叉响起槌球打在草坪上发出的沉闷响声,还有在露天的吉h赛篝火的灰烬中烤土豆时发出的咝咝声。有一次,爸爸带我去里真特街的一个展览大厅参观。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个潜水钟,还在一种新式的机器上称了体重。有个会吹玻璃的人给我做了一个漂亮之极的水晶马——可惜后来在回家的马车上碰断了一条腿。我当时大哭不止,爸爸把我抱在怀里极力安慰我,可一点用也没有。我还记得跟爸爸一一起去照相馆,当时还是盖达尔银版照相,我穿着白色的套装,头上扎着黑色天鹅绒的发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在屋顶上拍一张阳光下

![[现代女尊]达尔文的狐狸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