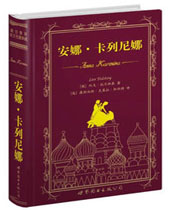罗丝安娜-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异化与质变,也正是史、华二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思索点。
《罗丝安娜》
1
七月八号午后三点,他们发现了尸体。从外观看来尸体相当完整,不可能在水里泡过很长的时间。
虽然他们的发现全凭偶然,但能这么快发现尸体,对警方的调查工作助益匪浅。
在伯轮运河的水闸下游,有一道阻挡东风长驱直入的防波堤。那年春天运河开通之后,这条通道就出现淤积的现象。不单是通行困难,船上的螺旋桨还老从河床卷出厚厚一团泥,任谁都明白这运河不疏浚不行了。其实早在五月份,运河公司就想自土木工程理事会征用一台挖泥船,但每个官员都视这申请书为烫手山芋,最后甚至推到瑞典国家海运部请示裁决。结果海运部认为这是土木工程理事会的工作,应自行解决,但土木工程理事会却发现所有的挖泥船都归海运部管,绝望之余只好求助于诺库平市的港口管理委员会。不幸的是,这申请书又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海运部,当然,它最后还是回到土木工程理事会手上。这会儿终于有人肯拿起电话,拨给一位对挖泥船了若指掌的工程师,他表示在现有的五台挖泥船中,只有一台能通过水闸。这艘名为“小猪号”的挖泥船当时正停泊在格拉瓦内市的渔港内。直到七月五号早上,“小猪号”终于抵达伯轮运河,停泊时还有一群附近的小孩及一名越南观光客在旁观看。
一小时后,一名运河公司的代表上船共商流程,一谈就是整个下午。隔天是星期六,大伙儿各自回家度周末,船只就原封不动地停在防波堤旁。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工头——就是奉命开船来的船长、一位挖掘师以及一个船员。后面两位都是高登堡人,一起从莫塔拉搭夜班火车来的;船长则住在拿卡,他的老婆还开车来跟他碰面呢。星期一早上七点,他们三人再次回到船上,一小时后开始挖泥工作。到了十一点,船底的货舱装满了泥后,挖泥船就驶向湖心卸泥。在回程途中,巧遇一艘向西行驶的白色小汽船抵达水闸,他们只好停船等待。船上的外国观光客都聚在栏杆旁,兴奋地向挖泥船上的员工挥手问好。那艘游船进水闸后缓慢地上升,往莫塔拉与维特恩湖移动。约午餐时间,汽船的信号旗才消失在最高的水门之后。直到一点半,他们终于能再度开工。
事情发生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天气晴朗温和,暖风阵阵吹送,夏日云朵也随之缓缓飘移;有些人聚集在防波堤上,有些则待在运河边。他们之中大半在享受日光浴,部分在钓鱼,另有两三个人注视着挖泥工作的进行。此刻,挖泥机的桶子正满装着河底的烂泥,穿出水面。挖掘师坐在船舱中,躁纵他再熟悉不过的机械;船长坐在厨房里享用咖啡,船员则用手肘撑着栏杆,站在甲板上无聊地对水面吐口水,挖泥的桶子正在往上移。
当桶子破水而出时,防波堤上有个人忽然向船的方向跑来,他挥动着手臂并大声喊叫,于是船员侧着头想听清楚些。
“有人在桶子里面!停!桶子里面有人!”
被弄糊涂的船员先是看着那个人,再回头瞪着已在货舱上方溢出污水的桶子。他也看到了——一条白色的、赤裸的手臂在桶子外面晃动。
接下来的十分钟是既漫长且混乱,有人站在码头上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什么都别做,不要碰任何东西,等警察来再说……”
挖掘师出来看了一眼后,就立刻回到杠杆后他安稳的座位上,启动起重机将桶盖打开,船长和船员上前拖出尸体。
是个女人,他们将她用防水布包着,面朝上地平放在防波堤上。受惊的人群马上跑过来围观,其中有些是不该在那儿的小孩子,然而竟没有人想到该叫他们走开。这时,只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的,那就是这女人的凄惨模样。
船员自作主张地在她身上泼了三桶水,日后在警方的调查陷入僵局时,有人就批评他当时的处置不当。
女尸全身赤裸,身上没有任何饰物,肤色显示出她常穿比基尼做日光浴,婰部颇宽,大退粗壮,陰毛则浓黑。她的胸部不大,有些松弛,侞头大而黑;从腰到婰部,有一道红而明显的刮痕,身上其他部位则相当光滑,没有任何斑点或疤痕。她的手脚相当小巧,没有涂指甲油;脸部则因泡水而肿胀,无法辨识出她原先的容貌。她的眉毛浓厚,有张大嘴,中等长度的黑发柔顺地贴在头上,脖子上有一缕发丝缠绕。
2
莫塔拉在维特恩湖的北端,是瑞典奥司特高兰省的中型城市,人口约两万七千。当地的最高警政首长是警务督察,同时身兼检察官的工作。在他之下有一名警察长,既是保安警察也是刑事警察的总长。警察长之下则包括一位九职等的首席探长,六位警员与一位女警。当中有一位警员津于摄影,另外若需要人手验尸时,他们通常求助于城里的医师。
发现尸体之后一小时,这些人大多已聚集在伯轮运河的防波堤上离灯塔几码远的地方。由于尸体周围人群拥挤,船上的人根本无从得知当时的情况,所以尽管船头已背向防波堤准备离开,船员仍在甲板上努力张望着。
在警用栅栏后面观望的人群,很快增加了十倍之多。栅栏的另一头停放着几辆车,其中四辆是警车,一辆是纯白的救护车,后门上还漆着红十字。一旁有两个人身穿白色连身装,靠在围栏上怞烟。他们可能是灯塔外的人群中,惟一对命案不感兴趣的人。
医生在防波堤上收拾工具,一边和瘦高、灰发的警察长聊天。
“现在我还无法看出什么端倪。”医生说。
“一定得把她留在这儿吗?”警察长拉森问。
“这由你决定…!”医生回答。
“这里应该不是犯罪的第一现场吧!”
“好吧,”医生也同意,“那他们载她去太平间时,麻烦你押车。我会先用电话联络好一切。”
他收拾好后先行离去。
警察长转过身说:
“艾柏格,你会先封锁现场吗?”
“当然会,真是倒霉!”
警务督察站在灯塔旁一声不吭。他通常不会一开始便介入调查,但在回城途中他说:
“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拉森没点头。
“艾柏格会一起办这案子吗?”督察又加一句。
“他是个优秀的人选。”警察长开腔了。
“当然了。”
谈话就此结束。停车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之后督察拨电话给林策平郡长,而后者只说了一句:
“我等你的消息。”
另一方面警察长和艾柏格做了番简短的讨论:
“我们必须先查出她到底是谁。”
“是的。”艾柏格说。
随后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消防队征用两个蛙人;然后,他打开一份港口抢案的报告,这是个即将结案的案件。他站起来走向值班警员问:
“有没有失踪人口的案件?”
“没有。”
“也没有人登报找人吗?”
“没有特征符合的。”
艾柏格走回办公室等着。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了。
“我们必须申请验尸。”是医生打来的。
“她是被勒死的吗?”
“我猜是。”
“有被强暴吗?”
“应该有。”医生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而且凶手相当细心。”
艾柏格边咬着食指指甲边想,他的休假从这星期五开始,他老婆还为此兴奋不已呢!
医生误解了他的沉默。
“你很惊讶吗?”
“不会。”艾柏格说。
挂上电话后,他走进拉森的办公室。跟着他一起去找督察。
十分钟后,督察向郡长要求法医的解剖许可,郡长立刻和法医学会联络。验尸过程是由一位七十岁的教授主持,他从斯德哥尔摩搭夜车赶来,不过看来津神奕奕,神采飞扬。整个验尸过程长达八小时,他几乎未曾休息。
教授写了份初步报告,其总结如下:
致命原因为残暴的性攻击后加以勒毙。有严重的内出血。
至此时,艾柏格桌上堆满的调查报告都只说明一件事:在伯轮运河的水闸下游发现一具女尸。
在当地以及附近邻区都没有人口失踪的记录,至少没有和死者特征相符的。
3
清晨五点十五分,雨天。马丁…贝克花了比平常久的时间刷牙,将嘴里的残垢清洗干净。
他将他的衣领扣上,系好领带,无津打采地审视镜中的自己,然后耸了耸肩走进走廊。穿过客厅时,瞥了一眼昨夜熬到很晚做的模型船“丹麦号”,才走进厨房。
他的脚步又快又轻,既是因为习惯,也是怕吵醒睡梦中的小孩。
他在餐桌旁坐下。
“报纸送来了吗?”他问。
“六点前是不可能的。”他老婆回答说。
此时外面天色已亮,但一片乌云密布。厨房里的光线灰暗而陰沉,不过他老婆并没有开灯,还说这是节约能源。
贝克欲言又止,因为说了免不了又是一场纷争,这可不是吵架的好时机。于是他用手指轻敲桌面,看着空茶杯上的蓝玫瑰花纹,在杯沿处有个小缺口,往下延伸了一条棕色的裂缝。这茶杯和他们的婚姻年纪相当,已经超过十年了。她很少打破任何东西,即使有也一定可以修好;奇怪的是小孩也都如此。
这种习惯也会遗传吗?他不知道。
她从电炉上取下咖啡壶,将他的茶杯注满。贝克停止敲打桌面的动作。
“你不吃个三明治吗?”她问道。
他小心地啜饮一口咖啡,放松地靠坐在桌边。
“你真的该吃点东西。”她坚持说。
“你知道我早上根本吃不下。”
“无论如何,你应该要吃。”她说,“特别是要为你的胃着想。”
他用手摩擦脸颊,感觉到被刮胡刀遗漏的胡茬子,接着又喝了口咖啡。
“我可以帮你弄几片土司。”她建议说。
五分钟后他把茶杯放回碟子上,无声地将它移开后,抬头看着他老婆。
她的睡衣外裹着一件毛茸茸的红浴袍,坐在桌边将手肘放在桌面,两只手托住下巴。她有头淡黄色的秀发、光滑的肌肤、一双圆而微突的眼睛。通常她会画深她的眉毛,但夏天时它们显得很苍白,就像现在,几乎和她的发色一样谈。她比贝克大几岁,所以即使近年来她胖了不少,颈间的皮肤也已有下垂的迹象。
从十二年前她女儿出生后,她就放弃了建筑事务所的工作,自此,她再也没有工作的念头。她的儿子入学后,贝克曾建议她找份兼差,但她认为薪水一定很微薄,还不如当个家庭主妇,快乐又自在。
“哦!是的。”
贝克边想边起身,将蓝色的凳子轻轻放回桌下,然后站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蒙蒙细雨。
停车场和草坪下面,就是空旷平坦的公路,地铁站后面山坡上的公寓,多数都还暗着。低沉灰暗的天空下有几只海鸥在盘旋。除此之外,窗外了无生趣。
“你要上哪去?”她说。
“莫塔拉。”
“会去很久吗?”
“天知道。”
“为了那具女尸?”
“没错。
“你认为到底要去多久?”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就报纸写的那些。”
“你非得搭这班火车吗?”
“其他人昨天就出发了,我可不能落单。”
“他们会跟以前一样载你去办案吧?”
贝克不耐烦地深吸一口气,瞪着外面,雨渐渐停了。
“你住哪儿呢?”
“城市饭店。”
“谁和你一块儿?”
“柯柏和米兰德,他们昨天出发。”
“开车吗?”
“是的。”
贝克听到后面传来她洗那个蓝玫瑰花纹杯的声音。
“这星期我要付电费,小的那个也要付骑车的费用。”
“你那儿没钱吗?”
“你知道我不想从银行里提钱。”
“我可不知道。”
他从内层口袋里拿出皮夹,打开来看一看,拿出一张五十克朗的纸币,瞄一下,却又放回皮夹,再把皮夹塞回口袋。
“我讨厌领钱。”她说,“从银行提钱会让我们的节约计划泡汤。”
他又把那张钞票拿出来折好,转身放在餐桌上。
“你的行李打包好了。”
“谢了。
“多照顾你的喉咙,现在正是发病的季节,特别是晚上。”
“好的。”
“你要带着那把可怕的手枪吗?”
是的,不是;也许会,也许不——有什么差别吗?贝克自己想着。
“你在笑什么?”她问。
“没事。”
他走进客厅,把壁橱上锁着的怞屉打开,拿出那把手枪,放进他的皮箱,再把怞屉锁好。
那是一把普通的点七六华瑟式手枪,有瑞典的使用执照。其实大半时候用不着,而且贝克的准头很差。
他走回走廊穿上风衣,再把深色帽子夹在手中。
“你不向鲁尔夫和小子道别吗?”
“叫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小子’是很荒唐的。”
“我觉得好听嘛!”
“吵到他们不好,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件事。”
他戴上帽子。
“我走了,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再见,保重身体哦!”
他在月台上等地铁时想,他一点也不介意出差办案,只是他的模型船“丹麦号”才完成一半。
马丁…贝克并不是凶杀组的组长,也没有那个野心,有时候他怀疑自己能否当得上,尽管除非他死了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职位已非他莫属。他是国家警署的首席探长,也在凶杀组工作了八年,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内最能干的警探。
他已经当警察半辈子了,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在雅各警局任职,六年后调到斯德哥尔摩,在不同巡区担任巡警官。之后他被保送国立警察学院,在那里他的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警探,那时他才二十八岁。
就在那年他父亲过世了,于是他搬离市中心租赁处,住回城南的老家,好照顾母亲。那年夏天他邂逅了他老婆。她和朋友在一个岛上租屋居住,而他恰好驾独木舟经过。他陷入了爇恋。那年秋天,他们想
![(安娜·卡列尼娜同人)名流之家[安娜]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80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