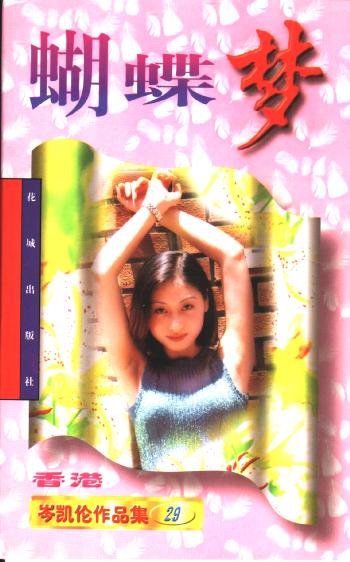蝶梦-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反正是要告诉我家馆主的,先和我说一下,怎么不行?”
“反正是要告诉你家馆主的,等她回来我再说,又怎么不行?”
“我回我自己的地方,想求个安静,怎么就是不行?”
吵得乐在其中的两人,循声往门口看去:
“馆主!”苑儿惊喜地顿住脚步。
“离小姐!”孟白恭敬地站起身来。
离春一手扶着门框,没精打采地跨进门来:
“你们两个眼里,居然还看得见我啊?”
苑儿跳过去扯住主人衣袖,整个人贴在她身上,扁嘴道:
“馆主,他欺负我!”
生着胎记的脸一偏,眉毛挑起:
“你不去欺负人,已经令我欣慰了。”
孟白重新坐在椅上,拍手赞同:
“还是离小姐讲道理!”
那双鬼眼斜过来:
“若你意犹未尽,定要完成这场未竞的争论,我给你一柱香时间。”
要说这两人,性子虽然活泼,却也懂得察言观色。一见这情形,都蔫下来,不敢造次了。离春左右看看,挑孟白旁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嘴里唤着:
“苑儿啊,去帮我弄些吃的来吧。这一整天,几乎水米未进。”
“你又这样轻忽自己的身体?!”这丫头急起来,立刻反仆为主。
“与那群封家人谈得太过投机,”苍白到青惨的脸上,自嘲一笑,“不知不觉就忘记了。”
“你啊……”苑儿抱怨一声,就奔去厨房寻觅吃食了。
离春抬起手臂搭上桌子,长袖垂下,对孟白瞟去一眼:
“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了吗?”
目送苑儿背影消失,这厅中只余两人了,孟白才领悟到自己面对的,是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的乱神馆离娘子,方才吵嚷时的兴奋,已被丝丝寒气压下,又回到平时低着头口称“离小姐”时的拘谨。
“您还记得,回去等一个月的那位锦衣公子吗?”
“还用特别‘记得’?今天上午的事情……”
“果然如您所料。他这三个月四处寻宝,被母亲阻拦,不堪其扰下,竟然将生身之母软禁起来。家里一名忠心的丫鬟,趁着他今天出门来这里的空隙,将主人放了出来。老人家在这丫头的搀扶下,直接来到京兆府衙,状告儿子侍母不敬,不听劝告,在家中胡乱翻掘,将好端端的祖宅弄得不成样子。这位公子出了馆门,没有两步,就被拘到公堂上。上面刚喝问一句‘你为何这般不孝’,他就吓得伏地颤抖,一古脑全招了。原来他曾多次看到自己的父亲蹲在床边,不知摆弄些什么,如果恰好有人来,就慌忙藏起手里的东西。于是,他便臆测自己要找的,就埋在床底地下。而且,那些日子里,他父亲恼他整日游手好闲,眠花宿柳,就扣下他的月钱,想切断财源,逼他走正路。这样一来,他对银钱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如果能够得到他惦念已久的财富,自然很好;再能顺便掌家,以后都不必受人掣肘,就更是一桩美事。打过如意算盘,正巧父亲偶感风寒,煎药时就下了毒。得手之后,他迫不及待搬开那床,掀起砖石,下面有只木盒。里面却只是一些手稿,是他爹年少为官、意气风发时,所作的诗词,还夹着些追求他娘亲的日子里,两人互通的信件。约莫是年纪大了,怀念过往,又不好意思让人知道,就死了个冤枉。也正因这不孝子白白杀了人,却找不到想要的,自然急切焦躁,这才露了马脚。”
此案前前后后,与离春先前的猜测全无二致。孟白描述时,也掩不住目光中的钦服,但听者非但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有些迷惑:
“怎么?他真是凶手?”
孟白惊得张大嘴巴,几乎说不出话:
“可是您早先说得条理分明,证据确凿……”
“那样也叫‘证据确凿’的话,这世上又不知要多冤死多少人了!”离春凝眉反思一通,“虽然推断得颇有道理,但我原以为那公子只是懵懵懂懂被人利用,而幕后主使另有其人——比如某位与他有共同利益,却彬彬有礼、口碑极好的同胞兄弟?换言之,我是期待真凶是一个更加聪明的人,一个更加懂得隐藏的人,一个如我一般有些‘乱神’气质的人,而不是那样恶行外露的。想想那人,做坏事都到处招摇,这样毫无深度,居然也能作凶手?唉……”无奈长叹一声,“等大理寺杜大人回来,我定要向他哭诉:是不是那些稍有心机的犯案者,都被你抓得干净了?”
孟白哭笑不得劝说道:
“离小姐啊,人家没有拆掉你的乱神馆,已经仁至义尽了。”
“噢?是吗?当年他要拆的时候,我也没拦着;现今我要他拆,他也不敢啊。”
离春起身,在厅中走动两步,微微一笑:
“说起这个,倒要谢谢你呢。帮我瞒住苑儿,不叫她知道。”
孟白羞愧地低头:
“也没多想什么,只是平时和她兜圈子兜惯了……”
“那丫头——你我都知道——每日蹦蹦跳跳,精灵古怪的,真让她获悉此事,非得去瞧热闹不可。她是没什么别的心思,但只要出现在围观人群里,被京兆府尹看见了,必然以为是我授意,要去抢他难得的功劳的。那何大人小肚鸡肠,嫉贤妒能,又非止一日了。真要惹上,就更添麻烦。”
“离小姐不须为这等人忧愁……”
离春摇头,笑出几分傲慢:
“对强于自己的人,略有敌意,不过是人心小小的晦暗,连肮脏都谈不上。如果这样也忧愁,那终日面对这一件件中人欲呕的事情,我愁也早愁死了。”
孟白虽知离娘子一向自视甚高,闻言也不禁气恼,只因刚备下的几句劝慰之辞,没了用武之地。搜刮心中积存的名目,似再也无话可说。偷偷望了眼内间的帘子,不见人来挑动,正要告辞时,离春开口问道:
“对了,关于那个封家……”
“哦。今天刚打听了两句,就叫方才那件事给耽搁了。只能说有了点眉目,但还不很确定。等我多问些人,再告诉您切实的消息。”
“好。”离春称许道。
苑儿端着碟子撩帘出来,厅里已见不到除离春外的第二人。不禁转着头寻找了一圈,眉梢嘴角微微垂下来,把手里东西撂在桌上。
离春偏头看去:
“这是什么?”
“馆主怎会不认得?这是近日来一直吃的胡饼啊。”
“就是近日来一直吃它,才不敢相信今日依旧……”
“那有什么办法?你又没有事先吩咐,一下子哪儿来得及准备,只好出去买了。城西本就多胡人,只好找些他们的吃食。想要煎炒烹炸的菜色,要到城东去呢。”
“好了好了,我就不挑剔了。”
离春执起胡饼,咬了一口。
苑儿再三往门口张望,终于忍不住问道:
“孟白人呢?”
“已经回去了。”
“怎么走得这样匆忙?”
“再过些时候,就要闭坊门宵禁了,你还指望他能呆多久?”
“我是说,连声招呼也不打,亏我还给他也备了一份。可现在……唉,也不能浪费了。”
妙目一飘,离春立刻摆手:
“你不必看我。我食量小,手里拿的这些足够了。”
苑儿叹口气,神情懈怠,但没一会儿,眼神又灵动起来,坐在方才孟白的位置上,贴着桌面向离春滑近:
“馆主啊,他都和你说什么了?”
“向我讨了你去作妻子,”不顾对面瞠目结舌,离春扔下咬了几个缺口的胡饼,继续一本正经,“他自然是没说。”见苑儿抬手要打,忙往一旁闪避,“他只是来告诉我,拜托他调查封家的事,还没有进展。”
苑儿的嘴张得更大:
“辛辛苦苦跑来一趟,只为了一句‘没有’进展?真是服了他。难怪不肯和我讲了,一定怕我笑他办事不牢。”
“嗯,或许吧。”
“不过,这人说话一向不知坦白,想从他口里知道什么,真是难了。”
离春平淡一笑:
“他若不说,你也可以自己问他。”
“那人,嘴紧得像蚌一样,怎么问啊?”
“你一个劲儿扯着他念叨‘告诉我吧’,自然是不行,总要有些手段的。”
“手段?用了呀。我满不在乎地对他说‘哼!你能有什么重要消息?只是向我吹嘘的吧?’”
说着把自家馆主当作孟白一般斜睨着,眼中光点不停闪烁。离春摇头无奈道:
“你若要表示不屑,歪他一眼也就够了。如你这般,不到一盏茶时间,瞟他数十回,不要说是他,我都禁不住想刁难你了。”
“馆主……”
“若要从别人口中套出些事情,须牢记我乱神馆的准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这我也知道。有时听你说话,只觉得精妙,心里也佩服向往,但到我自己这里,却总是……”
苑儿慢慢摇头,离春却微笑:
“这便是天性了吧?机灵精明,你是足够了,但是心机全无啊。虽说跟了我这么久,该没有的,还是一点没有。”见眼前人张口欲分辩,笑意更深,语调却愈加懒散,“不过,话说回来,心机越少的人,越容易活得逍遥自在,倒是令人羡慕啊。”
“哦?馆主今日怎么有感慨的兴致呢?”
“只是发现,人与人,真的天差地别。自封家回来馆中,看见你与孟白在吵嚷……”
苑儿略低下头,眼色柔和:
“真是对不住,你在外面那样劳累,我们却还搅扰你。”
“当时,倒是没有觉得喧闹,心里反而颇为欣慰——我身边的,是这样的人啊!不像今日见到的那些,几乎个个都是遣辞造句的行家里手。若镇日里被他们围绕,一举一动,只怕都要用尽心机,谨小慎微了。这样的日子,我倒是十分心仪,但过起来,到底不够安稳。不知道那封家夫人,是不是如我一般想法?”
这一番话,挑起苑儿的兴致:
“怎么?今天遇到的,都是些满腹机心的人吗?”
“称不上满腹机心,但心底的小算盘,各自倒都敲得挺响。你知道,‘一句话,十样说’,这至理名言在他们身上,可真印证到底了。举个例子,你刚才所言,‘孟白是坏人’这话……”
“我可没这样说!”
离春不理:
“他们可以说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语调忽变,一下子显得说话人小心谨慎,深谙进退,“‘离娘子,你看这孟白,说话从不坦诚,总好像藏着些什么,这样的人,若还不是坏人,倒真不知怎样的才是坏人了。’”余音未落,又还回离春独有的阴柔嗓,“会这样说的,便是丫鬟红羽。”
苑儿皱眉:
“不知怎的,听这话音,我便不喜欢她。”
离春不予置评:
“若是赵管事,他必然会说‘我一向对面相学颇有研究。人言相由心生,看孟白这张脸,真是诡异。再观他言行举止,也耐人寻味……’一直没人搭腔的话,他便会旁征博引地,一路说下去,只是绝不吐出‘此人并非善类’这种话语。一旦有人顺着他的语意,接茬说:‘这么说来,孟白是坏人喽?’他就会一边分辩‘这可是你说的’,一边焦急摆手,其实心底暗笑不止。”
揣摩着离春学来的语音,苑儿的眉头皱得更紧:
“这调调,让人觉得张口欲呕,又什么都吐不出。”
“不错。”离春点头,“如同一只癞蛤蟆,趴上你的脚面,不咬你,却活生生恶心你。”
苑儿清脆笑开来:
“这比喻,倒是贴切。”
“算了,吃着饭不提他,改说他家老爷。我很怀疑,他会不会说出‘某人是坏人’这样的话。要是别人这样说了,他反而会替那人鸣冤。自顾不暇,居然还有心思去悲悯别人,真是有点意思!虽然那一身的凄切,会带得他人情不自禁伤感起来,但比起他委以重任的管事爷,倒令人愉悦得多!”
“管事‘爷’?馆主不是最蔑视这些敬称的吗?”
“不是我要这样叫,而是自长工莫成那里学来的。那人讲话,倒是不会转弯,有什么就直说出来,‘孟白是坏人,孟白真的是坏人’,就是这样简单。但言谈之间迸发出的热情,好像这人拼了命般,不遗余力地相信自己所说的。所以,即使出自他口的,是最荒谬不过的言论,却也叫人深信不疑。”
“我刚刚对这人有些赞赏,听你这么一说……要对付这样一群人,难怪累坏了。”
离春笑得自负:
“别说只是这种程度,就算真的精似鬼,比起巧言令色来,又有哪个是我的对手?这不同性子的人,就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有一种人,想主动把事情告诉你,但不会一古脑全说出来。太急切地把消息全扔给你,怕你反而起疑,就一点点,慢慢告诉你,并诱导你自己去想。亲历亲为思索出的东西,总不会不信了。”
“这人是,红羽?”苑儿猜测。
“是。这样的人,期望你信她,你便应该作出十分信任,甚至感恩戴德的样子,夸奖她观察入微,描述得体,仿佛她说出来的事情,令你受益良多,豁然开朗。她一见这样,就会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具功效。但是,她要是认为,你已经完全相信了她,就极可能藏起一些,不说出来。所以,也不能一味赞扬,还要在语气里,留下一丝怀疑的尾巴,比如,说她聪明时,刻意摄人些、叵测些。如此这般,自然能让她心中打起小鼓,以为你已经对她如何弄鬼心知肚明。可话没有说开,她也不好解释,只好比原先计划的,更多说一点了。”
“我本以为,与人说话,不过是上下嘴唇相触碰,可没动过这么多心眼。现在听了这些,真是有理啊。一字一句都要精细至此,怪不得人都说馆主你是妖魔鬼怪了。”
苑儿嬉笑,却现出几分畏怯。离春没有多余的心思去在意,她已完全沉浸在计算中,眼神悠远,眸光闪动,与脸上胎记相映生辉:
“也不知今日埋下的那面鼓,敲得怎样了,总觉得她还有些事闷在心里,没和我说。不过,总而言之,这种类的人,算是容易对付的。另外一种嘛,比起向你倾吐来,更偏爱探你的口风。云山雾罩说了一堆,清楚明白的一句没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