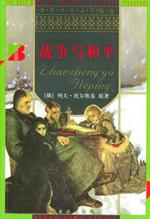战争猛犬-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舱内出来,使劲拉开了门。一顶法国军帽伸了进去,巡视了一下机舱,军帽底下的
鼻子因舱内难闻的气味而皱了起来。那个法国军官的眼光停落在五名雇佣兵身上。
他向他们招手,让他们跟随他上停机坪。当他们踏上陆地时,那个军官对副驾驶做
个手势关上门,旋即,DC—4 又向前左右颠簸着绕着机场开往机场主楼。一队法国
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正在那儿等候接收飞机上的孩子们,好把他们带往儿童医院。
当飞机摇摇摆摆地经过五个雇佣兵身边时,他们一齐向站在舱板上的范·克里夫挥
手致谢,随后转身尾随那个法国军官走了。
他们必须在那些小屋里等上一个小时。他们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头椅子上,这
时,几个年轻的法国军人从门缝里窥视他们,看一眼那几个“Lesaffreux”——他
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称呼那些形容可怕的人。雇佣兵们终于听到一辆吉普车发出长
而尖的声音在门外停住了,接着是在过道上立正的劈劈啪啪的脚步声。最后门打开
了,进来的是一个晒得乌黑、面容冷酷的高级军官,身穿热带的浅黄褐色军服,头
戴顶上缀着金镶边的法国军帽。香农留神到他那双睿智的、飞快瞥来的眼睛,军帽
下的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伞兵的翼形徽章别在胸口五排勋章绶带上。塞姆勒一
见就迅速立正,站得笔直,下巴朝上,五指也笔直地放在裤子裤线的地方。香农不
需要别人告诉他来者是谁,因为来的正是传奇式的勒·布拉斯。
这位身经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牌军人和每个雇佣兵都握了握手,在
塞姆勒面前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AIDrS (哦),是塞姆勒吗?”他温和地说,脸上慢慢漾起笑意,“还在打
仗。不过,不再是副官,我想,现在该是上尉了。”
塞姆勒不安。
“Out mon Colnmandant (是的,司令官先生),不过,我是上校了——只是
临时的。”
勒·布拉斯沉思地点了几下头。随后他向他们大伙儿说:“我会让你们住得很
舒服的。不用说,你们需要洗澡、刮脸,吃点东西。你们显然是没有换洗衣服啦,
衣服会供给你们的。恐怕你们暂时只好待在你们的住处不能出去,这只是预防措施
罢了。城里有许多新闻记者,同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触。一旦办妥,我们就
安排你们坐飞机回欧洲去。”
他要说的都说了,于是就打住话头。他把右手的五个僵硬的指头伸向帽檐,然
后就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坐上四周遮严的货车,从后门进了他们的住所。他们住在
甘巴大饭店顶楼的五间卧室里。这是一家新建的饭店,离路对过的机场主楼才1000
码,因此离市中心还很远。陪他们同来的年轻军官告诉他们就在这层楼吃饭,并且
待在那儿听候通知。1 个小时以后他又回来了,带着毛巾、刮脸刀、牙膏、牙刷、
肥皂和海绵。一托盘煮好的咖啡也送来了。每个人都快快活活地泡在冒着热气、发
出肥皂香味的大浴缸里洗澡,这是六个月来第一次洗澡。
中午,一个军队里的理发师来了,还有一个下土捧来一堆长裤、衬衫、背心、
短裤、袜子、睡衣和帆布鞋,他们把这些衣服鞋袜都试穿了一遍,各人拣了合适的
留下,然后那个下士就把拣剩下的拿走了。那个军官和四个侍者一起端来午餐,并
且关照他们不要走近阳台。万一他们想活动一下身体,也只能足不出户。他说,虽
然不能答应拿英国或南非的书和杂志,却还可以带些经过选择的书和杂志来。
自从上一次战后休假以来,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还从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
吃完饭,这五个人就钻进被窝睡着了。当他们睡在还不习惯的褥垫和难以置信的被
单上打呼噜时,范·克里夫在薄暮中把DC—4 离停机坪,飞出了一英里,经过甘巴
大饭店的窗口,又向南往纳米比亚的卡普里维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飞去了。他的任
务也完成了。
实际上,这五名雇佣兵在那家饭店的顶楼住了四个星期。同时,报界对他们的
兴趣也消退了。记者们被编辑叫回他们的总社,因为编辑们觉得,把记者留在一个
没有新闻可采访的城市里毫无意义。
一天晚上,勒·布拉斯司令官总部的一名法军上尉没有预先通知就来找他们。
他笑容满面地说:“先生们,我给诸位带来了好消息。诸位今晚将飞往巴黎。诸位
将坐23点30分的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
这五个对漫长的禁闭厌烦得发狂的人听罢都欢呼起来。
飞往巴黎需要10个小时,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和法国的尼斯要停两站。次日早晨
快到10点的时候,他们到了布尔歇机场。时值9 月中旬,机场上寒冷的晨风呼呼地
刮着。在机场的咖啡室里,他们互相道别。杜普里选择坐长途汽车先到奥利,然后
买一张单程票坐下一班的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去。塞姆勒愿
意和他同行,不过他至少要先回慕尼黑去看看家。弗拉明克说他想到诺尔车站去,
坐直达布鲁塞尔的头班车,然后到奥斯坦德去。朗加拉蒂打算到里昂,搭火车去马
赛。
“让我们保持联系吧。”他们说,眼睛全盯着香农。他是他们的头儿,全靠他
去找活儿,签订下次的合同,打下一次战争。同样的,如果他们当中有谁听说和这
一伙人有关的事而要和某个人联系,那么他首先想到的也就是香农。
“我在巴黎待几天,”香农说,“在这儿找临时活儿的机会比伦敦多。”
接着他们交换了地址,邮局待领邮件地址,或者是一个酒吧的地址,酒吧的侍
者可代传信函,也可以保存信件,等收信人来喝酒时取走。然后他们分道扬镰了。
由于他们从非洲回来的消息很保密,因此没有记者在等着他们。可是,有一个
人却听说他们回来了,他一直在等着香农。这时,在别的雇佣兵都走了之后,他们
的头儿才步出终点站的大楼。
“香农。”
喊名字的声音是法国腔,语气也不客气。香农转过身来,看见离他10码远的地
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把眼睛眯缝起一点儿。那个人长得很粗壮,唇上长着下垂的
胡须。他穿着抵御寒风的厚外套,走上前来,直到两人离着大约两英尺面对面地站
着。从两人互相打量的神态看,他们谁也不喜欢谁。
“鲁。”香农说。
“哦,是你们回来了。”
“不错,我们回来了。”
那个法国人轻蔑地笑了,说:“你失败了。”
“我们没有办法。”香农说。
“我的朋友,我有一言相劝,”鲁忿忿地说,“回到你自己的国家里去吧,别
在这儿待着。待在这儿是不明智的。这是我的城市。要是这儿有什么合同可订,我
头一个会听到信儿,我就包下来,然后去挑合伙人。”
香农没有作答,只是走向等在街边的第一辆出租汽车,他把手提包放进车里。
鲁尾随着过来了,脸都气青了。
“听我说,香农,我警告你……”
那个爱尔兰人又转过脸来对着他。“不,鲁,你听着。我想在巴黎待多久就待
多久。在刚果时我从来也没有被你说动过,现在也不会被你说动。拿出你的本领来
吧!”
当出租汽车开走后,鲁在后面忿然地盯着那辆车。他喃喃自言着大步走向停车
场里自己的汽车。
他点上火,挂上档,在车上坐了好几分钟,两眼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
“有朝一日我把这狗杂种宰了。”他喃喃自语。不过,这个念头似乎并不能使
他的心情变得更好些。
一
在支着蚊帐的帆布木架吊床上,杰克·马尔罗尼搬动着一大堆自己的东西。他
看见东边的树林上空有一道闪电停留了一下。那儿有一道模糊不清的围篱足以勾勒
出遮蔽着那一片空地的树林子。他抽着香烟,嘴里诅咒着他周围的原始森林。他像
所有久居非洲的人那样,又自问干嘛要回到这个讨厌的大陆来。
如果他认真分析,就得承认他在别的地方也住不下去。不用说,他不能住在伦
敦,甚至在英国,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住得下去。他不能过城市生活,因为那儿的清
规戒律、各种捐税,还有寒冷的气候都使他感到不快。像所有久居非洲的人那样,
他对非洲有时爱,有时恨。不过他承认,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已经喜欢上了非
洲。在这么多年里,他离不开疟疾、威士忌和数不清的昆虫的叮咬。
他是1945年从英格兰来的,那一年他25岁。在这之前,他在英国皇家空军里当
过五年钳工。那时有一部分空军在加纳的塔科拉迪,他就在那儿装配过被打坏的
“喷火”战斗机,让那些飞机到东非和中东作长途飞行。那是他初次见到非洲。1945
年9 月他退伍了,领取了一笔退伍金,告别了天寒地冻、粮食配给的伦敦,搭上了
开往西非的轮船。有人对他说,到非洲能交上财运。
他并没有发财,倒是在周游了这块大陆之后,在贝努埃高原获得了一项小小的
采锡矿特许权,那儿离尼日利亚的乔斯8 英里。当时,马来亚仍然处于紧急状态,
所以锡很贵,价格看涨。他和尼日利亚的土著工人并肩干活。因此,一些殖民者的
太太们在英国俱乐部里闲聊时说这证明了大英帝国末日将临,说他“采取土人的生
活方式”,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表现”。这倒是真的,马尔罗尼确实喜欢非洲生活
方式。他喜欢丛林,也喜欢那些非洲人。那些非洲工人似乎不必去考虑会遭到他的
吼骂,或者被他打耳光、被迫去干更多的活计。他也和他们一起坐着喝棕榈酒,他
不但没有蔑视那些部落的戒律,而且还遵守那些戒律。1960年,在尼日利亚独立前
后,他的采锡矿特许权期满了,于是他给一家公司当管理人员,那家公司在附近拥
有更实惠的采矿特许权,名叫曼森矿业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到了1962年,那项特许
权也到期了,他就被雇作曼森公司的职员。
他已年到半百,却依然身材魁梧,臂力过人,身强力壮就像一头牛。他的手很
大,因为成年累月在矿里工作,手上都被划破结成了疤。这会儿,他用一只手划拉
着卷曲的灰发,另一只手把香烟在吊床底下潮湿的红土上捻灭。现在天亮了一点,
快要到黎明了。他能听到他的厨子在空地的另一头生火。
尽管马尔罗尼在采矿学和工程学上都没有学位,可他把自个儿叫做采矿工程师。
其实,这两门学科的课程他倒是都学过,并且还学过大学里不会教授的学问——25
年艰苦工作的经验。他在南非的兰德掘过金子,在赞比亚的恩多拉城外采过铜矿,
在索马里兰钻探过珍贵的水,还在塞拉利昂搜寻过钻石。他能凭直觉辨认出不安全
的矿井,靠鼻子闻就能识别哪儿有矿石。至少,他自己这么说;并且等到傍晚他照
例从贫民窟里取走20瓶啤酒后,没有人会为他下的这一断言而去和他争论。事实上,
他是那儿最后一个老勘探人员了。他心里明白,“曼联”——这家公司的缩写——
给了他一份微贱的工作,这份工作要到离开文明社会很远的幽深的丛林和荒僻的腹
地去,并且必须—一勘探清楚。不过,他喜欢那样的生活。他喜欢独自一人工作;
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最近的工作当然是称心的。三个月来他一直在一个山麓小丘探查矿藏,那条
山脉叫“水晶山”,位于西非海岸的一个小飞地,赞格罗共和国的腹地。
他被告知到水晶山周围的什么地方去集中勘探。那儿有连绵的较高的山丘和起
伏的圆丘,高达二三千英尺,纵贯这个国家,与海岸平行,离海边40英里。这条丘
陵带把沿海平原和腹地分隔开来。它只有一个山隘,有一条路通过这个山隘到达腹
地。那是一条土路,夏天被烤得如同水泥地,冬天则泥泞得像沼泽地。山巅那边的
土著是文杜族人,除了他们的工具是木制的以外,这个部落差不多进人铁器时代了。
马尔罗尼在不少荒野之地待过,不过他发誓说,他还从未见过像赞格罗的腹地那样
落后的地方。
在这条丘陵带的一头是一座大山,这儿的丘陵以此山得名。这座山甚至还不算
那儿最高的山。40年前,有一个传教士只身一人穿过丘陵进人腹地,然后又循着山
隘改朝南走,走了20英里,只见一座卓立不群的山隐约闪现在眼前。头天夜里这儿
下过雨,那是一场骤雨,在五个月的雨季里,这样的骤雨很多,给这个地区带来300
英寸的年降雨量。当传教士看见那座山时,它正在晨光里生辉,于是他把此山叫做
“水晶山”,并把这个名字记在日记里。两天后,他被人用棍棒打死后吃掉了。又
过了一年,这本日记才被一个殖民军的巡逻兵发现,它被一个土人村落当成一本符
咒来用了。殖民军士兵奉命执行任务,扫荡了这个村落,然后回到海岸,把这本日
记递交给教会。这样,那个传教士给这座山起的名字就流传下来了,虽然他为忘恩
负义的世界做过的其余的事情都被忘却了。后来,整个丘陵带也就以此山命名了。
那个传教士在晨光中看到的并不是水晶,而是许许多多头天夜里从山上泻下来
的雨水汇成的水流。雨水也从别的山上泻下来,可是这种景象被稠密的丛林遮住了,
丛林覆盖在那些山上,从远处看就像一条有许多裂缝的绿色毯子,如果从那儿穿过,
就可以看到那是一片又阴又潮的丛林。而那座有许多水流泻下而生辉的山所以会有
这番景象,是因为山坡上的植被实际上比较稀疏。那个传教士不曾想到这一点,许
多别的白人也没有见过,因此对此都很奇怪,不知是什么缘故。
在这片又阴又潮的环绕着水晶山的丛林里生活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