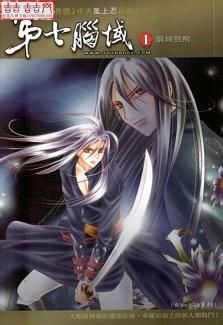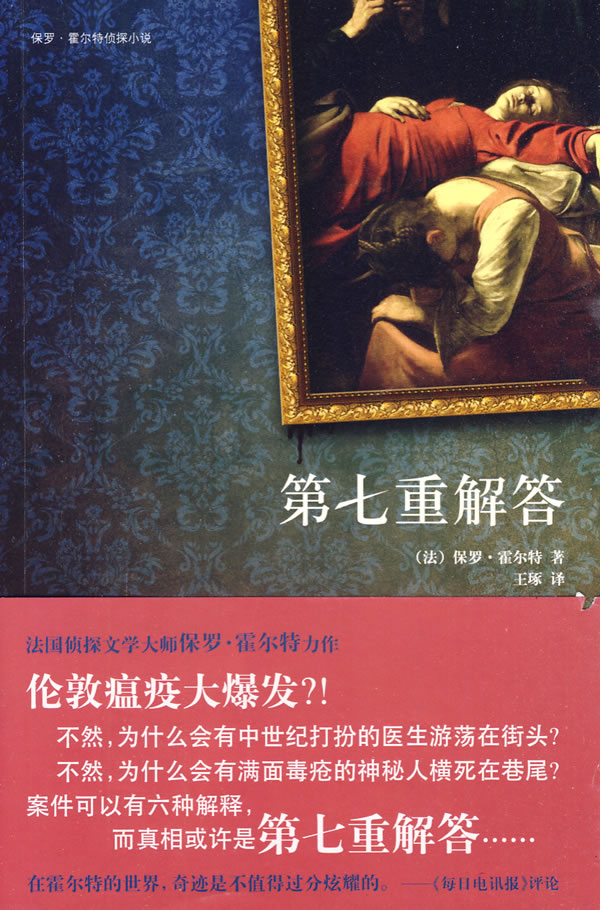第七重封印 by:朱夜(rednight)-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
李斌的额头淌着汗水:“啊!这个人有这么多血性腹水,肯定是肾脏的恶性肿瘤。”
“你摸到肾脏肿瘤了?”
“对。右肾明显肿大,有婴儿头部那么大。总量多少?”
我看了一眼积在连着吸引器的瓶子里的液平面:“不到500毫升。不过不是什么血性腹水,本来就是血。”
“怎么会!我肯定没有弄破血管!就算血管破了,现在她已经死了几个小时,血管里的血都凝固了,根本不会流出来。”
“你一心希望是个自然死亡,所以看不出来。”我摇了摇头:“你等着。”我沿着肋缘和腹股沟切开肌肉,李斌把肌肉向两边翻开,暴露整个腹内脏器。我指着右侧肾脏说:“是肾脏破裂,后腹膜巨大血肿,失血性休克死亡。”
腹部的大多数脏器全部为腹膜所包裹。肾脏位于身体的后壁,脊柱的两旁,只有前面被腹膜覆盖,后面紧贴着肌肉和肋骨。右侧肾脏比左侧低一些。大部分没有肋骨的保护,仅靠腰部的肌肉遮盖。正常人的肾脏充满血管。当血管破裂的时候,血液从破裂口流进肾脏周围、后腹膜和肌肉之间的间隙。由于腹膜有一定的张力,出血的速度不会很快,受伤的人不会立即死亡。同时,腹膜有去纤维作用,积聚在腹膜后方的血液通过这种作用不会凝固。
我用解剖针顺着脊柱往下,挑起了李斌的手指抠破的地方,把吸引器伸进去,吸出2100毫升血液。总共2600毫升,达到了致死的出血量。
“奇怪!”李斌啧啧地摇着头,“她又没有给车撞过,也没有被人打过,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体表完全没有伤痕?是不是血管自然破裂?”
内部通话器里“哔”地一声,然后传来胡大一的声音:“朱医生,你觉得从受伤到死亡有多少时间?”
“你想知道她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受的伤?”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人。”
“可是这几乎不可能推断出来。现在没了车票,不能证实她是从哪里上车。而且这个通道是两条地铁线路的汇合处,连她乘的是哪一条线路都没法确定。我看还是应该想法先调查她的身份。最好能抓住那个小偷。”我转过头看着玻璃隔墙里的胡大一,向他比划了一个手势。
胡大一咧着嘴笑了起来,露出两只稍微突出的犬齿,神情颇似看到了北极狐的脚印的萨摩耶犬:“她从离家最近的莲花路站坐上一号线的时间应该不晚于8点25分,到达人民广场大约是9点。然后走过通道去换乘二号线,坐1站路,在石门一路站下车,步行约15分钟,在9点半以前准时到公司上班。”
“什么意思?”李斌瞪大了眼睛,“这是魔法吗?还是小偷已经抓到了?”
“是老天有眼。”胡大一得意洋洋地笑道,“死者正好是最近我手上一起强奸未遂案的当事人。案子还没结,她已经先躺到这里来了。”
“你是说……”我尽力搜索着脑子里听到过的各种人名,在“季泰安”这个记录上停顿了一下,迅速向下搜索,最终找到了相配的数据项,“她是孙思诗,隆盛大楼那个什么传播公司的文员?”
“对。就是她。”胡大一干脆地答道。
李斌开始兴奋起来:“那么说是灭口案?那个男的为了报复而杀了她?”转念一想又摇头说:“不对!随便怎么应该有伤痕才对。”
“兄弟们!”胡大一支着桌子站起来,“这就是我要拜托你们的。找一下她大约在什么时候受的伤。凶器是什么。”
胡大一的问题提得非常明确,但回答起来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常规的尸体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其他重要器官的损伤和病变。排除了妊娠的可能性。右肾有一个很小的破口,因为太小,形状难以描述。剩下的只有顺着内伤的方向向体表去找。我和李斌用解剖放大镜沿着脊背一寸一寸地搜索下来,累得满头大汗。我开始后悔中午吃得太少。最后终于在右侧后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小的针眼样的伤口,边缘光整,没有一丝血迹。
无论是谁干的,这人肯定是职业高手。
我们结束了解剖工作,取了做检验的标本以后,我边洗手边思量着。
“有什么看法?”胡大一微笑着挤到我身边。
“要化验了才知道。”我干巴巴地说。
“我不是说血液报告。我是说尸体。”他保持着良好的耐心,继续微笑着。
“那不是我的工作。你去问李斌吧。正式报告很快就好。”
“没料到你还挺会打官腔。”
“这不叫打官腔。”我嘴上说,心里暗自加了一句,“这叫保护自己”。“不是该自己承担责任的,千万不要把脑袋伸出去给别人砍。”这句话同事们教育了我很多次了。法医出的验尸报告是要以自己的判断来负责任的,而实验室检验员的工作只要以机器的结果来负责任。当然,人的判断比机器要不可靠得多,易变得多。所以做检验员比做法医安全得多。
“我不需要你出的报告,”胡大一斜着身子靠在墙上,看着我的眼睛说,“再说你不是这个部门的,出的报告也没什么用处。我只想和你聊聊,就当作……那个什么……。吃中饭的时候的闲聊好了。说把,恩?”
“说什么?”
“闲聊。”
“我没时间。我还要去做那些血液标本。”
“我知道。那个不着急。我并不认为她被人下了毒或者安眠药。专业的杀手不需要这个。”
我抬起眼睛看着他:“你有什么证据?”
“对,我没有证据,你还没有验过血。”
“我是说专业杀手。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那你怎么想呢?”他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微笑,让人无法拒绝,也无力承受他的逼视。
我低下头,涂着肥皂:“伤口非常小,是用锋利的没有刃的工具突然插入人体造成的。刺破肾脏的血管后迅速拔出,腰部有力的肌肉一收缩,伤道的外口立即封闭,血不会向外流,只是在体内慢慢积聚。这时受害人完全清醒。她知道有人在她背后而且弄痛她了,但是在地铁四周都是人的环境中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受了致命伤。杀手可以随意地接近被害人,随意地往她身上挤,随意地提前离开,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不正常。从这一点来说,凶手是深思熟虑,志在必得。这样做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为了很大数目的钱,”我擦干双手,带上乳胶手套,准备去拿标本架。
胡大一饶有兴趣地追问:“还有呢?”
“要么怀着刻骨的恨。恨他的人肯定很多吧?”
胡大一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差不多吧。”
“要提审她的前男朋友吗?”
“那是当然的。你能估计受伤的时间吗?”
“很难说。内出血的速度很难估计。我不知道凶手是怎样估计的。也许估计她到单位才会死,那样死因看起来会更复杂。但是我想肯定是在地铁上。大街上要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觉得凶手对死亡时间的估计会如何?”
我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非常难估计。我知道肾脏科有一种检查方法,可以用带倒勾的长针,通过特殊的工具,在超声波的观察下快速刺入人体肾脏的部位再拔出来,取下很小一条肾脏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这种手术的一个重要的并发症就是出血。通常手术完成后病人需要平卧24小时,静脉滴注帮助凝血的药物,并且密切观察心跳、血压和尿色。即使这样,偶尔的情况下还是很难完全避免严重出血,需要马上开刀,找到出血的地方进行修补,否则有生命危险。你知道手术后发生严重出血最长的时间是多少?”
胡大一很谦虚地摇摇头:“洗耳恭听。”
我伸出一只手:“5天。”我伸长手臂趁势拿起标本架,从他面前挤过:“额外的工作完成了。现在是我的正式工作时间了。”
胡大一的直觉是正确的。血液样本没有检出任何酒精、毒物和药物。不过那不是我应该在乎的事情。我应该在乎的是,我的值班时间什么时候结束。
9月30日
我回家的时候泰安和阿刚都不在。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有一张纸条,很公整的有点孩子气的圆珠笔字迹写道:“豆浆在锅子里。桌子上的面包是泰安的早饭。厨房里的蛋饼留给朱夜。曹剑刚。”下面是蓝色记号笔粗大飞舞的字迹:“我全部吃光了。抱歉!想吃什么自己买吧!”没有署名。读来让我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我走到“开心堡”门口的时候,差点被从里面冲出来的一个男人撞倒。他没有说声“对不起”,反而粗鲁地咒骂了一声,匆匆拐过街角。我愣了一下,往“开心堡”门里看去。
外来妹店员还没有来上班。玲玲坐在柜台上自顾自地玩一个饮料瓶。韩雯捂着半边嘴唇,脸色铁青地注视着那男人离去的方向。鲜血从她的指缝里渗出来。
我推开门走进去:“雯雯?怎么回事?你撞到哪里了?”
她突地后退了半步,在柜台角撞了一下,眼神才聚集到我身上,恐慌地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然后她才回过神来,捂着嘴急急地摇摇头:“没事!没有撞过。”
玲玲把饮料瓶子竖放在柜台上,肉乎乎的小手拍皮球一般拍打着瓶子末端圆隆的部分,嘴里呀呀地说:“侬迭只(你这个)死女人,打侬(你)……打……”她玩得正开心,一边拍着瓶子,一边抬起小脸,冲着我露出天真的笑。
韩雯发疯似地揪住女儿的衣领,扬手要打。我急忙上去拉她的衣服,嘴里说:“小孩子又不懂!打也没用!”我的手还没有碰到她的衣袖,韩雯手已在半空中僵住,眼圈一红,眼泪扑倏倏地往下流。
“你…”还没等我开口,她转身快步走进柜台的里间。
玲玲望着韩雯离去的方向,又转头看看我,长着一双倒挂眉毛的小脸上顿时稠云密布。她呀呀地伸手叫道:“妈妈,妈妈抱抱…”韩雯关上了里间的门。我陪着笑脸说:“叔叔抱抱!”说着伸手把她抱起来,随手丢掉那个惹祸的饮料瓶子。小女孩不买账,两只小脚踢蹬着,双臂用力撑着我的肩膀,仰头朝向里间的门大声哭叫:“妈妈抱抱,妈妈抱抱……”我费力地边拍哄孩子,边向人行道上看。刚才那个男人连影子都不见,他的样子我没看清,只记得仿佛也是个倒挂眉毛。
韩雯很快从里间出来,脸上的泪痕和嘴唇边的血迹早已擦净。她从我手里接过孩子,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小孩粘人,烦得很。”
“没什么。蛮可爱的。力气也挺大的。”我打趣说,“将来可以做女排去打球。”
韩雯轻轻地拍哄着孩子,没有接口。我站在她身边,感觉自己完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了一句错误的话。
“我要买…面包!”我终于想出了一句应该不会错的话。
韩雯点点头,把孩子放到里间:“玲玲乖!娃娃在床上,自己去玩吧!”她走出里间,从一叠塑料袋中抽出一只,操起夹面包的夹子,低着头问:“你要哪一种?”然而,一滴泪水不受控制地落在她手背上。她慢慢地抓紧了塑料袋,指甲扒拉着,把它抓得不成形状。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我恰好晚来了一会儿。”
她抬起头:“你知道是什么事情?”
我呆了一下:“我…”
韩雯冷笑了一声:“看这里。”她掀起自己的上唇,露出挨打时嘴唇在自己牙齿表面擦伤留下的流血的伤口。“还有这里!”她丢下面包夹,捋起袖子,露出胳膊上陈旧的青紫:“这个,是上次我叫他不要整天搓麻将,被他拎着我的胳膊往墙上撞,留下来的。今天一早他才回来,一副输得空空的样子。我已经不想和他罗嗦。他开口就要钱。我不理他,他就自己开收银机。我说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你多少体谅体谅我一点吧。他说开‘差头’也难挣钱还整天受气,男人家搓搓麻将解解厌气,女人家管什么。我拉住他不让他动进货的钱,他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她顿了一下,盯着我的眼睛问:“如果你在,你会干什么?”
家务事是我最怕的麻烦事,我自己家还没摆平,这里又让我碰上一件。我尴尬地笑了一下:“我会叫他不要动手。”
“还有呢?”
“那个…我会找他单位…至少找他父母谈一次,让他们教育教育他。”
韩雯冷笑一声:“还有呢?”
“我…我想他也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吧?我会等他心情好的时间和他聊聊,多想想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的事情。不能老想着怎么去恨他,否则两个人不是要越来越僵?”
韩雯啧了一下嘴:“朱夜,你变了。”
“恩?啊,那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毕竟你还是喜欢他才嫁给他的啊,总有让你高兴的事情吧?”
韩雯盯着柜台里自己的倒影,一字一句地说:“我只喜欢玲玲。我要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读最好的贵族学校,见大世面。绝对不能让她输在起跑线上。否则就和我一样……为了小孩我吃多少苦无所谓。只要她记得我曾经为她做过。”她忽然换了笑脸,抬起脚对我说:“看看这个。还记得吗?”
我茫然地看着她脚上时髦的尖头高跟拖鞋:“呃?那个…好象在哪里看到过…”
“瞧你这记性!怎么读那么多书的!这不是前几天你在店里时,门口走过的那个女人穿的名牌货吗?”
我苦笑着说:“对…那个…好象是。”
“我才不会被人斩冲头(欺诈),去买那种贵得要死的东西呢。名牌又不当钱用。这是在陕西路上的小店里买的,样子和正牌货一模一样,穿着很登样(精神)吧?只要30块钱。”
我赔笑着点头:“好便宜啊。”
韩雯得意地说:“省下来